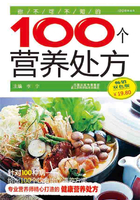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他真的是个怪人么?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更是不对。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
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蒂切利和达文骞。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们是最讨厌Ruskins的。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得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刊于
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报》第9版“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
山西通信
××××: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我是没有出过门的,没有动身之前不容易动,走出来之后却就不知道如何流落才好。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团黑影里去。微月中步行寻到田垄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了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地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
我不会说,说起来也只是一片疯话人家不耐烦听。以我描写一些实际情形我又不大会,总而言之,远地里,一片田亩有人在工作,上面青的,黄的,紫的,分行的长着;每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阳光,投射着转动的光影;每一个小城,前面站着城楼,旁边睡着小庙,那里又托出一座石塔,神和人,都服帖的,满足的,守着他们那一角天地,近地里,则更有的是热闹,一条街里站满了人,孩子头上梳着三个小辫子的,四个小辫子的,乃至于五六个小辫子的,衣服简单到只剩一个红兜肚,上面隐约也绣有她嬷嬷挑的两三朵花!
娘娘庙前面树荫底下,你又能阻止谁来看热闹?教书先生出来了,军队里兵卒拉着马过来了,几个女人娇羞的手拉着手,也扭着来站在一边了,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忙我们拓碑文。说起来这个那个庙,都是年代可多了,什么时候盖的,谁也说不清了!说话之人来得太多,我们工作实在发生困难了,可是我们大家都顶高兴的,小孩子一边抱着饭碗吃饭,一边睁着大眼看,一点子也不松懈。
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的,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就也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的问。“多了多了。”
我们高兴的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我们看看这里金元重修的,那里明季重修的殿宇,讨论那式样做法的特异处,塑像神气,手续,天就渐渐黑下来,嘴里觉到渴,肚里觉到饿,才记起一天的日子圆圆整整的就快结束了。回来躺在床上,绮丽鲜明的印象仍然挂在眼睛前边,引导着种种适意的梦,同时晚饭上所吃的菜蔬果子,便给养充实着,我们明天的精力,直到一大颗太阳,红红的照在我们的脸上。
刊于
1934年8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6期第12版
彼此
朋友又见面了,点点头笑笑,彼此晓得这一年不比往年,彼此是同增了许多经验。个别地说,这时间中每一人的经历虽都有特殊的形相,含着特殊的滋味,需要个别的情绪来分析来描述。
综合地说,这许多经验却是一整片仿佛同式同色,同大小,同分量的迷惘。你触着那一角,我碰上这一头,归根还是那一片迷惘笼罩着彼此。七月!——这两字就如同史歌的开头那么有劲——八月,九月带来了那狂风,后来,后来过了年——那无法忘记的除夕!——又是那一月,二月,三月,到了七月,再接再厉的又到了年夜。现在又是一月二月在开始……谁记得最清楚,这串日子是怎样地延续下来,生活如何地变?想来彼此都不会记得过分清晰,一切都似乎在迷离中旋转,但谁又会忘掉那么切肤的重重忧患的网膜?
经过炮火或流浪的洗礼,变换又变换的日月,难道彼此脸上没有一点记载这经验的痕迹?但是当整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自然“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脸上所刻那几道并不使彼此惊讶,所以还只是笑笑好。口角边常添几道酸甜的纹路,可以帮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认这一点:在迷惘中人最应该有笑,这种的笑,虽然是敛住神经,敛住肌肉,仅是毅力的后背,它却是必需的,如同保护色对于许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样。
那一晚在××江心,某一来船的甲板上,热臭的人丛中,他记起他那时的困顿饥渴和狼狈,旋绕他头上的却是那真实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实的狂敌杀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飞机:美丽得像鱼像鸟……这里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为同样的另外一个人懂得那原始的骤然唤起纯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时他在××车站台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风雨摧落后的落叶,瑟索地蜷伏着,他们心里都在回味那一天他们所初次尝到的敌机的轰炸!谈话就可以这样无限制的延长,因为现在都这样的记忆——比这样更辛辣苦楚的——在各人心里真是太多了!随便提起一个地名大家所熟悉的都会或商埠,随着全会涌起怎样的一个最后印象!
再说初入一个陌生城市的一天——这经验现在又多普遍——尤其是在夜间,这里就把个别的情形和感触除外,在大家心底曾留下的还不是一剂彼此都熟识的清凉散?苦里带涩,那滋味侵入脾胃时,小小的冷噤会轻轻在背脊上爬过,用不着丝毫锐性的感伤!也许他可以说他在那夜进入某某城内时,看到一列小店门前凄惶的灯,黄黄的发出奇异的晕光,使他嗓子里如梗着刺,感到一种发紧的触觉。你所记得的却是某一号车站后面黯白的煤气灯射到陌生的街心里,使你心里好像失落了什么。
那陌生的城市,在地图上指出时,你所经过的同他所经过的也可以有极大的距离,你同他当时的情形也可以完全的不相同。
但是在这里,个别的异同似乎非常之不相干;相干的仅是你我会彼此点头,彼此会意,于是也会彼此地笑笑。
七月在卢沟桥与敌人开火以后,纵横中国土地上的脚印密密地衔接起来,更加增了中国地域广漠的证据。每个人参加过这广漠地面上流转的大韵律的,对于尘土和血,两件在寻常不多为人所理会的,极寻常的天然素质,现在每人在他个别的角上,对它们都发生了莫大亲切的认识。每一寸土,每一滴血,这种话,已是可接触,可把持的十分真实的事物,不仅是一句话一个“概念”而已。
在前线的前线,兴奋和疲劳已掺拌着尘土和血另成一种生活的形体魂魄。睡与醒中间,饥与食中间,生和死中间,距离短得几乎不存在!生活只是一股力,死亡一片沉默的恨,事情简单得无可再简单。尚在生存着的,继续着是力,死去的也继续着堆积成更大的恨。恨又生力,力又变恨,惘惘地却勇敢地循环着,其他一切则全是悬在这两者中间悲壮热烈地穿插。
在后方,事情却没有如此简单,生活仍然缓弛地伸缩着;食宿生死间距离恰像黄昏长影,长长的,尽向前引伸,像要扑入夜色,同夜溶成一片模糊。在日夜宽泛的循回里于是穿插反更多了,真是天地无穷,人生长勤。生之穿插零乱而琐屑,完全无特殊的色泽或轮廓,更不必说英雄气息壮烈成分。斑斑点点仅像小血锈凝在生活上,在你最不经意中烙印生活。如果你有志不让生活在小处窳败,逐渐减损,由锐而钝,由张而弛,你就得更感谢那许多极平常而琐碎的磨擦,无日无夜地透过你的神经,肌肉或意识。这种时候,叹息是悬起了,因一切虽然细小,却绝非从前所熟识的感伤。每件经验都有它粗壮的真实,没有叹息的余地。
口边那酸甜的纹路是实际哀乐所刻画而成,是一种坚忍韧性的笑。因为生活既不是简单的火焰时,它本身是很沉重,需要韧性的支持,需要产生这韧性支持的力量。
现在后方的问题,是这种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决不凭着平日均衡的理智——那是不够的,天知道!尤其是在这时候,情感就在皮肤底下“踊跃其若汤”,似乎它所需要的是超理智的冲动!
现在后方被缓的生活,紧的情感,两面磨擦得愁郁无快,居戚戚而不可解,每个人都可以苦恼而又热情地唱“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或“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支持这日子的主力在哪里呢?你我生死,就不检讨它的意义以自大。也还需要一点结实的凭借才好。
我认得有个人,很寻常地过着困难日子的寻常人,写信给他朋友说,他的嗓子虽然总是那么干哑,他却要哑着嗓子私下告诉他的朋友:他感到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得荣耀,异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这话或许可以在许多心弦上叩起回响,我常思索这简单朴实的情感是从哪里来的。信念?像一道泉流透过意识,我开始明了理智同热血的冲动以外,还有个纯真的力量的出处。信心产生力量,又可储蓄力量。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我可曾觉察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也正是那坚忍韧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都为它忠贞地活着或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会永远地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彼此仍会微笑点头的缘故也就在这里吧?现在生活既这样的彼此患难同味,这信心自是,我们此时最主要的联系,不信你问他为什么仍这样硬朗地活着,他的回答自然也是你的回答,如果他也问你。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那理智热情都不能代替的信心!
思索时许多事,在思流的过程中,总是那么晦涩,明了时自己都好笑所想到的是那么简单明显的事实!此时我拭下额汗,差不多可以意识到自己口边的纹路,我尊重着那酸甜的笑,因为我明白起来,它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