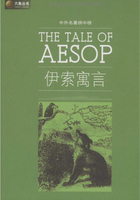我谈及《疯子》的话中有“嫌恶”一词,我用红墨水在其周围画了一个圈。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The Sleep Walkers里的话置于“昨天”与“明天”的唇间,而不是置于母亲及其女儿的唇间,莫非你会把“嫌恶”一词换成另外一个词?
关于我的灵魂的洞穴,我能说什么呢?那令我生畏的洞穴是我在人们的宽畅大道上、鲜花盛开的田地里和植物茂密的森林中感到疲倦时藏身的地方。当我找不到头靠的地方,我便进入我的灵魂洞穴。假若在我喜欢的人当中谁有勇气进入那洞穴,那么,他只能看到那里只有一个人正在双膝跪地做礼拜。
你喜欢《疯子》里的那三幅画,使我感到高兴,且向我指明你的两只眼睛中间还有第三只眼睛。我再就知道你的两只耳朵之后还有无数无形之耳,能够听到类似于沉静的细微声音,那种声音并非发自唇舌,而是源于舌与唇之外的甜蜜孤独、欢乐痛苦及对于遥远未知世界的向往。
你问我,在我写下“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us enslave Something in us”之后,是否想让任何人了解我?不,我不想让任何人了解我,如果那种了解仅仅是一种精神奴役的话。自以为了解我们的人何其多啊!其实我们只是发现我们的部分表象类似于他们生活中某一次所经历的什么东西罢了。但愿他们满足于佯装了解我们的秘密吧!其实,我们的那种秘密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而他们却将我们用各种符号和数字封起来,然后就像药剂师摆置药丸药粉瓶子那样,把我们将放置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信条的一个架子上!说你在你的部分书中摹仿我的那位文学家,不正是自称了解我们、晓知我们内心秘密的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吗?你能够让他相信独立才是灵魂的正道,冬青槲和柳树是不能在彼此树荫下生长的吗?
此信写到这里,而我开始想说的话一句还不曾说出来。设想一下,谁又能将那稀疏美丽的雾霭化为塑像和碑碣呢?但是,能听到声外之声的黎巴嫩姑娘,笔尖困难到雾霭中的形象和幻影。
向你那美好的灵魂致意,向你那高贵的情怀和博大心田问安。上帝保佑你。
忠实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919年5月10日纽约
亲爱的梅娅小姐:
《行列之歌》今日出版,我将收到的第一本书寄给你。该书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它是一个梦,其一半仍然是雾霭,另一半则几乎成为可以感触到的实体。假若你觉得其中有的东西好,它就会化为美好现实;倘使你认为有什么东西不好,它会全部返回雾霭中去。
向你的美好灵魂致以一千个问候和敬意。上帝保佑你平安。
忠实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919年6月11日纽约
亲爱的梅娅小姐:
我从野外长途游行回来,便看到了你的三封信和你那篇发表在《都城报》的美文。我从仆人那里得知,这几封信,该说这份珍贵财富,是四天前一起寄到的。看来,埃及邮政当局就像查封外界进步的邮件一样,曾中止过国内寄出的信件的投递业务。
我丢下这间办公室里等待我做的一切,整个白天都在聆听你那辗转蹒跚在甜润与严厉之间的谈话;我之所以说严厉,那是因为我发现你第二封信里有某些看法,我会因那些看法而感到痛苦的。可是,我怎能允许我的心灵去遥望那嵌满繁星的晴朗夜空中漂浮的云状物呢?我怎能把我的目光由鲜花怒放的大树转向它的枝条投下的阴影呢?我又怎能不接受满佩珠宝、香气四溢的纤细之手的轻触柔刺?将我们从五年的沉默中拯救出来的谈话,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会转化成为责备或争论。我接受你说的一切,因为在我看来,已有七千英里将我们隔开,我们不应该再在这遥远距离之间加入虎口之距,而应尽力运用我们对美好爱好、对泉源的向往和对永恒的渴望将距离缩短。我的女友,在这些日日夜夜里,我们经历的痛苦、干扰、疲倦和磨难已够我们受的了。我认为,一种能在绝对单纯前站稳的思想,是不会被某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或某一封信中的一种意见搅乱的。那么,就让我们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多半是言辞上的分歧放入金箱子里,然后将之抛入微笑的大海之中去吧!
梅娅,你的信多美多甜,就像从高处奔腾而下的一条香醇之河,唱着歌流淌在我的美梦峡谷中,简直就像奥尔甫斯的六弦琴,将天边变成眼前,把咫尺推向遥远,并以其奇妙的颤音将顽石化作炽燃的火炬,把枯枝变为抖动的翅膀。一天收到你的三封信,我该说什么呢?那是我偏离尘世之路的日子,整天漫游在“有高柱的伊赖姆”城中。
我用什么回答你的那些问题呢?心灵中有不能伴墨水流淌的东西,我怎能继续谈下去呢?但是,一定要继续谈。因为无声之言,你也是明白的。
你在第一封信中说:“假若我在纽约,这几天里我就会访问你的画室。”莫非你从未访问过我的画室?记忆的外衣之后,不是还有记忆的隐形体躯吗?我的画室是我的宇宙,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博物馆,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它是森林,在那里生命呼唤着生命;它是空旷的沙漠,我站在沙漠当中,映入眼帘的只有沙海和能媒之海。朋友,我的画室是一座没有四壁和屋顶的房舍。
但是,在我的这个画室里有许多我喜欢和我保存的东西。我素喜古玩。在画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些历代的古董,如埃及、希腊、罗马的雕塑和绘画,还有腓尼基的玻璃器皿、波斯瓷器、古书、意大利和法国的绘画,还有数件默默有言的乐器。有那么一天,一定要弄到一尊迦勒底玄武石雕像。我喜欢迦勒底的每一件东西,这个民族的神话、诗歌、祷词、建筑,甚至那个时代留下的微不足道的艺术品和手工制品,都能唤起我内心深处遥远隐约的回忆,将我带回到悠远的过去,使我透过未来之窗看到现在。我喜欢古迹,深深迷恋着古代文物,因为它是用一千只脚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人类思想所结出的硕果;正是那不朽的思想带着艺术潜入大海深处,旋即又带着艺术扶摇直上而达银河岸边。
你说“你满足你的艺术,你是多么幸福!”这句话使我思忖良久。梅娅,不啊!我既不满足,也不幸福。在我的心灵中,有一种不知满足为何物的东西,但并不像贪欲;同时还有一种不知幸福为何物的东西,但并不像困苦。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永久的悸动和持续的痛苦,但我却不肯替换和改变它——谁像这样,便不知何为幸福,亦不晓何为满足,但他从不诉苦,因为诉苦之中包含着某种怡适和某种形式的超脱。
你为你的雄厚天赋之才感到幸福和满足吗?梅娅,请告诉我,你满足、幸福吗?我似乎能听到你低声细语道:“不,我既不满足,也不幸福。”满足是自足,自足是有限的,而你是无限的。至于幸福,则是一个人将自己的心灵充满生活的玉液琼浆;不过,倘若他的杯子长七千法尔萨赫、宽七千法尔萨赫,即使把生命的全部注入他的杯中,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知道何为幸福。梅娅,你的杯子不是长宽各七千法尔萨赫吗?
关于我的“精神氛围”,我能说什么呢?一年或两年来,我的生活不乏宁静与平和,然而今天,宁静被喧嚣所替代,争执取代了平和。人们吞噬着我的日日夜夜,用他们的志趣和意向淹没了我的梦想。有多少次,我逃离这走投无路的城市,去往一个遥远的地方,都是为了摆脱人们的纠缠,同时也为了挣脱自己的心灵幻影。美国人民威武强悍,孜孜不倦,不累不眠,没有梦幻。这里的人民若憎恶起一个人,能用冷漠将之置于死地;如果热爱起一个人,也爱得死去活来。谁想生活在纽约,他就应该成为一柄利剑,但要插入蜜糖做的剑鞘里:利剑用于恫吓那些空耗时光之人,而蜜糖则可以饱饥馑者之腹。
我逃往东方的那一天将要来临。我对祖国的思念几乎将我溶化。如果不是这只我亲手插编的笼子,我早就登上了第一班开往东方的轮船。可是,哪个人能够丢下他耗毕生之力用雕石砌建而成的房舍呢?即使那房舍是一座监牢,他也不能或不想一日之间弃离。
亲爱的朋友,打搅你了!我光谈自己,尽诉说一些本该起来进行斗争,而不应该重提的事情。
你对《行列之歌》的喜欢,也使得我对之倍加珍视。你说你将背诵其中诗句,如此大恩大德,我当躬身低头行礼。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背诵比《行列之歌》,乃至我已写出和正在写出的更知名、更精美、更雅致的诗篇。关于书中的插图,你说道:“你们是艺术大家,凭借双子星座君王们赐予你们的能媒之力创造了这奇珍之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来了,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贫乏和主张理解那鸿篇巨制。因此,你们因我们的愚昧而成了不幸受害者,而我们也因之成了吃亏的可怜人。”这话我是不能接受的,并请原谅我对之表示反叛(我的反叛何其多啊!)。梅娅,你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在艺术男女之中,如同红花由绿叶簇拥。你在《都城报》上发表的关于《疯子》插图的评论文章,便是深刻艺术感触、精明独到思想和锐利评论目光的最好证明。评论家的眼睛看到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东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是第一位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如在自己家中,迈着坚定步伐,走进“九姊妹”林中的东方姑娘。你何不告诉我你是怎样晓知你所通晓的一切的?你是在哪个世界采集到你的心中奇珍异宝的?在你的灵魂来到黎巴嫩之前,曾生活在哪个时代?天赋之才当中的秘密要比生命的秘密更加深刻。
你想听听西方人怎样议论我,我谨对你这种热忱和民族感情致一千谢意。他们说了很多话,言过其实,猜想偏颇,认为兔子窝里出了骆驼。朋友,上帝知道我一读到谈我的那些美好言词,我便泪洒胸怀。称赞是人们置于我们肩上的一种责任重担,它会使我们自感柔弱。但是,一定要前进,哪怕重担压弯我们的背,一定要从柔弱中发现力量。我在另封信中给你寄去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评论,你将从中知道西方人已经厌恶了他们自己的灵魂幻影,对他们自己也已感到烦腻,于是找他们不熟悉的新奇东西进行消遣,尤其喜好东方的东西。黄金时代过去之后的雅典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月或稍多点儿时间以前,我把报纸上关于《疯子》的一组评论寄给了伊米勒·泽丹先生;当然,他也是你的一位朋友。
赞美上帝,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你们的危机。我看过那些游行示威的消息,想象你定会惊恐不安,于是我也惶恐不安起来。在惶恐不安情况下,我反复默诵起莎士比亚的诗句:
Do not fear our person.
There’s such divinity doth hedge a king.
That treason can but peep to what it would.
Acts little of his will.
梅娅,你是受神灵呵护的。在你的心灵中有一位受上帝保护、免遭任何灾难的国王。
你问到在我这里有没有你们的朋友?
有啊,凭生命起誓,凭生活中的伤人甘甜和神圣苦涩起誓,我们这里有你的朋友:其意志保卫着你们,其心灵愿你们安好,愿厄运远离你们,保佑你们免遭任何伤害。不在场的朋友也许比在场的朋友更亲近。对于行走在平原上的人来说,那大山不是显得比山中居民眼里的山更加威严、清晰和显著吗?
夜色已用它的饰带笼罩了这个画室,我再也看不到我的手所写的东西了。谨向你致一千个吻一千个敬意。上帝永远护佑着你。
你的忠实朋友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919年6月11日纽约
《疯子》已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该集子的部分内容被译成其他几种文字。法文译本不久将问世,到时候我将给你寄去一本。
1919年7月25日纽约
亲爱的梅娅小姐:
自打我开始给你写信到现在,你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曾长时间地思念你,与你交谈,询问你的内心所想,探索你的秘密。奇妙的是我曾多次感觉着你的化身就在这画室之中,正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不时地与我说话,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
我这样说,你当然会觉得离奇;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奇怪,一种需求使我不由自主地给你写起信来。假若我能破译隐藏在这不由自主和迫切需求之后的秘密,那该多好啊!
有一次你对我说:“头脑之间的唱和、思想之间的交流,也许知觉是无法感触到的;但是,谁能断然否定一国同胞之间的唱和与交流的存在呢?”
这段美好话语中有一个基本事实,我曾主观臆断过它的存在,而现在却通过心灵体验证实了它。近来一段时间,我已确信有一种精细、坚固、奇妙的精神纽带,它的本质、特性与影响不同于其他任何纽带,而是更强烈、更坚韧、更长久,就连血缘的、胎生的,甚至道德的纽带都不能与之相比。这纽带中没有一根由摇篮到坟墓闪过的日日夜夜所纺成的线,也没有一根由过去的理想、今日的愿望或未见的希冀纺成的线。也许这种纽带存在与这样的两个人之间:过去、现在或许将来都不曾、没有或不能将该二者聚集在一起。
梅娅,在这种纽带里,在这种心灵情感里,在这种隐形的相互理解中,有联翩的梦,它比徜徉在人类心中的一切梦都奇异古怪,那是包容在梦中的梦中之梦。
梅娅,在这种互相理解之中,有一首深沉、静怡的歌,我们在夜深人静之时能够听到它,它会把我们带到黑夜、白昼、时光和永恒之遥远的所在。
梅娅,在这种纽带里,在这种情感之中,有一种永不消失的痛苦忧烦,但它对于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会用我们所知道和想象的快乐尊荣将之替换。
我之所以把不能也不想告诉你的东西告诉你,只是因为你的心灵中有着相似的情怀。倘若我展示给你的是一项早为你所知的秘密,那么,我便是承蒙生活厚爱、被生活拥立在白色宝库前的幸运者之一;假使我所表明的仅仅是我个人的私事,那么,你可以将此信一火焚毁。
朋友,我恳求你给我写信,求你用翱翔在人间道路上的绝对单纯精神给我写信。你和我都对人类了解甚多,不但了解使他们相互接近的志趣和爱好,也了解令他们彼此疏远的因素与办法。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躲避一下,即使离开他们走过的老路一个时辰,站在一旁静观日夜、时光与永恒之外的东西,哪怕只一次呢?
梅娅,上帝永远呵护着你。
你的忠实朋友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919年7月26日
此书将在今年初出版,我将把收到的第一本样书寄给你。
1919年11月9日纽约
亲爱的梅娅小姐:
你恨我,你怨我,你有权利,你是对的,我只有默认听从。我是个远离度量衡世界的人,你何不忘掉我犯的过错呢?你何不将不适宜保存在能媒箱中的东西放在“金箱”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