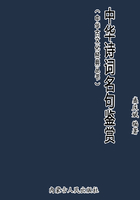我主张维护叙利亚在议会政体下的地理上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当叙利亚人应该实现这一点时,即新的一代人成熟之时;此事的成就要在十五年之后。我主张阿拉伯语要成为学校和所有政府机构的官方首选语言。至于把叙利亚置于美国关怀之下,则是一种极美想法;如果这种想法得以实现,我们将成为最幸运的东方人民。但不幸的是这种想法根本实现不了,因为美国政府不想要叙利亚,美国的报纸反对叙利亚,美国民众厌烦叙利亚。我与这个国家的许多有名望的人物及思想家交谈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不希望美国总体上介入欧洲问题,尤其是不要插手近东事务。
我知道,出于宽厚与慷慨,部分美国知士要求把叙利亚、亚美尼亚和阿拉伯半岛置于他们的政府关怀之下。但是,宽厚与慷慨是一件事,而国际政治毕竟是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国际野心仍然怀抱着国际政治。美国不想与欧洲国家发生争执。这便是弱小民族的一种不幸。假若将叙利亚置于美国,或法国,或英国,或所有这些大国的关怀之下,正像部分叙利亚人所要求的那样,那么,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必须继续提出强烈要求,那就是同时实现叙利亚的地理上的统一、国民议会政体、义务教育和将阿拉伯语作为优先语言和官方语言……如果我们不想咀嚼、吞咽和消化,那么,我们就应该维护我们的叙利亚模式,即使叙利亚在天使的呵护之下。我相信,叙利亚在脱离的见习阶段进入独创时期之后,一定能够做些值得感谢的事情;假若我没有这一点儿自信,我造就做了假若任何一个强国的选择。西方人可以在科学、经济和农业上给我们以帮助,但是,他们却不能给予我们以精神上的独立。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独立,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生机勃勃的民族。独立是人的实在的属性,每一个叙利亚人都有,但它正在沉睡之中,我们应该将之唤醒。
纪伯伦
伊米勒兄弟:
向你的美好灵魂和博大胸怀致意。
十天前我就想给你写信,但我不想让自己的一封信不附上寄给《新月》的一点儿东西,因此稍晚了一些,直到写成这篇《沦落者》。正如你所看到的,这篇东西奇异含糊,题目也含糊奇异。写这篇东西时,我自感自己在用雾霭塑像。但我认为写这样题材的东西是对东方新一代人有益的事情。因为它会唤起询问遥远的和隐蔽的东西的兴趣。上月我写了一篇故事,题目是《有高柱的伊赖姆人》,想寄给《新月》,但笔会——纽约的文学家协会——成员没能一致同意在《旅行家》特号上发表;你知道,《旅行家》是笔会的正式报纸。
我不知道,也不曾梦想到,叙利亚的监督机构竟敏感到了连《各自心中的黎巴嫩》这样的文章也不允许进入那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国家。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我觉得他们把那些文章从《新月》撤下来,他们是在赞扬我,而我是不值得赞扬的;他们在侮辱自己,而他们是不该受侮辱的。这种令人痛苦的问题已经给你带来了麻烦,也给可爱的《新月》带来伤害,使我感到甚为不安。
你向我转达文学家们对我表示同情并对我怀着美好情感,这使我欣喜、感动不已。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谦虚——我们仍在路端,已经过去的二十年,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对我来说都只是准备和立志时期。直到现在,我仍未做出什么值得留存在太阳面前的东西。我的思想尚未结出成熟之果,而我的网也尚未被水浸没。兄弟,你何不要求亲爱的兄弟们宽限我一点儿,好让我做出点儿值得敬献给他们的东西呢?你知道,假若来自外界的敬重是我所不配得到的,那将会使我心中充满痛苦和忧伤,我会感到由衷的害羞。
在已过去的春天里,我本准备去巴黎,然后去埃及和叙利亚,但我改变了主意,遂将自己置身于一些绘画和文学创作之中,这些工作需要我在这个国家留上两年,至少也要十八个月。如果不是这些工作和合同把我紧紧缠住,我今天已在开罗了。我的生活很饱满,简直有些混乱不堪。我雕刻的那些小石子,本想用来建造一座梦中之屋,如今却变成了一座狭窄的监牢。不过一定要回到东方去,我很想念我的祖国和国人。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伊米勒兄弟:
向你的博大心胸致意。
寄给你我的一篇文章《谈阿拉伯东方复兴》。正像你看到的,文中不乏剧烈、严责之辞。可是,我又不能把我的信仰表达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应该依靠自己,回到东方原则上去的时候了吗?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当向西方人显示我们还没有死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我们不需要抓着他们的尾巴往前走吗?
是的,我本想在今年访问埃及和叙利亚。但是,由于健康原因,我离开工作已经整整一年,从而使我倒退了两年时间,就是把我告诉过你的文学、艺术合同全部搁置下来了。我应该在这个国家待到用英文写的《先知》出版,完成我已许诺下的画作。我很思念东方,尽管有些朋友写给我的信使我感到内心失望,甚至有时使我宁愿在异乡人中孤度日月,也不愿意在亲朋之间苦熬时光。尽管如此,我也将回我的老“家”去,亲眼看看岁月使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相信,东方思想,尤其是阿拉伯思想,在不久的将来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请接受我的敬意与友情。上帝为忠实的兄弟护佑你。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918年
伊米勒兄弟:
《疯子》在美国和英国所造成的轰动效应确实是最奇妙的事情之一。法国赴美国代表团团员比亚德·兰克斯将《疯子》译成了法文,本季度末将在巴黎出版。《疯子》的部分内容被译成俄文、意大利文和挪威文,看起来西方人已经对他们的灵魂之梦及思想倾向感到疲惫,于是对奇异及熟悉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简直有些渴望至极。尤其是对东方的东西或被他们想象为东方的东西更感兴趣。
我相信东方思想,尤其是阿拉伯思想,在不久的将来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伊米勒兄弟:
一、重视印刷
几日前,《行列之歌》一书出版了,我寄给您一本,期望你们从中发现令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想以不同于大多数阿拉伯新书的装帧设计出版这部书,以便唤起阿拉伯世界印刷者们的雄心壮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外国图书上来。因为在我看来,印刷是一门艺术,我们应该给予重视,尤其在今天,我们正处于转期阶段的今天。我之所以这样说,因我深知一首好诗永远是一首好诗,哪怕用煤块写在墙上。不知您是否见过,那些被称为“诗集”的书,因为没有精美的装潢而叫人感到有些遗憾?《行列之歌》作为一首长诗,是我在森林里做的一个梦;当我把它写出来时,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雕塑家,试图用海上的雾霭塑一尊像。诗人的心事只能用锁链、桎梏似的语汇和韵律来表达,又能怎样述说自己的梦呢?
二、意在著述
过去和将来,我的第一志愿都是著具有精神滋味和道义价值的书。不过,若有物质利益,我想当最后一名受益者,而不是去争第一。我想当最后一名受益者,也是一种自私;请不要认为我不是个人主义者!
三、我的小传
……你很关心我,要我把我的小传寄给你。兄弟,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难题,简直可以说是难中之难了。除了说我生于四十年前,工作了四十年,我还能说我自己什么呢?
这就是我的小传全部。有时候,我仿佛认为自己每天都有一个新生。我的过去,只不过是在夜里做了一个梦。你知道,自认为孩童的人,是羞于在人们面前谈自己的生平历史和展示雾霭一般的朦胧过去的。我的意志、慕爱、背叛与驯服,直到现在还没有选定一个自由模子,以便面对太阳而站立。如果明日到来了,我却结出了适于见光明的果子,那么,那种果子本身便是我的生平小传,那其中包涵着我生平中所经历的痛苦、欢乐、寂寞、欢庆、光明与烟雾。
我的兄弟,请接受我的饱含友爱与敬佩的问候。安拉让你把兄弟的亲情牢记心中。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致阿卜杜·迈西哈·哈达德
阿卜杜·迈西哈·哈达德1890年生于霍姆斯。在叙利亚小学接受初级教育,之后入巴勒斯坦拿撒勒的俄国师范学校。
1903年迁居美国,1913年在那里办起《旅行家》报。1920年笔会成立之后,《旅行家》报变为笔会会员的讲坛。阿卜杜·迈西哈及其胞弟奈德莱·哈达德为笔会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这位文学家远离祖国半个世纪之多,只在1960年遍访过祖国的山川。这次返乡旅行的收获写成一本书,题名为《游子印象》。之后,阿卜杜·迈西哈回到美国,1963年客逝异乡。
除了开《旅行家》报,还留下《侨民的故事》、《游子印象》等著作。
他是纪伯伦最忠实的朋友之一。
1918年10月7日纽约
《旅行家》报主编先生阁下:
叙利亚难民需要援助,这个问题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鉴于叙利亚与外界的通路已经打开,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援助物资能否送到灾民的手中;
鉴于叙利亚的大批饥民在美国没有亲人,也没有能够专门帮助他们的人;
鉴于“援助叙利亚和黎巴嫩难民委员会”已变得虚弱与混乱不堪,再也不能尽自己的职责。
因此,我认为应该要那些曾为这个援助计划出过力的阿拉伯报纸的主编们和富有民族热情、能够代表公众舆论的优秀文学家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为委员会注入新的生命,将委员会置于能够为难民尽更高的义务的地位。我作为上述委员会的成立发起人之一,建议首先重新选举该委员会的成员;其次,重新审阅委员会的基本办法条款;第三,研究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办法。
请就此问题发表你的坦诚意见。上帝保佑你。
纪伯伦
致艺术家优素福·侯维克
优素福·侯维克1883年生于黎巴嫩贝特龙省的哈勒塔,就读于希克玛(意为睿智)学校,在那里结识了纪伯伦。
在罗马学习艺术,然后转巴黎。在那里与纪伯伦再次相见。1939年回到黎巴嫩,在贝特龙省的奥拉村定居下来,远离人们,专心持锤琢凿艺术作品。1962年逝世。
侯维克的著名雕刻作品有黎巴嫩和阿拉伯的名人雕像,如他的叔父易里亚斯·侯维克大主教、黎巴嫩英雄优素福·凯尔姆、费萨尔一世国王、法赫尔丁二世埃米尔、思想家和文学家艾敏·雷哈尼、诗王艾哈迈德·邵基……他还把黎巴嫩的许多神话传说用雕刻语言表现出来。
他著有《回忆与纪伯伦相处岁月》,由易德费克·吉里迪尼·舍伊布卜编辑出版。
1911年2月19日波士顿
优素福兄:
能在巴黎拥有一个山羊的榻位,那真是幸福的人!漫步在塞纳河畔,注视着那些旧书旧画箱,该是多么惬意!我居住在这座充满朋友和相识的城市,犹如被流放到天涯海角,那里的生活冷似冰霜,黑暗得如同灰烬,沉默无声好似狮身人面像,虽然我的妹妹就在我的身旁,不论到哪里,周围都是亲近的人。优素福,早晚都有许多人到我家里来,但我对这种生活不满意……我的工作正走上山巅,我的思想平平静静,我身体健康,正享受着存在的乐趣……优素福,但是,我并不愉快。我的心灵又饥又渴,需要吃的和喝的,但不知那食与水在什么地方……新林一位高贵之花,它不会生长在背阴处。荆棘则会生长在任何地方……雷哈尼住在纽约离我不远的地方,他的生活很贫困。我俩常常诉自己的内心苦楚,想念黎巴嫩,歌颂祖国之美……那便是患艺术病的东方之子的生活。那便是被流放到这个工作奇异、行动呆滞得令人啼笑皆非的“阿波罗”子孙们的生活……
优素福,你好吗?你生活在大路两侧看到的人类幽灵中间快活吗?我不在期间,你都画了些什么画?哈米尔顿太太给我写的信中说了你许多好话。你做她的朋友吧,她很热情,此外她还是暴虐、怜悯与黑暗、光明艺术之神的殉难者之一……但丁把你带到了何方?难道你陪着他到了那个深“渊”和那些危险渡口之间?波提切利的精神金发女友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方?莫非你在那远离世界的遥远舞台上,面对永恒世界,就站在她的附近?围绕着地狱和天堂,我有许许多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想将之付于墨水和纸张。请在罗浮宫和胜利女神前提及我的名字。向《蒙娜丽莎》致意。向翻飞在你的头周围的灵魂致敬……爱你的兄弟向你致意问候。
纪伯伦
致艾迪勒·瓦特荪
亲爱的瓦特荪女士:
是啊,尼采是位巨人,一位响当当的巨人。你每读到他的书,就会对他增加一分爱戴。也许他在现代灵魂中是最活跃、最自由的因素。他的著述将在被我们今天认为是伟大作品的许多东西闪过之后永存于世。我希望你,我——希——望读读《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如果有空儿的话。因为在我看来,这部书是历代最伟大的作品。请近日到我这里来,让我们谈谈尼采。
纪伯伦
致女子爵西西里娅·乌夫·鲁唐伯格
女子爵:
惠书收到。信中说:
“我喜欢叙利亚,因为她美,她的美中有一种精神特质,唤起我心灵中的一种神奇的异常情感和遥远而亲切的回忆。我热爱叙利亚人,因为他们聪明,只是时运不济。但是,我憎恶这个阶级,因为它抛弃了古老的东方文明的善美,而偏向新的西方文明的丑恶;这个阶级所收纳的东西偏离了人类阶层。”
女士阁下,这的确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东方的保守主义者们听后,无不表示遗憾,只有他们之中的现代主义者能够理会,听后微微一笑。在这遗憾的痛苦与微笑的讥讽之间,今日的叙利亚处于尴尬立场,处于三岔路口,一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至于我呢,则因为看到叙利亚的旧衣服上补了一块新补丁而感到痛苦遗憾。
当我发现躯体归于一个陈旧灵魂时,我是不会因高兴而微笑的。我像一个怜悯病母的儿子那样看着叙利亚。我的祖国母亲身患传统重病。女子爵,正是传统使人像走在白日光明中的瞎子一样。正是传统使人像走在夜幕中的明眼人一样。这和两者之间的差别,无非是第一个的心“包围着黑暗”,而第二个的心灵则“被黑暗包围”。
叙利亚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是宗教首领、部落头人和旧家族的长老。宗教首领们之所以保守传统,并非由于他喜欢其纯美与质朴,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保守传统可以维护他们的权威。至于部落头人和旧家族的长老们,他们则各国的同僚们那样,天生贪婪他们的权势,拼命抗拒由马格里布传入叙利亚的新灵魂。无须抱怨他们,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盘飞在他们国家上空的那种新灵魂践踏了东方礼貌的尊严,破除了迷信,撕毁了叙利亚脸上的“光荣”面纱,扯去了叙利亚身上的尘衣。
毕业于欧洲学校的现代人,或迁移到新世界的现代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就像低等世界花园里的果子一样,有着吸引人的外表,但却受了烟尘的污染,但他们很少伤及保守主义者,原因在于他们影响微弱,影子很短,欲望也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