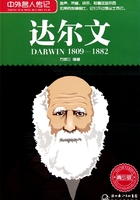在巴勒贝克责怨诗中有一首介于责斥痛骂之间的温和责怨诗;其曲既有动人心弦的“纳哈万德”风格,又含欢快的“萨巴”曲的味道,故其对灵魂所产生的作用二者兼容并包。
现在,我已写下这么多文字。我看我像个孩子,从上帝创造第一个人时天女所唱的一首长歌中抄录了一个词儿,或者像个文盲,从时代开始之前智慧之神写在感情册页上的书中,背记了一句话。
音乐,神圣的奥特里比,你的艺术姐妹往日曾手舞足蹈过一段时间,后被置入遗忘的堡垒中,而你嘲笑他们,但一天也未曾退出灵魂舞台。仿佛你是亚当第一次与夏娃亲吻的回声。回声自有回声,回声还有回声,不停流动,不住转移,包围一切,复活一切,令劳者乐意劳作,让天赋准则用听觉愉快地接受它的恩赐。
音乐,灵魂和爱情的女儿!爱情苦汁与甜浆的容器!人类心灵的幻想!悲伤之果,欢乐之花!情感花束里散发出来的香气!情侣的口舌,恋人间秘密的传送者!你能把思想与语言统一起来,你能把动人的美编制成情感。你是心灵的美酒,饮者可以升入理想世界的至高处。你是大军的鼓动队,你是崇拜者灵魂的净化者。携带着灵魂幻影的以太,慈悲、温和的大海啊,我们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你,把我们的心寄存在你的深处,请求你把我们的灵魂和心带到物质以外,让我们看看幽冥世界隐藏的一切吧!
灵魂的感情,你增殖繁衍吧!心里的情感呀,你增多生长吧!举起你的手,为这位伟大神灵建筑庙宇吧!灵感之神啊,请你降到诗人的心上,为他们的才智宝库注入对这位伟大神灵的赞美词语吧!画家、雕塑家的想象力啊,丰富,再丰富一些,提高再提高一步,为这位伟大神灵造像塑身吧!
地球上的居民们,款待这位伟大神灵的牧师、修女吧!为它的崇拜者祝贺节日,给他们建造塑像吧!众民族,顶礼膜拜吧!向奥尔甫斯、大卫和穆苏里致敬问安吧!隆重纪念贝多芬、费厄尼尔和莫扎特吧!叙利亚,请您以沙克尔·阿勒比的名义歌唱吧!埃及,请您以阿卜杜·哈穆里的名义歌唱吧!神圣的宇宙,请您大一些,再大一些,让他们的名声播撒在你的天空,让空气中充满纯美的灵魂,教人们用目看,用心听!阿门。
伊本·西那及其长诗
在古人的诗作中,没有比伊本·西那的《咏魂》长诗更接近我的信仰和我的心理爱好的作品了。
“领导长老”把最能诱惑人的东西,把与人的想象力形影不分的、由知识产生的最深刻的愿望带来的若干问题,以及只有经过连续考虑和长期观察才能总结出来的理论,都集中在这首超绝的长诗中。
伊本·西那作为当时的天才,这首长诗自他的意识中产生出来,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一个毕生钻研人体秘密和第一物质特征的人,竟有此种表现,那是足以令人称奇叫绝的。在我看来,这位“领导长老”已经通过物质道路,晓得了精神的奥秘;通过可以看见的东西,弄清了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结构。他这首长诗的诞生,清清楚楚证明了是智力的生命;知识带着自己的主人由实际经验渐渐走向唯理论,继而走向精神感情和上帝。
也许读者会在西方大诗人的作品中看到某些段落使你想起这首长诗。在莎士比亚的不朽作品中,有的意思无异于伊本·西那诗言的语句:
她不高兴地来到了你这里,
她伤心也许不忍与你分离。
席勒有类似的诗句:
盖子已经揭开,她吟着诗,
看到了睡眼看不到的东西。
歌德也有相近似的诗句:
她回来晓得了世间一切隐秘,
然而她的破衣没有缝补。
布朗亦有相似的诗句:
她像闪电,以高热放光,
尔后卷起,似没有闪亮。
但“领导长老”比这些诗人早几个世纪。他把在不同时间以断续形式降到不同思想上的东西集聚在一首诗中,这使他成为他的时代以及其后若干时代的天才,使他的这首《咏魂》长诗成为他在最优秀、最深远的题目中的最深刻、最优秀的作品。
安萨里
安萨里与圣徒奥古斯丁之间有着心理上的联系,虽然二者所处的时间与学说、社会环境各异,但却是一种学说的两个彼此相似的外貌。那种学说则是精神上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倾向,它将人一步步由可见世界及其现象引向形而上学、哲学和神学。
安萨里离群索居,抛开世间荣华、尊位,独自苦苦修行,深入探究将科学之尾与宗教之首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细线,精心观察那个隐形的容器;就在那个容器中,人们的知识、经验与人们的情感、梦想混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就是这样做的,先于安萨里五个世纪。读过他的《忏悔录》的人,都会知道他把地球及地上万物作为向最高存在核心攀登的云梯。
不过,我发现安萨里比奥古斯丁更接近与事物的本质和秘密。原因在于二者的继承之间存在着差别,即安萨里继承了先进的阿拉伯、希腊科学理论,而奥古斯丁所继承的则是公元二、三世纪教士们的神学知识。我所说的继承,是指随着日月的推移,事情由一种思想转向另一种思想,就像身体上的某些特点,从一个时代带到另一个时代,总是与人的外观形影相随。
我发现安萨里自有一种东西,使他成为连接他之前的苏菲派和其后的神学家的一个金环。过去佛教思想所达到的境界中有安萨里所倾向的东西;斯宾诺莎和威廉·布莱克的著作里含有安萨里的情感。
安萨里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心目中享有很高地位,他们把安萨里与伊本·西那、伊本·路西德并列为东方一流哲学家。他们当中的神性论学家则把安萨里看作出现在伊斯兰中最尊贵的思想家。出奇的是,我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一座十五世纪建造的教堂的墙壁上看到安萨里的画像与若干哲学家、使徒和神学家们的画像挂在一起。中世纪教堂里的主教们把画像上的那些人物当作绝对精神殿堂的顶梁巨柱。
更为出奇的是西方人对安萨里的了解竟比东方人多。西方人翻译他的著作,研究他的学说,仔细探索他的哲学倾向和苏菲派思想,而我们,我们这些仍然用阿拉伯语说话和写作的人,竟然很少有人提及或谈起安萨里。我们依旧忙于拾贝壳,仿佛贝壳就是生活大海向日夜岸边送来的一切。
乔治·泽丹
泽丹已经仙逝。泽丹的死与他的生一样伟大,和他的作品一样灿烂。
那崇高的思想长眠了。现在,静寂女神正在它的陵寝周围盘旋,示意庄重严肃,祛除痛苦啼哭。
那美好灵魂悄然离去,走向我们可感而不可及的世界。它的离去给活着的人们以启示:务必紧紧把握日夜。
那高贵的实体已从工作的劳累与艰辛中解放出来,裹着劳动荣誉的披风,走向工作超越劳累与艰辛的地方。泽丹已到眼看不见、耳听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是,既然泽丹已经登上畅游在无边大海中的车子,那么,他现在正忙于有益于那里的居民的事,埋头收集资料,惊叹历史奇妙,倾心钻研语言。
这就是泽丹——慷慨激昂的思想,唯投入工作方才惬意;如饥似渴的灵魂,只肯居于醒者肩头;宏大宽广的心胸,洋溢着慈悲与热忱之情,既然那种思想仍然以公众意识存在为存在,那么,它现在正与公众意识一道忙碌。既然那颗灵魂以知己朋友存在为存在,那么,它现在正和着上帝的火焰燃烧。
这就是泽丹的生活——一道从存在涌泻出来的甘泉,继而化为一条水流清澈见底的河,灌溉着谷地两侧的庄稼和树木。
看哪,河水已经流到海岸边,有哪位食客敢于哭或哀悼它呢?
或许泣泪和哀号与站在生命宝座前的那些人大不相宜?莫非那些人还没来得及往生命中滴洒安静额头上的一滴汗珠或心中的一滴血便匆忙离去?
整整三十个年头,泽丹不是在溶化自己的心、蒸馏自己的额头吗?我们当中谁不曾从那清澈的河水中汲取甘甜的水呢?
那么,谁想款待泽丹,就请向着他的灵魂高唱一首谢恩之歌,凭以替代悲痛的号丧吧!
谁想纪念泽丹,就请从泽丹集撰的知识宝库中取出自己那一份东西,作为遗产留给阿拉伯世界。
不要给伟大的人物什么,只管从伟人那里取拿,这就是对伟人的敬重。
无须给予泽丹以哭声与吊唁,只管从他那里拿取才智与赠礼,藉此使他永远活在人间。
阿拉伯语的前途
一
阿拉伯语的前途如何?
语言是整个民族或其总的民族性的创造现象的一种。如果创造力平息了,语言也便停下前进的脚步。停步中包含着后退,后退里包含着死亡和消逝。
那么,阿拉伯语的前途取决于操阿拉伯语的所有国家中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创造思想的前途。如果那种思想存在,那么,阿拉伯语的前途就像其过去一样光明远大;假若那种思想不存在,那么,阿拉伯语的前途就像其姊妹古叙利亚语、希伯来语的今天。
何为我们称谓的创造力?
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是前进的原动决心。创造力就是民族心中的饥和渴以及对未知一切的向往,是精神中一系列日夜渴望实现的梦想,但并非实现一端上的一个环,而是在另一端为生活增加新的一环。创造力于个人是聪明才智,于集体是热情火力;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将集体的无形倾向化为可以触摸到的东西的能力。蒙昧时期,诗人在成长壮大,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处于成长壮大情况下。古典文学时代,诗人开始分支,因为当时伊斯兰国家处于分支情况下。诗人起步、上升、变化,时而是哲学家,时而成医生,时而当天文学家,直至困神骚扰阿拉伯语中的创造力,于是进入梦乡,在睡梦里,诗人变成作诗者,哲学家变成演说家,医生变成算命先生,天文学家变成了占卜师。
如果上面的说法正确,阿拉伯语的前景将要看操阿拉伯语的所有国家的创造力。如果那些国家独具民族性或精神上团结一致,那种民族性的创造力经过久眠之后已经醒过来,那么,阿拉伯语的前途像过去一样光明远大;如若不然,情况则相反。
二
欧洲文明和西方精神会对阿拉伯语产生什么影响呢?
影响是一种形式的食粮,语言从外面将之取来吃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有益的东西化为语言的活的成分,就像一棵树那样,将阳光、空气和土的成分化为枝叶和花果。但是,如果语言没有臼齿咀嚼,没有胃进行消化,那么,食物将白白地走去,相反还会变成致命的的毒药呢。多少树木试图在阴影下生存,一旦移到太阳光下,便会凋谢死亡。有道是:有者因受赠而发财,无者因付出而更加贫困。
西方精神是人类的一个角色,是人类生活里的一个篇章。人类生活是一巨大队列,经常向前迈进。语言、政府和信念都是由飞扬在道路两侧的金色尘埃组成的。走在这个队列前头的民族是创造者;创造者是影响者。走在队列后段的民族是模仿者;模仿者是受影响者。当东方人走在前面,西方人跟在后头时,我们的文明对他们的语言产生过巨大影响。而现在呢,他们走在前面,我们变成了后跟者,自然他们的文明要对我们的语言、思想和道德有巨大影响。
不过,过去西方人吃我们烹饪的东西,经咀嚼咽入肚子,将有用的东西化为西方存在中的活的成分。而现在,东方人则吃西方人的烹饪品,倒是咽到肚子里去了,但变不成他们自己实体中的活的成分,却成了半西方的东西。这就是我所惧怕和感到烦恼的。因为这向我表明,西方时而像个臼齿已经脱落的老翁,时而又像个没长臼齿的婴孩!
西方人精神是我们的朋友,又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制服它,它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被它制服,它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向它敞开我们的心,它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把心交给它,它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从它那里得到适合于我们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灵魂置于它的状态中,它就是我们的敌人。
三
阿拉伯国家当前政治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西方和东方的作家、思想家一致认为,阿拉伯国家处于政治、行政和心理上的混乱状态中。多数人认定这种混乱将导致破坏与消亡。至于我,则要问:“这是混乱,还是萎靡不振?”
假若是萎靡不振,那么,这种萎靡是每个民族的终点、每国人民的结局——萎靡就是困倦式的临终、睡眠式的死亡。
假若真的是混乱,那么,混乱是合法的,倒常是有益的。因它表现的是隐藏在民族精神中的东西,以醒代替微醉,以苏醒代替昏迷,如同暴风决意动摇树木,并非为了将树连根拔起,而是要刮掉它的枯枝,扫去它的黄叶。假若在一个仍然处于一些原始状态的民族中出现混乱的话,那么,清楚地表明这个民族的个人身上存在创造力,整个民族在作准备。薄雾是生活教科书中的第一个词,但不是最后一个词;薄雾就是混乱的生活。
那么,政治发展的影响将把阿拉伯国家中的混乱转化为治,将把其中的含糊、复杂问题转化得条理分明、融洽协调。但是,永远不能以实体取代萎靡,以热情取代烦恼。陶瓷工人能把泥做成酒坛或醋罐,但他却不能用沙子和石头创造出什么。
四
阿拉伯语将在高等学校和非高等学校普及,并用阿拉伯语讲授一切课程吗?
不把高等学校和非高等学校办成具有纯民族性质的学校,阿拉伯语在那里就得不到普及;不把学校从慈善机构、社会集团、宗教集团手中转到地方政府手中,就不可能用阿拉伯语教授所有课程。
比如在叙利亚,教学是以施舍的形式从西方传来的。我们仍然在吞食施舍的面包,因为我们是饿得心发慌的人。那面包救活了我们;把我们救活之时,也是把我们置于死地之日。那面包救活了我们,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的所有感官,微微唤醒了我们的头脑;又将我们置于死地,因为它分裂了我们的语言,削弱了我们的团结,切断了我们的联系,疏远了我们群体之间的关系,致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了若干兴趣爱好、审美观点各不相同的小小殖民地,部分被捆在西方国家的绳子上,举着他们的旗帜,为他们的长处、尊严唱赞歌。在美国学校吃了口知识饭的青年,已经自然地变成了美国代理人;在教会学校吸了一口知识汁的青年,变成了法国大使;穿上一件俄国学校织的汗衫的青年,变成了俄国的代表……那里的学校每年都会培养出这样一批代理人、代表和大使。当前关于叙利亚政治前途上的意见分歧及不同倾向,就是上述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那些用英语学习了部分知识的人期望美国或英国监护他们的国家;那些用法语读书的人则要求法国管理他的事情;那些没有用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学习了的人,则不要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要求执行最接近于他们的知识和意识的政策。
我们靠哪个国家的费用学习而向着哪个国家的政治倾向,也许是东方人报恩思想感情的证明。但是,一边砌上一块砖,而另一边却推倒一堵墙,算是什么思想感情呢?种一株花的同时毁坏一片森林,算什么思想感情呢?使我们活一天而死一辈子,又算什么思想感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