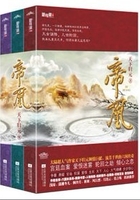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门外赫然站着那个风一般骚的胡小隆。他没有穿中午的那件很长的大衣,有点腼腆地打量了一下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我们。小弟迫不及待地喊了声大叔,然后……天雷勾动地火——他们顺利面基了。然后佩儒妹子亮出了花火大神的身份,小隆显然有印象,因为之前在QQ上交流时佩儒就以花火28强介绍过自己了,轮到培芬时梦婷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小隆就很激动地扑过去说原来你就是朱蓓啊,QQ上唯一一个给我报假名字的人。
培芬一脸尴尬地澄清,我波澜不惊的表情有点垮了。终于搞清楚名字后,小弟突然狂性大发把我压倒在床,我强烈要求换个体位遭到了她的坚决反抗。而后小隆要我们去他房间玩,看着小弟恳求的眼神,我又疲软了,不反抗地被拖走了。
在小隆房间先是看见了他女朋友天天,干净利落的中分红唇,显得很干练。后来又来了三个前辈,玩了一会儿杀人游戏,猫爹就发短信通知我召唤小弟了。
十一点多乔木请唱歌,开了两个大包,我们在109。有个眼镜男先是站在门那,狂霸酷炫拽地一言不发,显然是王若虚。不温不火的几首歌过后,王若虚就坐在里面沙发上跟翼姐他们玩起了筛子。花花和方老师深情对唱“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后来黄叔叔也加入进来,激情四射。梦婷还没喝酒已经有点燥了,小眼睛炯炯盯着我要我选首歌跟她合唱,后来她喝高了,还使劲在我耳边吹:“这个酒怎么喝也不醉。”“我感觉到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一边无奈地应她“对哎你千杯不醉”,一边看她跑到中间边唱边扭臀……唱到High处还使劲在地上蹦了几蹦。
乔木跑到我们这唱了好几遍《嫁衣》,正直深夜,凄美得带点诡异的歌,而后就一直在我耳边盘旋,盘旋。后来好像有人走了,乔木醉了砸了瓶子,碎片落到地上发出清冷的响声,她喃喃地重复“祝新概念16岁生日快乐”,然后是“怀念赵老师”。
四五点的时候大家都很累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醒着的人也没什么心思唱歌,只有音响里幽幽地响着歌曲。被佩儒压着的腿因为长时间的血液不畅微微麻木。我睁开眼,看见小正太蒋奔正靠在梦婷怀里,梦婷脸上带着有点迷蒙的神情近乎慈爱地揽着他。后来听说他俩在凌晨的上海街头手拉手散步。
五点多的上海,天空还是灰蒙蒙的,远处的灯火拼成了一片,像是湿嗒嗒的镜花水月。
我和佩儒、心韵走在回宾馆的路上,以沉默代替欲言。不想去敲415的房门把培芬吵醒,拿了心韵的钥匙倒在207埋头大睡。
Day27
早上醒来发现好混乱。由于我跟佩儒可耻地占了207心韵、梦婷的房间,心韵坐在床边打了一会儿盹然后下楼了,梦婷幽会回来发现床上惊现两只巨型未知禽兽大叫捂嘴然后拖着心韵睡了方老师房间。
下楼。离别的阴影已经显山露水,其实心里明白今日一别很多人恐怕就再不能相见了。忘了是谁先拿出本子要留言,然后很多人都神奇地掏出了本子,我什么也没带,负责给他们写。
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表达此刻的心情或者对久别重逢的期待,不想在小朋友们的本子上写下太过凝重感伤的话,然后扯过心韵的本子就写“你很有想法,跟我学做菜吧,好吧其实我就是来搞笑的”,看她扑哧一下忍俊不禁,我也变轻松了,她又依葫芦画瓢给另一个男生本子上留了这句。昨晚唱歌的后遗症来了,耳边一直萦绕着乔木唱的《嫁衣》的旋律,差点就在别人的本子上写了《嫁衣》的歌词,还跟佩儒开玩笑在谁谁本子上她写第一句“妈妈看好我的我的红嫁衣,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我写最后一句“一夜春宵不是不是我的错”,还要重复四遍。佩儒给很多人写了王菲的歌词“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深有感触,在上海没有等到落雪,无法跟你们一起感受一起颤抖有点遗憾。
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去颁奖了,因为还要坐两站地铁,所以大部队分散行动。我跟佩儒、梦婷、心韵一道往青松城去,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之涵已经在群里交代了路线……事实证明到那里真的方便快捷无压力。
我跟佩儒两个人饥肠辘辘,脱队冲进路旁的麦当劳觅食去了。在地铁站捧着可乐大口咬着汉堡像俩难民,不顾形象,我语重心长地拿我跟舍友公然在学校里游食那一套教导佩儒:反正又没人认识我们。佩儒懵懂地点点头,于是忽而有点带坏祖国花朵的罪恶感。
群里说获奖名单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我们四个胆小鬼却一致决定不去先睹为快,反正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还是等到了那里再揭开它的盖头吧,好像谁先看,这场名叫新概念的绮梦就要醒了。
还有一站时,手机亮了。
1:28pm新短信。
From猫小弟:你和暖姐是一等。快来!所以说,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事与愿违啊。
跟梦婷说我们俩是一等,她的开心压根掩不住,由里到外散发着光彩,地铁里的人就这么漠然地看着我们手舞足蹈的样子,佩儒跟心韵的脸一瞬间垮下来,因为二等。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个大Bug,小弟并不认识你们,所以自然就没提到你们,所以那个时候并不代表你们就不是一等了。而几等并不说明什么,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而已,很多出名的作者就没拿过一等人家照样牛掰啊。语言苍白无力,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她们,想到乔木在第十五届说的:所有二等在她心里都是一等,不过就是多个奖杯嘛。
我自己能说的就是,你们还年轻啊妹子们,老子当年也是千年老二啊。
出了肇家浜站,过个马路就是青松城大酒店。还是记忆中那样高大华美的样子。保安看着我们青涩的脸庞,立刻说是新概念的吗,直走上楼到劲松厅。
明明有好电梯不坐,却选择爬坏了的不动的电梯。劲松厅门口围满了人,大门紧闭。人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或喜悦,或难过,或疲惫,或振奋。
想起来第十四届拿了二等上戏也没去碰机会挫败而回,电梯里遇到一对北京来的母女,母亲一直忍不住念叨着多不公平啊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声音里夹杂着哽咽。当时拿了一等的兴高采烈去各个高校房间自招,跟其他人的暗淡形成了强烈反差。
时隔两年,收获了一等,对我来说却已经无关紧要了,靠文化成绩上了大学,读着一个与文字沾边却并不喜欢的专业,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新概念走出去的其他人那样在文学这条路上渐行渐远,我们沮丧难过却又无力挣扎。去年,第十五届后不久,赵老师就去世了。细碎的感伤就在那么一瞬击倒了我,以至小弟找到我时问我怎么一言不发很累的样子。
快2点的时候名单就正式张贴在布告栏上。即使微博上早就公布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挤过去,或许在期待一个奇迹。于是那个男编辑大声说微博上我们也有公布。
第十四届的时候有参赛者代表讲话,主编发言,还清楚地记得赵长天老师还是李其纲老师说这届的稿子整体水平不如往年,然后开始念名单,所有人屏住呼吸时刻准备着迎接自己的名字,报到有些大神的名字时人群中会发出一阵欢呼。第十五届,作为一个比较具有非凡意义的庆典,郭敬明张悦然还有很多从新概念走出去的人都来了。而第十六届,有的只是一二等分开领下证书奖杯,然后就可以走了,美其名曰响应习总号召简化程序,也或许真的就是离过年就3天了,让偏远地区参赛者可以早点赶回家。后来才知道居然有几个人连二等都没有,问编辑只是说没找到名字就是没有奖。
当当和启迪也走到我们身边,恭喜我跟梦婷拿的一等,又认识了启迪的徐州老乡汤斌,某位断断续续参加新概念,第十二届时候b组的牛人。大家的最后一句话好像都是明年见,第十七届见,丢丢说做梦梦到第十六届就是最后一届了,以后再没有新概念了,于是大家就都沉默了,片刻后又纷纷表示自己会撑下去一定会有下一届的。
小弟说她明年不参加了,要跟我一起参加第二十届,那时候我们都是C组的怪阿姨了,我说去你的我明年还想参加b组呢谁跟你第二十届见啊。
但愿新概念也只是累了,它暂时地休整一下,然后还能向赵老师当年提出的要求“三新”一样,一届又一届地办下去,生生不息。人们还将从天南地北赶来,欢聚在一起,然后等待下一次久别重逢后的狂欢。
小隆来了,小弟闻风举着留言本子蹿过去,然后小隆就趴在某男生后背写:愿你美好如往昔。只能说字很丑,留的人很有勇气。我纸跟笔都没带,却有点蠢蠢欲动,分别的日子里偶尔翻翻这些留言感觉多好啊,就撕了小弟本子一张纸递给了小隆。要是被我这么一张张撕下去她的本子就告急了,于是我无耻地顺走了小弟一包薰衣草主题的明信片,大肆散播去了。
黄叔叔写得让我很有共鸣:新概念之于我是一场盛宴,我自倾杯,君且随意。梦婷跟别人一起去自招了,我和佩儒就仿照丢丢、姜羽桐那样倚着墙壁坐下来等她。朱磊指着个脸上有点肉肉的男生说是阿青,抱着仰望大神的心情又派发了一张明信片,阿青以为要寄给我,还准备写上邮编,后来看朱磊直接给我了,就没写。朱磊介绍我就是跟他同乡的朱蓓,阿青说听起来像兄妹,之前启迪也说朱蓓朱磊,她有个同学叫朱蓓蕾,我忍俊不禁。
许久梦婷跑过来说厦大门口排好长的队还没轮到她,把包往我旁边一丢,朱磊从身边经过,把外套也扔在上面。潘云贵大神来了,求了签名,他人真的很好,声音轻柔温和,像春天的气息,把每个人的名字都问清楚,然后签名留言的颜色好炫金闪闪的,就是一直没有摘下口罩让我们一睹芳容。乔木坐到我们对面,她睡迷了到了两点多才醒匆匆赶来。
等了好久我跟佩儒都累了就准备回宾馆。在售票机那遇到了黄叔叔跟另一个妹子,我跟佩儒说跟着他俩走就行了。我们跟了一路,在到1号出口不远处脱队及时拐进了2号久光百货。后来发现脱队的下场是凄惨的,1号出口因为我们抛弃它自此跟我们结了梁子,不过这是下文了。
我们在久光负一层逛进口食品,两个女屌丝只能看看吃的,穿的用的太“高大上”了用不起,只有佩儒妹子还一直跟我说等会逛完吃的上二楼三楼看看买点纪念品,我一笑而过。看到了很大只的大白兔奶糖,包装就只是个大大的糖果形状,萌得我一脸血,跟佩儒一人手里拿一个,乐呵呵的比傻逼更傻逼。然后又抄了香槟松露巧克力,明治的糖,佩儒土豪都是成双成对地拿,让我望尘莫及。培芬突然发消息问我把梦婷包放哪里了,我说还在原来她放包的地方。后来雨汀又打电话过来问,我跟佩儒感觉不对,就匆匆结账回去了。
开了207房间,梦婷打来,还是问包的事,电话里她的声音惊慌并带了哭腔。我的心顿时沉下来,梦婷敲门进来。她哭着伏在床上,说这么大的人了还没法照顾好自己弄丢了包早知道就不该来上海不要这个一等奖之类的赌气话。我们才知道她在厦大门口排了好久轮到她却被一句高三才有资格打发,上楼包却不见了,问了最后离开的人,说在电梯快要关门的时候远远地对着工作人员喊了一句把包放在前台等人拿,也不知道听没听见。我听着她边哭边零碎地说些包肯定找不回来了,那里面有她所有的东西,心里闷闷的很难过。只好一个劲地劝她不要哭了,然后拉着佩儒回去帮她找包。
到了地铁站发现我特别不在状态,心里还记挂着梦婷,害怕找不到包,领着佩儒走下去又上来发现到了原地就再下去,两个来回,地铁才载着我们来到青松城。天早已黑了,上海是个灯火通明的美人。我跟佩儒都饿了,逛了两小时吃的却忘了吃饭,同时在小吃摊门口停住了脚步。热腾腾的香豆腐和烤肠,顿时感觉被治愈了,我笑着对佩儒说。在一楼跟英俊的前台小哥说了下来意,小哥打了个电话,事情就这么神奇地被解决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通用称谓)把包送下来,拖着沉甸甸的包,感觉整个人都变好了。
终于回到了静安寺站,却怎么也找不到1号出口,傲娇的1号出口调皮地跟我们玩起了躲猫猫,好吧其实是我大脑短路了。
跟佩儒上上下下起码三回,又反复问了我自岿然不动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作人员两次,他们冷漠并稍显不耐烦地指了指方向,最后我们实在没力气了随便找个出口出来,车如流水马如龙,外面又是另一个世界,完全陌生的世界了,不变的是上海迷离的灯火,闪闪发光。问了个大叔得到通向静安寺的正确方向,在路上遇到了买蛋糕的启迪和梦婷。梦婷的心情已经平复,连声向我们道谢,双马尾妹子,愿你越来越好,不要轻易被挫折打倒。
人走得差不多了,少了好些通宵欢腾的孩子,海友多了几分冷清萧条。在楼下玩了几局杀人游戏,这是大家在一起最后的时光了,佩儒禁不住劝也加入了。
抽到了两局平民,发言时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然后在投票表决时死命地坑旁边的佩儒不断投她,后来发现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可真相是她比我这个万年平民还要平民。第三局抽到了杀手,整个人都不好了,而这些愚蠢的人类居然通过笑没笑就肯定了我的杀手身份,我真是弱爆了。惩罚是一口气喝三杯水,拿杯子接水的时候很流弊地想到没规定必须倒满啊,就端着三个水位高度呈等差数列的杯子回去,被夸机智了好开心,我干杯你们随意。
十点半的时候佩儒收拾东西走了,这个后来几乎一直相互陪伴的姑娘,原谅我尽管很不舍却忘了拥抱,最后还是被乔木先亲左脸颊后右脸颊最后夺走了初吻。
不玩游戏了,就坐在大厅里聊天,超哥说他一直参加了六年,明年你们来吧我就不一定了。快一点的时候爸妈开车来了,于是起身告别,乔木要跟我拥抱,认识她三年了,这似乎还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我回抱住了她。超哥提议说我们都来抱一下吧,然后是嘉伟、康明,当当最后有点羞涩地走上来,说我们也来抱一下。
再见啦。
第十三个星座回去的路上,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那些人,那些风景,想了好多。想起了第十四届时候,跟我妈还有姨妈三个人初次来到这座城市,学着别的家长买了一堆泡面打发早中晚;想起那时候的乔木,米白的风衣,夹着一支烟,笑容清澈;想起了刚来时在浦江之星大厅跟乔木的第一次对视;想起了大厅里各就各位的人们在我到来时一起注视我猜我是谁时的忐忑与慌乱;想起了拿了二等匆匆离开的失落;想起了汽车疾驰而过离开上海时我默默对自己说明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