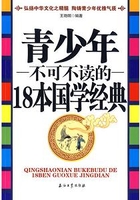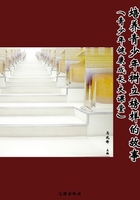李永富与两匪从后山崖溜走,穿竹林荒径来到一片乱树林边,下去与大队人马汇合,老远见康寨主渐被百十个苗人围拢,不明白康寨主为何原地不动?而他的石弹在几十支火枪弓箭面前此时显得那么微弱,片刻连石弹也不发了。又见斜对坡林边四虎黄少伯、双钩二虎几同伙拼命逃跑,后面再无他人,叫了声“坏了!”拔腿就跑。这个想依仗匪威出人头地的怕死鬼到因怕死逃得性命,那个康寨主不知什么前世恶果成熟丢了命,该死的李永富、黄少伯反倒时候未到。
李永富想想康寨主完了,自已还有什么光景?回天仓山家他不是没想到。但家的情景在脑海一出现就觉得寡淡味,没劲头没意思,一会儿也呆不住。还是依靠残存的麻口山。
三天后,黄少伯先到麻口山,见李永富三人姗姗而归,倒没责怪。能回来就好嘛!怎么责怪呢?鸭子莫说扁嘴,老鸹跳到猪背上—一样的黑。
黄少伯回了巢,天仓山李家还在盼家人归来。
“他爹,”葛氏说,“快半月了,福娃他们还没影子,信也该送到了。”李春玉说:“按理说是啊!”日添一日忧虑添一重,翘首以望,却望来了一个牵线搭桥的媒人。
韩清风自回家后,左思右量,怕夜长梦多,永兴娃身边活生生有个非常的百鹊喳来叫去,得不知啥时就叫没了福娃的魂?决定先下手为强。但自古只兴藤缠树,女方主动有违礼教失体面,如何两全其美?想来想去觉得替李家代请媒人,站在李家立场说话,这样就显得体面了。于是韩清风对媒人培训了一番。
“河妹,该给你定个亲事了,”韩清风抽着短烟杆,一脸正经地说。
“爹,哪儿的?”河妹问。
“嗯……下河陈乡长家。不错吧?”
“那把爹你嫁给他家吧!”河妹甩头、翘嘴、哼一声。
“呵呵,”韩清风正色的表情变笑脸,“爹逗你的,还不晓得你的心事?李家福娃!”
“不嫌羞!”河妹甩头、翘嘴、哼一声。但性质变了,因为她抿笑着跑开了。
媒人是个中年男人。来到天仓山,见面就是乐呵呵地,直来爽去,开门见山:“呵呵呵呵,听说你家出了个神人,我来看看!恁门好的娃儿,应该订个好亲事嘛,凤凰配凤凰,跳蚤配臭虫,这事包在我身上!”李春玉则不慌不忙,招呼请坐、上茶后才接上话题。
“福娃子的事,承你看得起,”李春玉客气地道,“看看有无合适的。”
“有哇,依我看,你干亲家韩财主那女子河妹,就是配你娃的凤凰,干脆把干亲家转正为亲家,我有把握撮合!”媒人经过韩清风培训及格,会说话。李春玉心中笑笑,也不点破,道:“只是我们劳动人家,怕河妹吃不了那苦,再说彩礼重了吧我背不起,轻了吧不像话。”
“这个嘛,我去跟韩家说,财短义长,我相信韩家有眼光。”
“那就劳慰了,”李春玉说,“只是他哥永山娃还没定到亲,不合规矩。”媒人摇摇头:“钥匙是人配的,婆娘是人睡的,规矩是人定的,河道是水改的,方圆是人画的,担心啥?”
长辈谈话后辈是不能在场的,李春玉笑了,道:“你是黄巴笼(黄莺)的嘴,不愧是说家子。”
媒人走了,永兴三少年回来了。“恁么地这久才回来?”
三少年你一言我一语,总算大致叙说清了故事,李家人惊得出了一身后怕的冷汗。
全家团圆,李春玉终于有机会,这回也不得不捅破河妹与永兴之间的那张纸。
“你喜不喜欢,”李春玉笑眯眯地,似乎明知故问道,“虽然儿女亲事自古都是父母之言,媒说之命,但我也要你亲口表个态!”
永兴只是笑笑,但却脸红。
葛氏以过来人经验略归羞涩地嗔怪道:“你还多说啥,还看不出来?”李春玉故意地问道:“全家是不是都喜欢河妹呀?”
姐姐、二嫂都高兴,李永山是哑巴亲嘴—没话说。百鹊一脸怅然。“嗨嘿呀呀!福娃哥,等你婚了,给我也找一个!”百鹊被逗笑了,全家笑了。李春玉说:“文人吃汤圆—一个一个地来!”
福娃定亲了,算是娃娃亲。河妹做梦都笑了,叫声“小干哥!”
“死女子,看把你兴得!”河妹娘读懂了河妹的梦,并非黄粱美梦,是真的。母女己常单独同床。
韩财主果然仗义,怕李家拿不起彩礼,倒添彩礼送去李家,然后李家又以自巳的名义送去韩家,都有了面子。但提出了个条件:能不能带上两姊妹,只表演不对打。这可使李春玉为难了,满足亲家的虚荣心、壮韩家声势吧,石牛身负官家命案,藏都藏不及,还抛头露面?百鹊虽有命案,性质不同。也罢,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定亲的日子,韩家乡人多多,三少年武艺的随便表演,无异于广告,在乡人惊奇得张目结舌的口风中公开飘扬。趁宴席未开,三少年手拉手欲溜去河边玩耍。河妹倒也不以为意,追身说:“福娃哥哥,我也跟你们去耍!”她己改口称“福娃哥哥”了。“嗨嘿呀呀!嗨嘿呀呀!”三人被石牛带动了步伐节拍,一路而去。乡人惊叹这几个“四小无猜”的娃娃,不但不说三道四,反而羡慕起来,惭愧于他们的循规蹈矩。
初夏的河水还不大适合游泳。百鹊、石牛闹腾着练抓蝇子,蹦跳着石牛就想下水,但碍于姑娘在场不便脱裤子,永兴是旱鸭子,哗哗地河水撩拨少年情怀。
“牛弟,”永兴说:“以后你教我凫水,我教会你写字!”石牛叫道:“沙坝上写字—抹了又来!这不现成的吗?”百鹊欢道:“好哎好哎!”于是,少年们就在河边沙滩地玩起沙坝写字来,河妹教百鹊。
石牛写的字老是东倒西歪,叫道:“写字比练武艺还难整,我们还是要长期练武,别荒了田地长了草!”
百鹊毫不假思索地随口而出:“裤裆里冒烟—裆燃!(当然)”此谚子一出,待反应过来,石牛、永兴笑得一屁股仰面跌倒在沙地上,河妹刷地红了脸,百鹊终于脸红了。
前仰后合笑够了,永兴说:“我给爹说说,尽量每天早晨莫给我们安排活儿,给我们时间练习。”
下午李家人回山上。
“福娃啊,百鹊两姊妹,你们常来耍哟!”临走时,韩家上下人等怀着敬慕的心情送行。河妹上前给永兴说了句悄悄话,转身跑回。永兴笑了,笑得很甜。
古老封建的中国,封闭落后的山里,四川填陕西,居住分散,这湾一户那梁一家,自古人类趋居河边,越向山顶人烟越少,似乎只是生命本能的延续,有什么乐趣呢?人们相互往来走动走动,便是种新鲜,或红白喜丧事,便是最热闹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