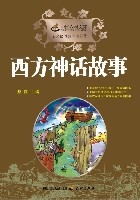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去北京待了两天,回来的第二天又去访谈。寒暄过后,看到书桌上有一封公函,问是什么事,推过让我看。是太原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办公室合署的信件,说本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将在进山中学等地,举办纪念赵宗复同志(一九一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乔亚、刘鑫、梁维书等同志的座谈会,请张老参加。
对赵宗复这个人,我还是大体了解的。一九六五年来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赵宗复是赵戴文的儿子。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就听说跳楼自杀了。当时以为定然不小了,看请柬上写的,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这么说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
再看桌上,还有张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的底稿。见我看,张先生笑笑说,这是他们让我为赵宗复写篇祭文,说是上兰村窦大夫祠旁边的赵公馆恢复旧貌,里面要建赵宗复的墓和碑,到时候要用。座谈会去不了,能为赵先生写篇祭文也算是尽了心了。
上兰村的赵公馆我去过,后面的花园里,有重修的赵戴文的墓和碑,这么说是要在他父亲墓的旁边,再为他建墓树碑了。
我发现了张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诀窍。先搭架子,再细细填充。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已写好了,下面有两句,知道要写什么,句子没有组织好,就画了许多“□”代替。后面还有几段也大体写好了,其中也有“□”代之的字句。最后一句是“伏维尚飨”。想自己平日写文章,总是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办法,从头开始,哪儿写不下去了,硬往过冲,而不知转圜之妙。空下来,往前写,最后回过身来,再收拾这些“钉子户”,才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好办法。是得学着点。
提起赵宗复,张先生就从赵宗复说起——
日本人投降了,回到太原,年轻人的热情都很高,觉得国家复兴了,遇上了好时代,自己也要做大事。在山里憋了七八年,浑身的力气使不完,这下子可找到了施展的大舞台。对我们这些还有点文化,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最爱做的就是办刊物。在晋西山里,你写得再好,也没地方发表,回到太原可就不一样了。别看年纪不大,毕竟是凯旋之师,是收复者也是征服者,日伪那一摊子全成了自己的,手里大小都有一些权力,办个刊物根本不算一回事儿。
赵宗复当时做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办了个刊物,不厚,就那么薄薄的一小本,叫《学习》。他也不知听谁说的,我爱写文章,约我给他的刊物写一篇。那几年,我最爱看鲁迅的文章,就写了一篇,叫《如果我做了皇帝》。文章里说,假如我做了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把金銮殿刷成白色,因为二战胜利了,正时兴白色的宫殿,美国的叫白宫,英国的叫白金汉宫;第二件事是,在家打牌也得收税,因为现在一切横征暴敛,都有了堂皇的名义,打牌经手金钱,当然应课之以税。通篇都是讽刺当时社会现象的。写完给赵宗复的时候,用的是本名。过后赵给我来电话,说还是改个名字吧,我说你改吧,他就给改了个名字叫仲韬。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想来是他认识张帆,跟张帆是朋友,知道我是张帆的弟弟,就用了个“仲”字,韬嘛,韬晦的意思。真没想到,我那样写,他就那样发了。
文章登出后,赵宗复觉得好,到家里看望,鼓励我继续写。
那时我住在东缉虎营一个院子里,前面两间住的是薛博民,后面两间住的是我一家人。那时我大儿子纪林还没出生,家里就我跟雨湖夫人两口。我不是跟着随部工作团第一批回到太原的吗?安定下来,租下房子,就去孝义把雨湖夫人接了过来。
刚租下房子,还没买下床,雨湖夫人来了,我们就在地上睡。她没见过电灯,很是奇怪,怎么墙上那么个黑黑的小疙瘩,按一下那个玻璃泡泡就亮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怎么也想不明白。别说她了,就是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我只上过小学,没上过中学。当然我走南闯北,经见得多,见惯就不怪了。
赵宗复来了,也没有好招待的,那时我抽烟,敬上一支纸烟,就是太原西北卷烟厂出的“顺风”牌。点着得赶紧吸,慢点就有灭的可能。宗复只顾跟我说话,不知怎么一下就灭了,只得再点。宗复笑笑说,顺风顺风,顺风而灭。
韩:说说你刚回到太原的情况。
张:随部工作团是个临时机构,光复之后就改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太原分会,主任是智力展。听起来官不大,实际权力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太原市委书记,当然不能这样类比。工商业不管,宣传舆论全管。主任之下有分工,我是宣训特派员,一听就知道是管什么的了。有这个权力,就办了一份报纸,叫《青年导报》,周报,一周一张;又办了个杂志,叫《工作与学习》,半月刊。这一报一刊的社长,都是智力展,他平常忙于政务,不怎么管事儿,主要由我负责,就是总编辑和主编了。正式发行,已是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
当时的社会风气,跟过去不一样。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还在重庆,许多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更进步的提出,国民党应当还政于民。我们市分会里,有许多进步青年,跟我住一个院子的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意思是负责发动民众运动的。还有一个叫张致中的,是组织特派员。有一次,我们几个跟智力展谈起时局,说是二战胜利了,国内局势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一党专政肯定搞不下去。不知谁当场说,像梁化之搞的这一套,迟早要被历史唾弃的。智力展说,梁化之还是革命的,对时局负责的。智走后,我们都说,梁化之怎么会革命呢?根本不可能。
一九四六年春天,杜任之随山西大学回到太原,山西大学又在侯家巷原校址复了课。一天我去杜任之家里看望这位老上级,说了我办报办刊的情况。杜说,这很好,要利用这个阵地,办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有了杜任之这话,心里就有了底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韩:赵宗复好像当过进山中学的校长。
张:他是赵戴文的公子,阎锡山对他还是器重的。光复回到太原,年底还是第二年初,赵宗复就当了进山中学的校长。对我办报纸,办杂志,都是完全支持的。还介绍了几个人来我这儿工作,全是进山中学“投枪社”的学生,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是在校生。记得里头有个叫刘文瑞的,后来叛变了,最积极的是翟凤仙,是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这也是我在报社实行的新办法,发展通讯员,分两级,一级是普通的,一级是特邀的。关系最近的,最进步的,当特邀通讯员,发给证件,标明第几号,都有记录。拿上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证件,出去采访是很荣耀的。有个叫卫兴华的,是我们的第一号通讯员,解放后有人说是特务,我给写了证明说不是,后来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省文联的张万一你知道吧?
韩:知道,是个戏剧家,前些年开会时见过。
张:翟凤仙就是张万一的夫人。前些日子,我还见过她。这次组织纪念赵宗复的活动,她是主力,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学生时代的精神。
我办《青年导报》,还是受限制的。那时年轻,有股子莽撞劲儿,想登的东西不能登,不想登的东西偏要叫你登,心里很憋屈。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胡宗南指挥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洛川、宜川分两路直取延安。十九日延安叫占领了,太原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各主要报纸都出了号外,《青年导报》没出。智力展问我为什么不出,我说,还不到时间。见我态度不好,也没再说什么。
到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智力展当了国大代表,对报社和杂志的管束就更严了。我们之间也不像以前那样协调了。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有次特种警宪指挥部的人抓了他,我问智力展是为什么,智说他也不知道。这事我就对他有意见,薛博民是跟着他一起在晋西的老朋友,老部下,薛出事了,怎么就不打听打听。现在想来,我也许太年轻了,智力展那样回答,说不定是一种韬晦之计,对我说不知道,可能暗地里正在进行营救。后来薛博民果然出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老薛说,他听说特务要破坏一个机构,是个点心铺,去通报消息,后来这个机构还是叫破获了,被捕的人招出了他,把他牵连进去,所幸案子不重,也没动刑,关了几天就放了。
在报社干了一段时间,觉得限制太多,不想干了。
一次小聚会,就我和杜任之、赵宗复三四个人,我对他俩说,这个营生干不下去了,报纸上要称共产党为“共匪”,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俩也觉得我在智力展那儿再干去,不会有什么名堂,不如早早退出。正好阎统区搞“三自传训”,公务人员都要参加,身体上受管束,精神上受折磨,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做这种事的。又去找杜任之和赵宗复想办法,他俩说,那你就去省议会王怀明那儿吧。
当时王怀明是省议会的会长,省议会是民主性质的机关,不搞三自传训那一套的。不必提杜任之了,光有赵宗复的面子,王怀明也会给这个人情的。没多久,我就辞了《青年导报》的职务,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去省议会当了秘书。《学习与工作》杂志,在此之前就停办了。“文革”后王怀明回到山西,我也参加了接待,就是因为我与他有这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