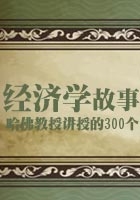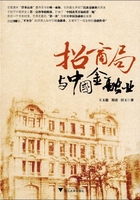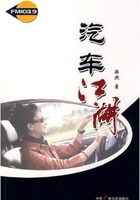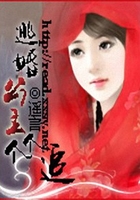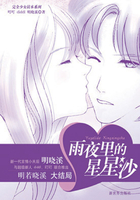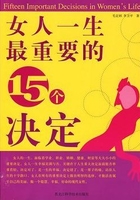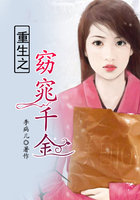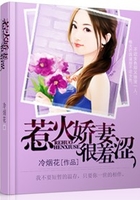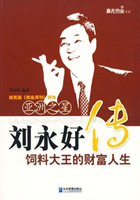当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都设有证券部门,从事证券业务。相当一部分银行资金违规进入了房地产、证券等高风险市场。一些金融机构甚至创办、联办经济实体,以银行办公司的优势,收取高额利息。那时,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
混业经营被认为是滋生违规操作的“暗箱”。回头来看,当时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能力和监管层的监管能力均不强,分业经营放得过宽,“防火墙”太低,风险自然很大,监管层“先治乱”的思路是及时正确的。
由此,“分业经营”的杀手锏被祭出——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明确提出,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
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被分成了三家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被分出,并入中国人寿,自身改组为专营财产险业务的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即现在的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剩下的中国平安,成为了一颗拔不掉的萝卜。
事实上,中国平安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产险、寿险在经营上的分开,但此次分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产、寿资产分离;此外原有平安信托、平安证券的股权安排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和诸多法律问题。中国平安和监管层的分歧在于,具体采用何种形式分业。
按监管思路,产、寿险及其他各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意味着产、寿险公司完全没有股权关系。但中国平安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初级或过渡模式,会导致经营主体规模小,成本高、竞争力弱、服务单一,偿付能力低,风险监控能力弱等问题。
中国平安向监管层上报的方案是集团控股模式,即由一个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产、寿公司和投资子公司,由集团控股公司对业务、财务、投资、人事、计划和风险内控等重大决策进行统一管理的分业模式。
具体来说,即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以投资人的身份控股99%设立平安财险、平安寿险,并控股平安信托,平安信托则持有平安证券股份。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与下属各专业子公司均为企业法人。分业后,集团公司以股权为纽带,通过委派董事组成董事会对专业子公司实施领导、监督和管理。
1998年中国平安全国工作会议上,马明哲在“平安第二个十年远景和战略”的主题讲话中,连提了四个问题: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应走哪条路?我们如何到达?
问毕,“国际一流的综合性服务集团”几个大字赫然跃入听者眼帘。
不听话的中国平安连续数年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被“点名”。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回忆,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几年,监管部门在会上做新一年度工作安排时,都会有一段“某某完成分业经营”的句子,这“某某”就是中国平安。因为中国平安年年都完不成,所以年年“被计划”。
即便如此,马明哲也非常坚决,“没有第二条路走”,除了产、寿险两项主营,想要的其他金融牌照决不撒手。
马明哲的策略就是“拖”。按孙建一的说法,“如果监管部门不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批,我们就一直拖”。
但“拖”的成本很高。
马明哲求见监管部门的领导,碰到“只谈五分钟”就遭拒的尴尬;监管部门甚至明确表示,分业未完成前,不审批中国平安新的分支机构。这对中国平安来说代价甚重——那时,铺设分支机构是各保险公司攻城略地、抢占市场最有效的方式,一旦挖掘新据点,市场规模一日千里;死守几座山头不动,等于倒退。
公司管理团队和中层干部开始有人动摇。
“你成天在外磕头作揖,为了和一个(监管部门)领导说上几句,几个小时站在街上等人家,值不值?”有领导班子成员替马明哲抱不平。马明哲的表态则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我宁愿给人下跪!”
在中国平安一次次的尝试中,原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中国平安的嘱托——“平安要‘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渐渐成为平安高管对外的口头禅。
创新敢为的蛇口精神,再度支撑着平安人走出困难岁月。“如果平安不能走出第二条路来,那还不如当初就不要成立平安,让人保多开几家分支机构。”孙建一说。
全球金融业模式的发展趋势,印证了马明哲最初的判断。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法律上确立混业经营模式。
那时在国内,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面临着海外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于是,一场“混业还是分业”的讨论在国内掀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活动。监管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思路,从“管制”向“促进发展”悄然转变。
2001年12月7日,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业经营改革的通知》,确定了中国平安按保险集团模式进行分业改革——同意股份公司更名为集团公司,并以股权为纽带对其他独立法人的子公司进行管理。
“业务分开,股权不分”——这与老中国人保的“分业”截然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平安坚守七年的分业方案经多次修改和完善,核心内容终于获得监管层的肯定。一家“特殊”保险集团公司由此正式获得官方认可,马明哲深深地舒了口气。
2002年4月2日,保监会批准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业经营实施方案》,中国平安的分业构想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中国平安是国内最后一家完成分业经营的保险公司,亦是继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后国内第三家金融控股集团。
倔强的马明哲用八年时间跑完一场马拉松,已创造了中国保险业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不过,怀揣批文冲过终点线的他,来不及止步欢呼,因为这场规模空前的中国平安大手术还远未完结。
登陆资本市场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抱负和追求。”在马明哲的记忆中,从湛江调到蛇口工作后另一次增长见识的经历是在1989年。作为平安保险经理的他前往美国,参加了一次保险业短期课程。
“在纽约,我第一次听说了摩根士丹利、高盛的厉害,大开眼界。”培训归来,“师夷长技”的念头已在他的心中植下。
平安保险成立初期,马明哲就萌生过海外上市的念头。上市前,中国平安大致经历了三次资本扩张。
1989年9月,平安保险首次增资扩股,引入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深圳市财政局、平安员工合股基金等新股东。
此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摩根士丹利、高盛两大国际财团于1994年6月参股中国平安,取得13.7%股份。中国平安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随后,中国平安在国内以每股6元的价格进行私募,完成后股东激增至70余家。
由此,第一轮资本扩张完成,中国平安注册资本金由成立之初的4200万元猛增至15亿元。
第二次资本扩张始于1997年。经银监会(银复[1997]146号)批准,中国平安总股本由15亿股增至25亿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继续增持至各持7.63%。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虽仍是中国平安的第一大股东,但持股量已由17.79%稀释至17.09%。此轮增资完成后,中国平安注册资本增至22.2亿元。
第三轮增资——2002年引入汇丰保险集团——最引人注目。是年10月,汇丰保险集团出资6亿美元,认购中国平安增发的2.47亿股外资股股份,以10%的持股比例跃为平安第二大股东,其资本金增至24.7亿元。
这一举动令市场哗然——中国平安当时每股净资产仅为3.2元人民币左右,汇丰参股价已超过了这一价格的6倍!不过,“10%的持股比例,汇丰还是嫌少。”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说,当时汇丰选择的是政策上限。
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双赢的选择。
汇丰的引入,既奠定了此后近10年中国平安业务发展的基石,也成为中国平安上市的幕后推手之一;而迅猛发展的中国平安之于汇丰,不仅带来了丰厚的股息账面收益,更解决了汇丰在国内扩展业务的网络问题。2005年,汇丰再度以每股13.2港元的价格,斥资81.04亿港元,从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手中购入两者持有9.91%的股权,持股比例跃至19.9%上限,成为中国平安第一大股东。经过10送10的股本扩张,中国平安总股本接近50亿股,汇丰的持股成本也折至10港元左右。
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2318,融资143.37亿港元。虽然中国平安上市晚于中国人保财险(2003年11月6日)和中国人寿(2003年12月18日),但其仍在当时创造了众多“第一”: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股票发行,亚洲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2002年以来仅在香港一地上市的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
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回归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创有史以来全球保险公司最大IPO和当时中国A股市场第二大IPO纪录。
两次上市路演中,中国平安向机构投资者叫卖的亮点,都包括来自麦肯锡、摩根士丹利、高盛、汇丰的国际化标准,以及“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综合金融集团的本土化优势。这显然和原大股东招商局开放与创新的理念一脉相承,更是数年前中国平安的寿险实验与外脑创新的沉淀。
马氏创新
寿险萌动:打倒友邦
1992年7月马明哲的台湾之行,让寿险进入中国平安的发展视野。
台湾国泰人寿——当地最大的寿险公司,与富邦产物保险同是蔡氏兄弟的家族企业,一样发展30年,并在各自领域担当领头羊。但国泰人寿的资产指标超出富邦一个数量级。台湾归来,马明哲迅速将业务向寿险倾斜。通过走访和研究,中国平安的寿险队伍很快上马。
同年,上海滩保险市场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催化了中国平安加码寿险业务的进程。
这一年,中国保险市场正式对外资开放。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子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AIA)重回中国市场。即便是到今天,美国友邦保险在中国的外资独资寿险牌照,也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美国友邦保险以破竹之势席卷上海滩。按那时媒体的报道,1992年11月,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徐正广开始了他中国内地的寿险理念第一课,三天后,第一批寿险代理人(上海人称为“跑街先生”和“跑街小姐”)出现在上海大街小巷。
友邦咄咄逼人的态势,让国内保险公司措手不及。
其一,上海本土寿险势单力薄,谈何反攻。
其二,中国人保、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均以产险起家,重产轻寿,与“寿险重产险”的国际趋势不符,面对以友邦为代表的国际化冲击,不堪一击。
其三,也是最致命的,友邦的杀手锏“寿险个人营销体制”,多数公司从未听闻。那时内地的保险公司,一无代理人,二无完善的个人寿险,寿险业务只靠一些微利团险业务维持。
但马明哲毅然决定迎战。在中资公司中率先看到寿险的重要性,并将上海定位为国内最具开发价值的寿险市场——在这两个关键点上的判断,为中国平安赢取挑战中国人保等大型公司埋下伏笔。
中国平安将1993年设为“人寿险年”,1994年6月,马明哲聘请了台湾中兴人寿副总经理黄宜庚担任顾问(2003年1月曾任平安人寿总经理),并引入郑舜文、董秉琨等富有市场经验的台湾保险经理人,在中国平安内部推广台湾的寿险营销模式。
1994年7月,黄宜庚在中国平安启动寿险营销培训班。第一天听众屈指可数,第二天需要撤掉隔小空间的屏风,第三天听众已挤到走廊。黄宜庚当时大胆预测:“三年后,大陆寿险业务将会超过产险,到2000年,大陆寿险的保费会达到1000亿元左右。”
在当时,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除了马明哲,多数人肚子都笑疼了。不过,此后市场的发展,一一验证了这位“黄大师”的预言。
中国平安即是鲜活一例。寿险大跃进启动后,中国平安保费收入即从1993年的5.5亿元,猛增到1996年的97.1亿元,其中寿险业务高达71.9亿元,占比74%。
1995年年初,中国平安与台湾国华人寿签订合作协议,国华人寿以营销顾问的形式协助中国平安进行寿险业务建设。2000年,平安还曾推出“龙腾计划”,邀集台湾500名平均经验达8年以上的保险销售经理西进。马明哲将他们布阵至中国平安2800个营业部,先进理念被播撒到各分支机构。
寿险营销体制拓荒上,中国平安创造了国内多项第一。1994年中国平安寿险体制改革实施动员大会上,中国寿险业第一个个人营销体制章程发布,中国第一批个人寿险营销团队成立。1994年7月31日,中国专业寿险公司承保的中国大陆第一张个人寿险保单在中国平安深圳诞生。
正面交锋同时进行着。1994年,马明哲调遣精兵强将抵沪,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正式进入上海市场。彼时,友邦已在上海展业一年多,业务员1800多人,保费收入逾亿元。
在第一任分公司经理何志光的带领下,中国平安上海业务突飞猛进,于1995年先于其他中资公司完成产寿分设。寿险保费收入从2.7亿元跃至9.5亿元,市场占有率达33%。1996年10月,中国平安内部数据显示,他们已将友邦甩在了身后。
由于在上海的展业、代理人机制设立与产寿分业都先人一步,到1999年末,平安人寿保费收入近34亿元,占比42%,首次超过中国人寿的30亿元与37%,成为上海寿险业霸主。排在后面的分别是,美国友邦保险约10亿元,占比12%;太平洋人寿6亿元,占比7%;中宏保险8000多万元,占比1%;太平洋安泰人寿约3000万元,占比0.4%。
国际化:引资与引智
在众多民族保险企业中,中国平安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一方面,它不为条条框框所桎梏,敢为人先,叛逆,勇于试错,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激进分子”;另一方面,它的包容并蓄、诚信务实与总部位于香港的大股东招商局一脉相承,根植于南方,放眼全球,率先实现资本、人才、管理国际化,是国内为数不多较早接受国际标准检验的中资企业。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将平安集团的特色概括为:国际化标准、本土化优势。
中国平安聘用海外人才始于1995年。当时,中国平安提出,人才国际化是中国平安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胆引进国际一流的专业和管理人才,发挥其作用。
实际上,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不拘一格降人才与借脑的思路,最早为袁庚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