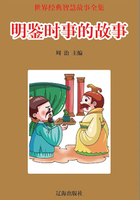再者青年总是糊涂的,无经验的。以读书研究而论,他们往往不知门径与方法,浪费精神气力而所得无多。又血气正盛,嗜好的拘牵、情欲的缠纠、冲动的驱策、野心的引诱,使他们陷于空想、狂热、苦恼、追求以及一切烦闷之中,如苍蝇之落于蛛网,愈挣扎则缚束愈紧。其甚者从此趋于堕落之途,及其觉悟已老大徒伤悲了。若能以中年人的明智,老年人的淡泊,控制青年的精力,使他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则青年的前途岂不更远大,而其成功岂不更快呢。
据说法朗士常恨上帝或造物的神造人的方法太笨:把青春位置于生活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爱情,磨折于生活重担之下。他说倘他有造人之权的话,他要选取虫类如蝴蝶之属作榜样。要人先在幼虫时期就做完各种可厌恶的营养工作,到了最后一期,男人女人长出闪光翅膀,在露水和欲望中活了一会儿,就相抱相吻地死去。读了这一串诗意洋溢的词句,谁不为之悠然神往呢?不止恋爱而已,想到可贵青春度于糊涂昏乱之中的可惜,对于法朗士的建议,我也要竭诚拥护的了。
起初,我的目光是随意而轻快的,渐渐地,涩涩地凝住了。
收藏时光
潘向黎
1995年初夏的某一个早晨。我悠闲地享受了早餐与音乐,泡了一杯茶,正在想今天干些什么,无意中将目光投向了墙上的挂历。
起初,我的目光是随意而轻快的,渐渐地,涩涩地凝住了。挂历翻在6月这一页上,是一幅室内布置的摄影,色泽浓重而明快,隐隐散发着夏日原野的气息。
已经有好几页被翻过去了,翻到无人注视的背面去了。我此刻想不起它们分别是什么画,但我知道,只要我再次看见它们,还会认出它是1月或4月,因为曾经注视过它整整一个月。然而,那又有什么意义?
我想把它翻回第一页。像一本好书的封面,它十分简洁、朴素,白底厚实的纸上,印着金色的“恭贺新禧”的字样。看着它,我曾感到得到某种承诺的安心。可是,那种新年期盼的莫名欢快早已消失,那时盛开的爆竹,烟花,连尸骨都已腐烂了,转眼,白晃晃的夏天已逼近了。
家里所有的挂历都是我翻的,热心地每月不误。其实,翻挂历的是另一双手,一双无形之手,同时顺便也翻走了我生命中不可重复的一个又一个时令与季节。我不知道挂历是否对我有一种胜利感:表面上我操纵它,事实上我才被操纵,而且通过它反映得清清楚楚。在这场无声的争斗中,我们永远节节败退,它就是记录。
我有收藏挂历的习惯。此时此刻我能立即取出“1984年”或者“1985年”。对我来说,过去的某一年与某一本挂历是密切相连甚至有相同含义的。
1984年是一本俗艳的明星挂历。那一年的上半年我像半个疯子似的准备高考,结果没有考进理想的大学,失恋般地进了另一所大学。那些日子,常常注视着某个明星白痴般的笑脸,心里充满了绝望。然而终于也熬下来了。
1985年是一本日本仕女画的挂历,十分古典、精致。其中有一个月份是那幅著名的《微雪》。冒雪前行的女子打伞的姿态,半开如惺忪睡眼的伞,雪粉与肌肤一样婉约、微妙,充满梦幻感。那一年我开始享受大学生活,与女友一起背《红楼梦》,练习大楷字,什么都干又都浅尝辄止。我没有恋爱,似乎有些晚熟。
1989年是一本平庸的世界风光。我已经在读硕士。研究生楼是一座大而无当、灰蒙蒙的楼,楼道里终年光线不足,我也不用功,只在念书的幌子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四平八稳而无拘无束。
1990年是一本很大开本的世界名画,每一幅都是美术史上作为例子的,都美得惊心动魄。那年我开始痛苦的热恋,常常注视着其中那幅《哀悼基督》神思恍惚。那种食不知味的状态是体力难以支持的,所以那年我的挂历上常常出现体温记录与服胃痛药的次数。
1992年是一本小巧的桌式挂历。图案都是船,双桅船、帆船、海盗船,充满异国情调。一切暗示着远行。开头几页上,有各种记号,惊叹号,问号,五角星,还有电话号码与人名,那是我为出国在忙碌的证明。然后,4月的一天写着——“出发”,便不再有任何记号。在我记忆中,这本挂历便凝固在4月那艘忧伤的老木船上。我走后那些船依旧在我房间里,和我留下的一部分自己一样,守望着旧日的一切。而另一部分的我与5月都远走异国了。
现在的我,因为没有自己的家,所以与双方父母轮流同住,拥有了双份的家居。挂历也有二本,一本在我父母家,是印象派绘画,另一本,就是眼前的这一本,挂在公公婆婆的家里。这二本挂历互相补充,在一本上没有记载的,肯定在另一本上可以找到痕迹,拼合出一份实实在在、无懈可击的生活。不知说明我生活的双重性、还是某种分裂?我似乎常常扮演多重角色,时而沾沾自喜,时而忧心忡忡。我越来越忧患,也越来越洒脱,我越来越认同,也越来越叛逆。只有极少数老而又老的朋友,知道我的真实面目,而且知道何以如此。
不能再讲这些了,免得我忍不住诉说的冲动。还是回到过去。一本又一本的旧挂历,放在一个箱子里,有拉链的旧皮箱。我很少打开它,因为它会像伤感小说的阅读那样令我不能自拔。那个箱子犹如一个收藏死去情人信件的所在,令我悲伤、压抑又无能为力。
我可以烧掉里面所有的东西,但那反而使之升华,从现实存在升华到记忆中的永恒,从而更具备精神上的威慑力。我不会那么做,我要让它们在床下阴暗的角落慢慢发黄、发脆,苦苦等待我偶而打开箱子的时刻。我明白我在报复。报复一种决绝的抛弃与背叛。可是,这种仇恨本身恰恰是我一败涂地的证明,我所能对付的只有挂历,这时光骨髓,而曾在它上面蠕动或振翅轻唱过的东西,早已远离了我,头也不回,轻盈无比地远离了我。眼前的一页挂历是一扇打开的门,向我暗示许多可能与希望。但多从不能及时地相信它尝试它,我还在为过去那扇关上的门而流泪或微笑,后悔或者回味,有时还把这些写下来,生怕有一些除了我世上再无人知的东西永远被湮没——这时,眼前这一扇门就徐徐地关上了。等它“卡达”一声关上时,我才醒悟自己又犯了一次多么可笑的错误。这时,下一扇门缓缓打开,看见它面前的人蓬头垢面、心神恍惚。
岁月也许并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挣扎与过失,要不,我为什么对它如此恋恋不舍呢?我收藏它的尸体,是希望它的灵魂会有朝一日还魂的吧。
快乐的、优雅的、令人陶醉的日子,总希望它能留住或者至少延长,但事实上,因为这种贪求,那单纯的甜美中便掺上了无奈的苦汁。至于痛苦、屈辱、过分矛盾的日子,我们又一心指望日子快些,飞快地前行,将那些难以承受的留在原地,而我们逃遁而去。为了怕它们尾随而至,我们草草地退出一段生命,退到痛苦与人都无法企及的地方——记忆之国中。
我们忘了,无论美妙的或丑恶的,痛苦的或陶醉的,都是我们渡过生命的小径。在早晨(那生命初始的早晨啊!)的树林中,小径密如蛛网。而我们的双足,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一旦踏上便不能回到相同的起点。
如果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得有失,都可能令你在日落时痛悔,都无法割舍对其他选择的想象,那么选择哪一条路又有什么区别?选择与不选择,又有什么区别?
即使你由此产生了许多经验,具备了比起始时高超的智慧,那又如何?你不能回到那个时刻,不能再做一次选择并有明了它的底蕴。我们未被赋予第二次生命来比较、确证,那么选择有什么正误、高下之分,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的悲欢、对错,甚至死亡与新生,坚贞与放荡,都会沉入时间之水,水面永远平静。
岁月无敌,我们败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千年悲悼的泪水汇成暗河,在日常生活的地下悄悄呜咽。
而挂历,这与“过去”最后的联系,过去的一切确确实实发生过的物证,它是“过去”关上的门上的一条缝隙。透过它,可以遥遥看见那过去的世界依旧在另一时空盛开如莲,尽管此岸的生命落英缤纷。
面对现实,我明白,我们年轻的心无法承受真正的爱。
面对青春的萌动
聂振伟
“早晨,我一走进教室就又与他的目光相遇了。我感到脸发烫,慌忙避开。真是莫名其妙!我平时和男生说句话都脸红,更害怕别人盯着看。我低着头,快步走到座位旁,急忙拿出语文书挡住脸。整整一节课,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课本。
‘铃……’可怕的上操铃声响了。我无可奈何地站上领操台,浑身上下感到不自在,手脚似乎变成多余的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因为不用看我就知道,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有双眼在看着我。尽管那目光中并无恶意,也绝无侮辱性,而且还可以说是一本正经的,但每当我一想起那目光心里便涌起一种说不清的烦恼和厌恶。十五分钟的音乐似乎播放了一个世纪。”
这便是青春萌动。
爱情是甜蜜的,可过早地尝到它也有些涩。
这是一个高中生讲的:
“我被爱神‘俘虏’时刚上高二,他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们曾一起度过了一段力图将幻想变成现实的生活。这段时间里,尽管自己像一把锯,在恋爱和学业间扯来扯去,一会儿想到他,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还要考大学……但初恋的美好织成美丽的光环,让我无法见到真实的现实。
渐渐地,我忽然觉得,一个人的心虽然有时可以很大很大,却有时又很小很小。心明明早被七八门功课、大量的复习题和学校里各种活动塞得满满的,却还得给他腾出一席之地。你看,这该有多难。哪像岑凯伦小说里那上学的女孩儿和心上的白马王子相恋得那么轻松和浪漫?真没想到,此时此刻,爱竟成了我生活的负担。
在我被扯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我只好决定暂时离开他,我希望能安心考完大学后再和他联系。他很体谅我,没有多说一句,便默默地和我减少了联系。没想到,收不到他的信,我的心更不安。当我有一天再也抑制不住推开他虚掩的房门时,看见他正伏在桌子上,一封封写给我却没有发出的信堆在那里。刹那间,思念冲破了防线,我又重新担起学业和恋爱两副沉重的担子。我不忍心看着他在痛苦中煎熬。可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在12点钟以前睡过觉,我太累了。
高三了,这样的生活使我疲惫不堪,当我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时,我决定离开。和一位外地的朋友联系好,准备到那里去上学。也许一年的分离会使我成熟一些。但我最终也没走成,妈妈的眼泪封住了我的路。当我们母女相依流泪的时候,我心里在说:“妈妈,我知道在外地上学会很苦。但是我留在这里更苦,您懂吗?妈妈!”
到此为止,我才知道爱情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恋爱的资本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远离现实的幻想、做不完的功课和考不完的试,以及对前途担不完的心……
面对现实,我明白,我们年轻的心无法承受真正的爱,爱与学业之间必须放弃一方。短时间会痛苦,但每个人对自己受伤的心都会进行自我调节,继续向前。
当你的物欲一一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仍然会有一种贫乏感,这全因为连我们自己都变成了一个躯壳,精神是空虚的。
青春虚荣之劫
宋月航
很多年轻人一定都有过与我相同的想法,认为钱是万能之物。其实,当你的物欲一一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仍然会有一种贫乏感,这全因为连我们自己都变成了一个躯壳,精神是空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所为,让自己都感到陌生。
我叫小丽,今年20岁。我生在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我们宗族中,我能读完高中,已经是很耀祖的事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再干与父母一样的营生了。很费了一番努力,我到了一家乡镇企业当合同工,这时,我的心才算有了点舒展。
厂里的同龄人与我的差别很大,姑娘们最爱谈论穿戴,下了工就进舞厅,或上影院、下饭店,花钱如流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快乐的。我出落得美丽动人,可自己与厂里的同伴相比,却有一种自卑感。因为我不能如她们那样尽情享乐,我的日子不开心。每月的工资除了自己吃饭,还惦记寄给家里点,我根本没有余资打扮自己。
我觉得自己像这个环境中的局外人,想逃避这种心境,可她们总是花枝招展地在我眼前晃动。
在我正闷的时候,一天晚上,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带着他的一个朋友来找我玩,他们约我到饭店吃饭,这是我第一次下饭馆,我们边吃边谈,最后结帐的时候,花了六张大团结。我同学的朋友掏的钱,他看上去很富有,还骑着一辆“嘉陵”摩托。
以后,这骑摩托的人常来找我,我也愿意与他交往,因为他能让我满足虚荣。他叫老黑,早已结婚,女人在家种田,他做了几年药材生意,赚了大钱,欲望自然也就多了。人身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老黑与我各自找到了互相的满足。他垂慕我的容貌,我看中他的钱财,还算公平吧,至少我没白花他的。
我在工友中的位置大变,总有人凑到我跟前,艳羡我的穿戴,有些饰品她们只有欣赏的份儿,根本买不起。这些都是老黑给我的。
我所能给予老黑的,便是与他同床。虚荣能使女人走到这一步。
老黑的妻子耳朵真灵,她找上门来与我撕骂。看热闹的人把楼梯都塞满了,我立刻成了厂里头号新闻人物。
老黑为了我,不惜血本地与他妻子离婚了。我俩从此公开过起了夫妻生活。
时隔不久,厂里一个红头文件取消了我的合同工资格。我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再漂亮的衣服也没机会往外穿了,日渐愁眉苦脸。原先温顺的老黑一天比一天粗暴。有一次,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让我给他洗脚,我不小心泼了点水在地上,他揪着我的头发就打……
以前,老黑用钱满足了我的需求,我觉得他什么都好。其实,他倚财欺人,干了不少坏事。在我熟悉他之后,我愈加发现他恶的一面,内心时时涌动起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也要随着这恶的裹挟,越走越远。
终于有一天,两名公安干警把他抓走了。事后听人说,老黑参与了流氓抢劫,他的钱财并不全是凭个人经营挣来的,还有骗来的、抢来的。我看着那些曾让我光彩过的华丽衣裳,它们原本就不是干干净净来的,却包装了我的青春。我几乎哭死过去,是自怜还是尚存的一点良心在责问?
在我把这些话写给自己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重新的生活:在我家乡的土地上,我挥汗劳作,在生活的艰辛中,我体会到真实、纯美,这对于人生来讲,也许是最珍贵的。
我恐怕不会离开土地了,我曾经是那么厌恶它。今天,让我厌恶的是自己曾有过的一段经历,是土地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而所有的今日必将以无与伦比的崭新的姿态挺立于你的面前,不是你检阅它就是它检阅你。
感觉今日
艾明波
感觉今日如同感觉一种氛围。
感觉今日如同感觉一片明媚。
感觉今日就是感觉幽幽的竹箫的鸣响,就是感觉岁月的脚步又一次踏向初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