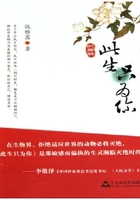随着夜的深刻,我们几个就成了空壳,不但没了灵魂的感觉,连筋骨血脉也仿佛不存在了。角度转换,我以一个安静的湖的角度,注视那个怯弱的我,以及我的同伴们,这几个没有灵魂的人正在讨论灵魂的问题。他们已经走题了,无意中把灵魂和鬼怪连在一起了。
我们找不到回住所的路了。
灵魂就是我们最惧怕的那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漆黑夜晚的骤然到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类似忌讳的事情,或是一个真空。
假定它有。
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到灵魂呢?是不是因为离我们太近?就像这个湖边的夜晚,我们看不见咫尺之外的事物。也许还因为我们把灵魂一词弄得过于神秘。它既是一个广大无边的无,又是一个具体细微的有,无可把握地漫游在我们的精神里。生活使我们将它凡俗化,力图让它成为皮肤埋住的任何器官。但在另一些时刻,神圣、高洁,面对心动之美,我们生出绵长的悔意——有一部分生活我们没能很好地过,有一些我们对不起,灵魂此时成了我们的理由。周而复始的黑夜白天,它本该具有的作用越来越难于发挥,那是透明的存在。它的存在应该使我们在一些时刻里忘记自己是凡胎。
“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那一定是距我很远的地方”,身体的生存必然伴随圣洁灵魂的消遁,梭罗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人最好不去探知灵魂的住所,这是一种危险的旅游。一旦挖掘深了,便会发现灵魂和我们身上的魔鬼已相处为好友。看到善无动于衷,接触恶眼睛发亮,灵魂的嗜好与肉体的嗜好是一致的。欲望泛滥正如江河涨水,泥沙混杂却不能否认灵魂正在疆域之内作怪——我们已经分辨不清什么。久而久之,提起灵魂的时候再也没有感情的冲动和心情的配合。
只有黑夜能提醒我们不要忘了灵魂。一个喜欢黑夜里走路的人,有可能是一个深刻的人(我指正派的人),他和灵魂在一起的机会就多些,他不会像我们似地把它挂嘴上。视觉迷蒙,心灵才活跃。这不禁让我想起又一个特殊的黑夜:隧道。时间在那里被残忍地阻隔切断,灵魂喜欢潜伏在那里。长达一小时的隧道过完了,光明重现,而你确信没有产生堕落的念头,那么灵魂刚才握住了你的手。
黑夜里,行走的时候能感觉到灵魂撞脸,和大白天摩肩接踵的活人一样多。缺的是一盏灯,灵魂照耀的灯。往往,所有的灯都开了,自己也通不过,负载过重的心比黑夜更深更沉。心的四周已不是光芒,而堆砌了技巧,所以我们无法完全按照心的指引走了。我前边提到的那个熟人,他说自己不惧怕和自己对话,是一个看上去毛病很多的人,正是因为他不欺瞒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和心脏和谐一致,所以才在众多场合难与身边的人相处。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剔除了灵魂(免得它碍手碍脚),就不习惯看到谁和自己的灵魂呆在一块儿。
一个和灵魂厮守一处的人,一定是一个以惯常目光看起来别别扭扭的人,因为他比别人身上多了些什么,而且这个东西携带不可能方便。只有夜晚来临,他才显出比别人睡得安稳,“不怕鬼叫门”。但那天在镜泊湖,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看上去顺眼,在场合混得不错的人。我们都害怕了。人害怕夜晚这说明了什么呢?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发现坐在一片河边卵石上。很均匀地、有序地躺在河岸上的那么一大片石头。谁也不说话,好像就这么认可了。随意的抛掷就像一块石头从天而降。每一块石头上都焕发着一种蓝幽幽的光和雾,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上帝不仅为每个人做出了安排,还为灵魂们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我找到了它们之所在。难怪人们灵魂丢了,原来它们早就不和肉体在一起,而和森林、湖泊为丛了。剩下前台那些肉体、驴皮影似的人形,在远离这里的地方吃喝玩乐、苦恼悲伤着。有一部分人,最终会回到这里,认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像洪水之后仅存的那对夫妻,他们明确得到了神的吩咐,走出庙门,以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每一块石头反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但是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永远回不到这里,被错隔在漫长的、先是游戏后是恐怖的夜的另一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排列好青春历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脚印,每一次心跳,为自己做一次庄严的检阅!
检阅自己的青春
赵冬
每当我们挥褪纤尘,洗祛铅华,抖落人生旅途的困惑与疲惫的时候;每当我们跃上命运的制高点,心想事成,扬眉吐气,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够有一次冷静的思考——检阅一下自己的青春。
面对回忆,我们是否在重读自己的同时,涌起一份骄傲和自豪,唱起那首《青春不悔》;面对太阳,我们是否敢于裸露自己心灵上的某一处残疾,而重新设计人生?心中的偶像不再仅仅只是英雄、伟人、明星、大腕、款爷,更多的则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那些平平凡凡而又兢兢业业的人们,是老师是父亲是守望过我们精神家园的前辈。
检阅我们的青春方阵,不仅仅只有容颜的涂擦,穿戴的讲究,居室的豪华,还有学识、情趣、爱心、良知、机遇、缘分、奉献……许多许多。帅哥靓姐,不一定都有壮丽的青春;凡夫俗子,却实实在在地吟唱着自己如歌的人生。
我认识一位19岁的外地女孩,离家在外打工,当她听到一位被烧伤的婴儿因父母付不起高昂的手术费,医院拒绝进行植皮手术的时候,便走上前去,拿出自己一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2000元钱,送给了婴儿的父母,她却只说了一句话:“钱不多,是我的心意。也许,孩子比我更需要这钱。”
我认识一位双腿残疾的小伙子,一天夜里,他摇着手摇车往家赶,在一个漆黑的胡同,发现三个流氓正对一个女青年施暴,他冲了上去,双拐狠狠地砸在流氓身上。女青年得救了,他却被打得遍体是伤……
我认识一位出租车司机,一天晚上驾车回家,遇上一个醉汉倒在路上,他停车把醉汉扶进车,醉汉呕吐弄得满车脏物。他把醉汉安全送回家后,默默地用水擦洗,直到半夜。他说,不为别的,救人于危难,应该是做人的准则。
我认识部队医院里一位漂亮的女战士,她每天工作完毕,都要去病房里打扫卫生,为患者洗衣服洗被,端水倒尿,所有的脏活累活儿她都抢着干,一干就是四年,直到复员,干得无怨无悔。
……
岁月的沟痕蜿蜒在绿色的土地上,时间的箫声逡巡在蓝色的天空中,眼睛里的风景随奔跑的年龄,组成一座青春方队,明眸闪闪,秀发飘飘,倩影娉婷,衣袂飞舞……我们在接受自己的检阅!
检阅自己的青春,把我们自己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群的价值做一次评估,只要能够真正经受得住自己的回顾与审视,无愧于我们的黄金时代,哪怕我们的青春期里没有鲜花簇拥,没有奖章闪耀,没有锦旗围裹,我们至少也能拥有周围的注目与赞许,来证明自己青春的诠释。
排列好青春历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脚印,每一次心跳,为自己做一次庄严的检阅!
惟有虔诚,能超越困难和借口,活出一个真诚的人……
做人还是要虔诚
姜维群
现代人缺什么?缺的是虔诚。
什么是虔诚?一言以蔽之,虔诚就是认真到一丝不苟的态度。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都有一种感慨,在那大漠孤烟、荒寂无人的世界,创造了那样艺术的辉煌,靠的是虔诚。虔诚是执著的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信念,所以虔诚也是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现代人聪明了,尤其是爱玩弄小聪明的人,大都视虔诚为傻为痴为缺心眼儿。虔诚是倾付一切心血、集中全部精神的事,然而现代人的观点是,以最小的投入去攫取最大的利润。且不论在生意场上算不算投机,即使在官场、情场上这般做也颇令人堪虞。
做官虔诚者不欺君欺民,这样的官常有愚忠之弊,然而这臣不忠上欺君下骗民,为子不孝糊弄父母,自以为聪明者最后都被当世骂或后世唾。为艺者不虔诚,只想耍弄点小技巧糊弄别人,最终被糊弄的是自己,一生白忙活。虔诚是发自内心的倾慕敬仰,是调动全部身心投入的狂热。现在时髦的是求神拜佛,那么多的人跪在泥塑木偶前一脸虔诚颂祷有词,然而他们虔诚么?这种虔诚不是对神灵的虔诚,而是对自身发财的虔诚,是对自身平安的虔诚,正像许多为官者,对他的上司那般虔诚,其实是对自己的乌纱帽“虔诚”而已。
做人还是要虔诚是指心态而不是形式。真正的虔诚是对工作的敬业,是对他人的真诚,乃为人生一大境界。虔诚不是利益的索取,而是不计较得失的付出,大音乐家常有晚年耳聋失聪者,但仍创作不止;大画家大书法家晚年不乏失明者,但仍挥毫不停,其人生的支撑点在于对艺术的虔诚。人对虔诚越来越远了,认为那些是思维的不健全、智慧的不完满,然而恰恰是这样信念虔诚的人,创造了世界各个领域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我们每个人都有长项和弱点,然而虔诚常常弥补弱点弥合缺憾。人生的弱点和缺憾常常是盼望得到害怕失掉,正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下人们活得那般累那般不自在。虔诚让人们忘掉得失,忘掉得失的人生并不等于不得,终日锱铢必较的人未必不失。虔诚告诉人生这么一个道理,做人虔诚做事虔诚为艺虔诚,此等人交友有真朋友,工作有大成绩,艺事必有大进展。
虔诚是人生的大手笔,小聪明是人生的小刻刀,前者写出的是人生的亮色,后者雕镂的是眼前的实惠。惟有虔诚,能超越困难和借口,活出一个真诚的人,调动出真正大智慧,在红尘滚滚中内心不染埃尘。
一个天机畅达,追求生命至理的人,其最高境界不是自登极乐,而是重回尘世,与众生共命,此即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与众生共命
陈幸惠
轻微的剥啄之后,我终于无声地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了芭蕉上人的世界。
苍灰清寂的小屋里,即使在接近正午的时刻,也依然充满破晓的情调。
正在蒲团上结枷跌坐的上人,想必已结束了他每日的功课,双目垂闭,无所旁骛,一派心定气闲、平和专注的样子。
10年岁月的轮转,并不曾在他舒展的眉间、清瘦的脸上,留下任何征服的辙痕;不,应该说,10年流光,只是溶溶漾漾、吹不皱满塘春水的一阵清风,拂过他无所窒碍的胸怀,在他原有的安详宁静中,更添注了一点坚忍刚毅与宽容悲悯的成分罢了。那是一种足以使顽石点头的温和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即使面对众生苦难,也都能深情拥抱的慈悲与勇敢。
我想起自己心头那点小我的迷惑与烦恼,不禁陡然澎湃起一片若有所悟的感动;曾经执着盘踞在心的伤痛与酸楚,遂不觉在面对上人的时刻,裂成微不足道的碎片,煎沸成热泪,颗颗自颊间滚落下来。
因为,生命自身,本无风雨;若有,那边只是自己修养工夫不够罢了,除了当下反求诸己、另创新境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举世炎炎,众生颠倒沉迷,上人之所以自那一片混乱的火热中退出,除了去追求一个自觉生命的完成之外,或许,他的初衷也只是要将自己,化为一片清凉,去消弭若干焦躁生烟的苦热呢?成佛成圣先成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则上人在众人皆醉之际,独苦苦追求一个绝对清醒独立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情怀呢?
然后,我十分惊讶地瞥见,上人那张散发乌黑光泽的书案上,竟整齐地叠放着一套线装“四书”,和一部《阳明传习录》。满室佛书宝卷之中,竟有如此风格不类的经典,伴随这位闭门深山的异人,倒真使人有几分意外了。我翻开那密密圈点、细加批注的扉页,赫然一段文字映现眼前——
……儒家学问乃生命之学问,力行之学问,而非供人以为概念式的分析之用。
……认同中庸,则不致偏激;认同大学,则不会做小人;认同孟子,方能具大丈夫之气概;认同孔子,则必可培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襟怀。
……一个天机畅达,追求生命至理的人,其最高境界不是自登极乐,而是重回尘世,与众生共命,此即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为,天下事乃天下人分内事,世间忧患不解,不安不真不善不美之种种不圆满未除,则任何人皆不可自外于此重任也。
……
我从那墨痕淋漓、机锋四出的楷书批注中,无限感动地抬起头,却只见淡淡的光影,如一束柔缓垂注的瀑布,正自上人身后的天窗披泻下来,无声地冲击在他肩上,然后轻轻溅洒散开,仿佛形成一圈朦胧但却华严的光环;而上人端凝静坐的形象,便嵌在光环中央,使人产生道成肉身、肉身成道的联想。
虽然,我不能探知,上人由当年的静藏内敛,自乐其道的淡然,到如今心生“与众生共命”的深情大愿,其中是如何山山水水的一段历程?而“与众生共命”这样悲悯浩瀚,更上层楼的境界,又如何可求?但仔细想来,人生诸境,但肯尽心去做,又如何不可求呢?更何况上人是如此忠于自我,富于实践精神的一个人。
我默然伫立良久,再度环顾小屋一眼,终于合上书册,诚恳地在心底为上人祈福,然后悄然离去。
我毫不犹疑地离开上人的幽居,正如我不辞辛苦,跋涉登山来寻求真理与启示一样,具有同样的理由。——因为,我既是问所问而来,如今见所见而去,便再也没有任何的遗憾,一切落于形迹的言语,皆是多余;而人生种种遇合,在上人参透实相的眼里看来,就如钟声过江、江水拍天一样,是不必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因此,10年前那个曾与上人坐而论道的少年,如今在一个美好的春日里,重又回来,至于上人,知与不知,见与不见,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只要我来过了,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便可无挂无碍、心安理得地回去——一切随缘,那不正是上人行事的一贯作风吗?
我释然而笑,心如涨满和风的一片白帆,轻快但稳定地走向山下烟尘弥漫的人世间。正午的阳光下,两侧青山,石瘦松肥,壁立如绵延的翠色屏风,迤逦到一个我不知的所在,但我的眼底,我的心下,一片薄岚,一丝纤云的遮蔽都没有。
回首云山尽处,那果然是一条迢长蜿蜒的道路。
我们曾那么狂热地相信了那些誓言,并且借着对它的感动,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路,直至我们渐渐长大,天各一方。
似水流年
?徐
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猛然梦到了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场面,仍是那片坡地,你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憨实的目光中不乏单纯。
星期天的早上,醒来时一切如常。丈夫正试穿我帮他买的新恤衫,楼下有收废品的小贩摇响阵阵铜铃,也有不知名的流行歌曲遥遥地响。然而这一切在那个梦之后便潮退于时光之外,以至于丈夫问我什么,我也没听清楚,生命似乎一下子省略掉了十年,这十年中的某些东西被浓缩成一个不经意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