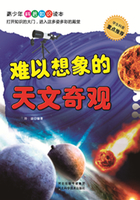太阳终于穿破黑暗而渐渐升起,万物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枫树枝在阳光的照耀下似团团的火。瑰丽的云霞飘动在淡蓝色的天空,有的像盛开的鲜花,在天空中轻柔浮动;有的与阳光交映,如同从篝火中飘起的碎片。
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将是怎样的一天呢?我为这新的一天而感到欢欣。夜晚的神奇消失了,但我难以排除,那神奇仍伴随着我,使我感到这平凡的白日仍有星光在闪烁。
那份伤了我们心的爱情故事,原只是一抹轻淡如云烟的浅笑。
春天里的爱情故事
杨庆华
读书的时候,有几个很知心的朋友,他们是良、毅、钰、桦和我。钰是我们女孩中间最漂亮的,而良和毅是那种气质极佳的男生。
一直到各自工作,我们依旧常聚在一起,去郊游或溜旱冰。好像谁也不曾留意到,良和桦恋爱了。剩下的我们三人无形中便多了一份敏感,我们似乎都心照不宣地考虑到,在这三人中极有可能再出现一对恋人。钰和毅是我看好的。
那是个春季。钰和我座在钰家的床上,钰忽然说起良和桦来。而我却说:还有一对恋人,钰怔住了问:哪一对。我便一字一顿地答:毅和钰。钰脸“腾”地一下红透了,不依不饶地伸手打过来,俩个人笑过闹过之后,我很认真地对钰说:毅是个很出色的男孩。钰此时才羞涩地低下头。
毅面对着我,似乎知道我的心事,显然很高兴的模样。待坐定之后,毅便望着前方的湖面,说:春天真好!我们划船好吗?我摇摇头,竟不知该如何开口。春风凉凉地吹着,而长椅上的毅好像不想再听到我说任何一句似乎已经是多余的话。可是毅和钰是很般配的。“毅。”我终于开口,“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中间还应该有一对恋人。”毅显然对我的话不知所云。“钰是个很好的女孩……”“不要说了!”毅猛然站了起来,不去看我。“我已经有了女朋友。”毅说,“想知道她的名字吗?”一时间,我迷惑起来,我不知毅的女友是谁。“她叫杨易。”毅轻轻地说。并伸出双手欲扶我的肩膀。我巧妙地躲开,毅的坦率使我窘迫不堪。
当时正是六月的天气,杨花飞絮。我装做絮花飞入眼中,低下头,泪落了下来。也许这一生我都会后悔,自己做出的这一切傻事。毅俯下身,我感觉到我的额头被一双温软的唇印了上去,而我在那一刻却转过身,大声地说:我永远不想再见你!便不顾身后的那人是如何的伤心和惊讶,跑开了,永远地跑开了。
当钰听说毅有了女友的谎言时,默不作声,眼睛红红的,我竟觉得自己有愧于钰。
日子悄悄地流逝,一个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接到钰的电话,约我下班去她的家里。
我坐到钰的面前,钰脸上很黯然,好久才说:昨日毅来过。我不知道她的下文是什么,不过听到毅的名字,心竟慌慌地跳了起来。“毅都告诉我了。毅那天很伤心,喝了很多酒,他说他非常喜欢你,他还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制止钰再说下去,空气尴尬、难耐。我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钰的家。
当迈出钰的家门时,我知道已经失去从前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失去了毅和钰。
很多年过去了。前几日,走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了钰。钰似乎较从前成熟了,俨然一个妇人。钰见到我,很兴奋的样子,而过去的故事对她恍若未曾发生一样。钰结婚了。钰说毅去了深圳。在分手欲道别时,钰忽然提起了在我与她与毅之间的感情纠葛,竟忍不住笑,说:少女时代真美!
在我从前的岁月中,我无论如何不曾想过,若有一天与钰或毅再度相逢,那份伤了我们心的爱情故事,原只是一抹轻淡如云烟的浅笑。
“你无法放弃。”他用最后孱弱的生命教我懂得了珍惜生活的权利。
感谢生命
张子影
一直没能记起那个年纪轻轻的小保姆长什么样子,那时我太小了,母亲说满了月的我才只有一只小猫儿大,邻人与接生护士都说:“这孩子怕是长不大的。”
但是父母还是将我带回了家。不久父亲去了前方参战,母亲的身体又极坏,于是那个年纪很轻的小保姆就来我们家了。1岁以前,我几乎每周都要生病,高烧起来又多半在夜间,医院离家有两三里路,要穿越一个坡地和一片旷野,妈妈抱着我,尚是小姑娘的保姆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漆黑的夜里急急赶路,黑夜的风从四面呼呼吹来……母亲说:“那么白净绵软性子的小保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每次都跟了我去,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她可只是来帮我们的小姑娘,非亲非故。”我想在我生命之初就得到这样的亲情和爱护确实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才懂的。
19岁那年我大学毕业了,本该充满幻想和激情地走进社会投身生活,可工作不久就开始发病,持续高烧和全身皮下出血,一纸诊断书将我禁锢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因为一开始治疗无效,人迅速苍白消瘦,不久即衰竭卧床了。随着病情恶化,我的情绪日坏,绝望和急躁下,一个中午我拔掉了输液头,将所有的药水药片扔出窗外,关上房门将医护人员与家人拒之门外。我蒙在被子里脆弱地伤心:生命太苛刻了,我才19岁就要走上悲剧的结尾吗?
“咚咚咚”,有人敲门,我想使劲大叫:“我谁也不要见!”可声音听起来却是这么弱。
“我是八床。”一个熟悉的声音。
八床是一样的病友,因为患再障性贫血,20多岁的年纪已在这医院住了三年。我摇晃着下床,打开门。八床背个手风琴在门口站着。
“新练个曲子,你躺着,我拉给你听听。”
八床这是怎么了。这几天他一直不好,这么重的家伙护士怎么会让他背?我望着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琴声响着,断续又执著。八床苍白的脸上冷汗涔涔,按琴键的手指开始颤抖,那是非常熟悉的《桑塔·露琪亚》。刚入院的时候我和病友一起唱它,还讲有趣的故事。可现在我最先软弱下来垮了精神——“别拉了。”我按亮了床头的呼叫灯。
八床几个月后就病逝了,最后一次走过那病区的走廊。门口的黑板报上还是他的笔迹:
“你无法放弃。”他用最后孱弱的生命教我懂得了珍惜生活的权利。
我的病使一个又一个医生退却,治疗无大的进展。最后,人们热心推荐一位退休十年已不主刀的老医生,是他,默默打量我许久之后,决定为我手术。
无影灯亮了,麻醉血压心率呼吸神经补液输血……那么多双眼睛专注在我一个人身上,老人高抬双手,眼里闪着慈祥的光:“姑娘,别紧张,你数数我的胡子就知道这老头看过多少病人。”
嘴里插着胃管,我牵动嘴角笑笑,我不紧张也不害怕,我甚至非常平静非常坦然,过去18年的日子飞逝而过,生命是我的,可为了这个生命,有多少人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幼年,少年到大学,到毕业,到现在躺在手术台上,多少深情,多少教诲,多少关切。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幸福……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手术室外面的走廊站满了前来等候消息的朋友、同事和领导,甚至连一些不相识的人知道后也加入了等候的人群。
七天后,我醒来。我看到了面挂泪花的母亲、父亲,看到了慈祥欣慰的老医生,看到了我熟悉的病友,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八床了,脱离危险之后我第一次流了泪。
三个月之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第一次下床,摇摇晃晃走出了病房大门。
残雪已经化尽,阳光温馨扑面,视野里土地和田野一直碧绿到遥远的天边,那是生命的延伸吧?无数新叶哗哗啦啦摇动在风中像无数只透明挥舞的小手掌,那是生命的欢呼吧?河水在春天的土地上柔软明亮地流动,蔚蓝的空中鸟儿自由地翱翔,那是生命的深情吧?一切都如此新鲜,一切都如此可爱,生活和生命重新回来了……
面对这美好的一切,我忽然泪水盈盈。人的一生,也许要经历很多很多,是苦难还是欢乐完全是命运的赐予。我们只有坦然地接受,勇敢地面对。不知相貌的小保姆、永不再见的八床、白发白须的老医生、辛勤善良的父母亲、关怀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生命与生活所赐,让我永远感激。
我更感谢厚爱我的生命。
与时间面对面,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与时间面对面
麦李
从小我就知道“孤独”是个好东西。那些死了还让人们记住名字的人生前就常用“孤独”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
近几个月,新调整的工作终于让我有机会实践多年的理想。我拥有了一整个不受干扰、想干啥就干啥的白日。第一个月,我坚持不说一句话不见一个人,每天站在窗前欣赏风吹树叶子哗啦哗啦响,然后泡上一杯绿茶,光脚坐在木地板上看书。第二个月,我发现时间开始黏乎乎地徘徊,屋里干净得没有人烟,家具们都冷酷无情地呆在它们该呆的地方。我有时也躺在沙发上给朋友们打电话,不过他们都太忙了。有句诗说:“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之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我觉得它好极了,而没有人比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倾听时间的振翅之声。
最可怖的是第三个月,老公的工作忙了起来,常常不回家吃晚饭。我那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涌向他的话突然失去了宣泄的对象,我忧郁地想,和社会最后一点联系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