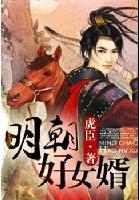殊儿忍不住道:“她自从嫁了人,哪里正常了,听说天天和那范状元吵,吵完回到宫里,自己又跑回去,自从这何家小姐嫁进来,她又往这里跑,都嫁了人,竟这样不矜持……”兀的回神,吓得一张脸都白了:“奴婢该死。”
她却倏地驻足,轻道:“不好。”将何婉曦推到殊儿哪里就提裙往回跑。
花厅内寂静无声,唯听枝叶簌簌,昭阳双颊酡红醉卧案旁,酒坛倒了一地,满目狼藉,上官漫粗略扫了一眼,四下里却不见赫连瑜的身影,她走进去,风灌进室内,吹得裙裾鼓动,直觉身后有人靠过来,她猛地回头,只觉眼前素色幔帐乱舞,臂上被人一拽,下一刻背部紧紧贴到花壁上,熟悉的薄荷香夹杂着酒香,她一颗心尚咚咚直跳,他的手箍住她的肩头,掌心滚烫。
抬起眼来才见他眸子已成深蓝,幽深如夜空,灼灼落到她面上,气息含着酒香拂到耳侧,他呼吸粗重,上官漫见他神情,不禁蹙眉:“她果真在酒里放了东西。”
“唔。”他隐约含笑:“叫种做缠绵的春药,质地粗糙,来的却是猛急。”
她刹那面红,忽又透出苍白了,气道:“她竟这样……”不知羞耻,说到一半便咬齿,她自小虽在冷宫,礼教却是极严,万万想不到昭阳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给男子喂下春药,其目的昭然若揭,况她已嫁做人妇,堂堂一个公主,竟做出这样下贱的事情来,她一时悲愤难辨,一股脑门便发泄到他身上:“你竟也喝下去,万一……”他暧昧不明的低笑一声:“没有万一。”她才知他是故意,一时又气又笑,他低头便吻下来,那唇滚烫炙热,灼的她双颊似也燃起来,身子轻颤,忍不住紧紧抓住他的衣襟,只觉他颇粗鲁扯开腰上绶带,环佩叮的一声坠落地上,他的吻烙铁一般落到胸前,她将滚烫的脸埋到他的颈窝,只闻耳畔尽是彼此浓重呼吸声,再也听不到旁的了。
第二日皇帝乾坤宫召见,暖阁里白烟屡屡,夹杂着浓重的药味,皇帝阖目仰脸躺在摇椅上,手里尚攥着一本奏章,想是睡的熟了,指节一松,眼看便要落下来,她悄声上前接在手里,将奏章放到书案上。
许久未见,竟觉他老了许多,清瘦面上细细碎碎褶皱,刻满了岁月痕迹,发只用玉簪箍住,才见他双鬓已然花白。
皇帝喉间咕的一声,猛然便醒了,她忙伏下身去:“父皇。”皇帝惺忪睁开眼,声音尚带着睡醒的混沌:“漫儿来了。”
她低低道:“是。”
皇帝垂下眼来瞧她,她一身绯红的锦装翟衣,这样伏在地上,衣裳层叠逶迤一地,只觉艳光四射,便一时有些恍惚,上官漫许久未听他开口,跪在地上,膝盖便隐隐发疼,忍不住身子一颤,皇帝才回过神来:“起来吧。“招了招手:“赐坐。”
便有内侍搬了锦凳来,她矮身坐下,低眉敛目等他开口,皇帝看她一眼才道:“朕命他们两月内完工,是你绘的图,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便代替朕下去监着吧。”
她倏地一惊,未想他并不过问那机关之事,急急跪下去:“儿臣领命。”
皇帝缓缓阖上眼:“朕倦了,退下吧。”
她狐疑一声“是”无声退下去,只闻暖阁内传来隐隐咳嗽声,曹德急急拿了鼻烟壶,皇帝低头嗅了,失了力气般靠近椅背里,声音疲惫:“朕给她一张免死牌,怎么用,就要看她自己了。”
由专人擎灯领她进了密道,里面闷热幽暗,唯那内侍手里微弱的灯光,脚下一滑,身侧有人将她扶住,低低的一声:“殿下。”
那声音听着熟悉,她猛地看去,才见洪飞一身戎装立在一侧,因着生的高壮,甬道里窄矮,他只得弯着腰,显得局促别扭,她有些吃惊:“你怎在这里。”
洪飞道:“属下奉旨前来。”
暗道的事,自然是知情者越少越好,说不定今日参与的这些人某一日均会无声无息的死去,密道里征来均是没有家室的百姓,茕茕一人,为了赏钱被带到蒙面带到这里,也是不准出去的,只怕暗道建好之时,便是这些人丧命之期,连她身为帝姬都生死未卜,洪飞竟也被派了来。
她默默点头,不再说话。
赫连瑜中午回来,并不见上官漫,只见天瑬二人侍立门口,不禁问:“夫人呢?”两人皆是胡人,汉语说的并不利索,索性用胡语来说:“夫人自皇宫出来并未让奴婢跟着,只让奴婢二人先行回来。”
他闻言漫不经心的点头,恰时管家过来:“大人,午膳已经备好。”他没了心思,道:“撤了吧。”
青瑞道:“这是开始行动了么?”唯见赫连瑜深深蹙眉,负手踏出门去,杜明在身后摇头晃脑:“下一步,对老大来说,不好走哇。”
未想这一停留便是一下午,甬道里已然不见了原来的模样,未防有知情者混进来,她将路线改了许多,由洪飞陪着漫无目的的走,只听一人惊疑:“这是什么?”
派下来的扈从皆知事情严重,发现物品丝毫不敢懈怠,恰巧上官漫在这里,便捧上来,上官漫一见不过是本手札,扈从不敢打开,只颤颤巍巍捧过头顶,因着没有亲近的宫女侍奉,洪飞便接过来,翻开,竟无一字。毕竟都不想发生什么事端,见那纸上无字,皆都舒了口气。
洪飞本也是神情严肃,这会表情才缓和了些,开着玩笑:“难道是无字天书么?”
听得上官漫心里一动。
扈从已低声命令:“散了。”
这才来到僻静的一处,叫洪飞拿了举着灯来烤,不到片刻,果见一行行清丽小字浮上来,她如获至宝。
这字迹她识得。
“成婚那日,我是心甘情愿,嫁给萧郎,皆为了他手上的兵权,我依稀记得嫁前那晚,八哥穿着一身白衣立在树下,丫鬟奶娘为我梳发,他便在那里看着我。那眼中的神情看得我的心都碎了。
我应该对他笑,因为一切皆是我心甘情愿。他散去丫鬟们,只剩了我们两人,离我在几步处站定,我盯着铜镜里的身影,亦不敢回过头去,只怕泪流满面。
我不会负你。
他这样说,我眼中泪水顷刻而出。”
“两年过去,他终于登上那个位子,还记得那天呼声震天,我独自在院子里听着鸣钟贺乐,心里喜欢异常,未想萧郎这样快就回来,一把将我抱起,只在院子里飞旋,苏瑾,他大笑:我们生个孩子吧。”
“可是那晚,他约我去暗道相会,姝璃宫曾是我住过的地方,那下面并没有设下机关,方便他安全前往,我自暗道进去,与他相见并不是难事,可我已为人妻……我终于还是去了,他只狠狠将我抱在怀里,吻落下来,这样猝不及防……”
“我选了一条不归路,每每撒下谎言进宫,心中都残留着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我告诉他,身体乏累,不便同房,他便搬到书房里去睡,他总是这样依着我,哪怕再无礼,他也依着我。”
“八哥拍他出行的日子越发多了,我也几乎就住在了那里,可八哥并不是我一人的,月圆之夜,他遵循祖制,留宿凤栖宫,我独自在床畔守了一夜,这里是闭塞的石室,寂静的听不到一丝声响,只闻见自己的呼吸声,漫漫长夜,苦守空房,我终觉得倦了。”
“那一夜后,我竟病了,因八哥无法前来,我独自回了王府,管家给萧郎捎信,他竟连夜赶了回来,他风尘仆仆扑到榻前,紧紧握着我的手,低低的唤我,苏瑾,他喜欢这样叫我,也便在那一刻,我突发现,这个男人,才是我一生可以依靠的。”
“我与八哥刻意拉开了距离,我也再不进宫去,八哥逼问我,我只说太累,他竟大怒,我们不欢而散。可我未想到他竟这样狠心……”
“萧郎回朝一直沉默,我才知那赫连启竟来向八哥要我,我已为人妻,又有了身孕,如何和亲,我气得浑身发抖,哄萧郎先睡了,偷偷跑进宫去找八哥理论,他竟逼我选,不去和亲便要留在宫里,我气得举掌便是一个耳光,他也懵了,气急败坏叫嚣:你再也别想见到他!我害怕了,连夜赶回去,却见王府一场大火燃的半边天都红彤彤一片,我的萧郎,府里几百条人命……”
翻到最后,也只扭扭歪歪的几句,似是心情极其剧烈写下的:
“上官昊,我恨不得饮其血,啃其骨,可怜我腹中的孩儿尚未成形便撒手人寰,这血债必要血来偿,我便是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我诅咒你,诅咒你子叛妻离,生女女被辱弃,不得善终,亲子骨肉相残,血亲论乱,孤独终老!”
最后一句,笔痕力透纸背,在纸上滑下一道深痕,仿佛一双血红的眼睛带着憎恨凄厉蓦地剜过来,利剑一般直刺胸口,几欲窒息,她刹那惊出一身冷汗来,手札啪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