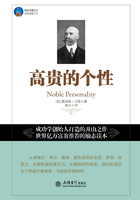暖阁内静得厉害,皇帝尚在与赫连瑜说话,夜色已经深了,子时已过,宫中人皆已入寝,耀阳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惹得曹德侧目,耀阳受了惊吓一把,忙捂唇,皇帝竟笑了:“耀儿困了吧,送帝姬回去。”
曹德忙唤了人来送耀阳回去,过了半晌,皇帝渐见倦色,赫连瑜起身告辞,上官漫依礼送他出了暖阁。
夜色深不见底,内侍前面引路,宫灯映着他颀长身形,他垂首顺阶而下,看不清面容,只听语气似是闲谈:“几日前曾听殿下忘记了些事情,如今是记起来了罢。”
上官漫陪在一侧,扫一眼前面的内侍,那晚他情绪异常,未来得及取笑她,今日要一并讨回来么,她的这一切,在他眼里,原不过是个笑话,幸好,她心中只记得说幸好,她从未在他面前许诺过,她没来得及为他缀璎结玉,是谁在吟,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那似誓言一般的美梦,终也让他生生扼杀,再也不会有了。
她微笑:“大人对此事倒很是上心,往事已矣,介怀于此有何意义。”她就此止步,依风含笑:“大人说是不是。”
他亦陡然驻足回眸,微扬脸照见他隐忍面容,他眯眸看着她,那样的神情,仿佛被她的话戳中要害,剐出鲜血淋漓来,她的心兀的一阵抽搐,下一刻他却意味深长笑了:“殿下不拘小节,着实让臣下激赏。”他扫一眼等候在侧的内侍,幽深眸子唯见深意:“那日臣说的话,绝不是戏言,殿下还是记着为好。”
那些昭阳替她找来的夫婿都遭到怎样的下场,她不知道却也猜得到,可他凭什么,这样笃定决定她的归属,她气的浑身战栗,他已转身下了台阶
冷声道:“多谢大人相告,临观如若下嫁,定会相夫教子,与驸马相敬如宾,也望大人与姐姐如此。”
夜色里赫连瑜修长身形一顿,旋即前行,一起与内侍去了。
再睁眼,已是次日凌晨,天放亮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刻,虽是捧着手炉,仍是冻醒了,昨夜也未着榻,倚在案边合眼眯了会,曹德无声进殿,衣衫上尚带着春露气息,堆笑道:“这里由老奴照料着,殿下去眯会吧。”
她也未推脱,点头道:“那就有劳阿翁了。”
曹德忙道:“哪里敢,这是奴才的本分。”上官漫不再说话。
帷幄里传来翻身的簌簌声,偶尔一声低咳,曹德静静侯了会子,才听帐内传来皇帝睡意尚浓的声音:“什么时辰了。”
“回皇上,破晓了。”
皇帝唔一声,问:“漫儿还在外面么?”
曹德怔了一下:“老奴劝殿下去眯会子,圣上若要见她,奴才这就去宣。”皇帝才道:“罢了。”曹德掀了帐子,用赤金勾勾了,笑道:“皇子们在外面请安呢。”
皇帝道:“太子来了么?”曹德略略迟疑:“回皇上,老奴并未看见太子殿下。”忙又补充:“太子殿下也病了,几日未出太子府呢。”皇帝冷哼一声:“他病得可真是时候。”
随即传早膳,皇帝未用几口便撂下了,曹德无奈,只得撤了。
皇帝转脸道:“你在朕跟前数十年,也是阅人无数,你觉得临观那丫头如何?”曹德依旧堆着笑:“恕老奴直言,临观殿下那性子,当真有几分像极了……”他未说完,只见皇帝摆手,略略不耐:“朕不问你这个。”曹德呵呵笑道:“正因为像,老奴才要说,若说她的资质,只怕超出太子许多,更不用说帝姬们。”
皇帝沉吟不语。曹德自胸中捧出一折叠好的宣纸:“老奴偶尔得之,还请圣上一观。”
皇帝笑道:“什么物件让你这样上心。”接过抖开,那笑意渐敛。
上官漫刚进耳房里,便见曹德拧着眉头急的团团转,不禁问道:“阿翁,发生了何事?”
曹德愁眉苦脸指着桌上一个紫檀嵌寿山石藩人进宝盒,长眉一耷,只用袖子擦汗:“今日圣上让老奴将这个拿来打开,老奴只以为是个普通匣子,打了半晌都未打开。”上官漫抬眼一瞧,只见匣子四壁雕着紫檀嵌寿山石藩人进宝,顶面却是密密麻麻的方格组成,木格之上各刻有天干的十个符号,不禁笑道:“此匣用普通法子是打不开的。”
曹德道:“那老奴就找人劈开来,圣上要的是里面的东西,这匣子留着也无用。”上官漫忙道:“不可。”
“为何?”
上官漫道:“万万不可,这匣子里设了机关,若是强行打开,只怕里面的东西也玉石俱焚。”
曹德闻言直跺脚:“那可如何是好。”他猛瞧向上官漫,只似遇着了救星:“殿下,您既然能识得这个匣子,定是有法子解开,求殿下救老奴一命。”四下里无人,他作势就要跪下去,惊得上官漫忙去搀他:“阿翁,您这是要折杀了临观。”
曹德跪地不起:“殿下,求殿下帮老奴一把。”
上官漫只得道:“我便试试吧。”
九九八十一个方格,需纵横都是天干排序,各个归位,此匣方能打开。曹德让人燃了清脑宁神的香来,室内静寂无声,只觉淡香拂面,曹德拢袖立在一侧,便见上官漫时而蹙眉时而咬唇,忽而又一叹,偶又抿唇一笑,他扫一眼南墙安置的八扇花鸟锦绣屏风,微微一笑。
忽听上官漫低呼:“成了。”啪一声,她素手挪开盖子,弯眸笑的明亮照人,道:“阿翁。”
曹德竟怔了一下才笑的似是狐狸一般趋步过去,上官漫不敢看里面何物,袅袅撤开身来,道:“我去到殿里看看父皇。”
曹德忙笑:“殿下且慢。”匣内一卷素白娟轴,双手捧上:“还请殿下一起呈给圣上吧。”上官漫诧道:“这……”抬眼唯见曹德对她暗暗点头,终双手接过,曹德几步行至屏风跟前,也不知触动什么机关,屏风无声滑开,里面别有洞天,直直望见玄色帷幄,她心里猛地一跳,原这耳房直通暖阁,皇帝倚在毡枕上看书,头也不抬道:“过来罢。”
她一颗心突突直跳,捧着卷轴跨入暖阁,双手举国双肩,只闻皇帝道:“打开。”她一怔,依言在一侧案上展开。
素净卷面墨线勾勒,如画显现眼前,皆是横平竖直,密密麻麻的标注,并不是什么画,她扫一眼,却猛就呆在那里。
其上分明是皇宫布局图,又不是很像,唯有姝璃宫的所处,一跳长长粗线直通画外,却被一笔朱砂生生截住。
她终于认清这是什么,忍不住捏了捏袖子,指上出了汗,捏着只是滑,双手拢在袖子里,只觉拢着一团热气,皇帝有意无意的瞧她:“可认出这是什么?”
曹德无声退出去。
她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字眼在腔中辗转,如雷霆万钧,皇帝猛将手里的书“啪”一声扔到案上,她身子跟着一震,皇帝一扬手,一道白萱飘曳而落,无声落到她脚边,她只敢垂眼一扫,那宣纸上内容她自是熟悉,因着平日里请先,偶尔画些个东西……
皇帝道:“既然你有这个本事,想来是已经发现暗道了。”
这一句何等惊骇,她几乎喘不过起来,亦不敢不答,方才被他一试又反驳不得,狠狠咬齿道:“是。”
皇帝淡淡扫她一眼:“你出宫去了罢。”
立即便如有响雷阵阵滚过心头,历时冒出冷汗来,直直跪下去:“父皇!”
皇帝重重一拍:“你好大的胆子!”
她身子猛然一颤,指甲死死掐进肉里,也不知是否掐出血来,她直觉喉间血腥弥漫,帝姬预谋出宫,这是何等大罪,若有心人搬弄是非扣个谋逆的帽子,说不定一并将太子捎带着,她脑中瞬间闪过顾充媛罗姑太子的脸,那日大雪纷飞,那人侧脸如画,也渐渐模糊,她垂着眼,额上淌下汗来迂回眼睑下,她竟连眼睛也不敢眨一下。
她倒生出孤注一掷的孤勇来,事情既然已经败露,挽回已来不及,她牙一横,唯有叩首:“此事是儿臣一人之举,并不涉及旁人,请父皇开恩。”
皇帝闻言冷笑:“朕真是养了个好女儿,这种时候竟还想着旁人。”
她咬齿不语。
皇帝语气略缓:“你出宫去可有人认出了你?”
她脑中蓦然闪过赫连瑜的脸,那几个字缭绕舌尖,徘徊脑海里,他的面容忽隐忽现,她斗着唇额头碰地,光可鉴人的乌金砖面,真是凉,她眼眶里逼出泪来,终颤声回道:“回父皇,并无旁的人。”
皇帝冷笑:“朕怎听闻有人知晓了此事。”
她额上生出细细密密的汗来,蜿蜒至颊边,碎发拂下来,似有小虫在叮咬,一直不敢抬头,半晌才答:“儿臣不知。”
“太子不知?”
她心里猛然一惊,忙道:“太子殿下并不知晓。”
殿内唯听铜漏“叮”的一声,打在平静水面一片涟漪,皇帝终道:“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