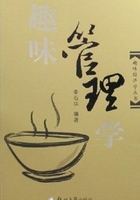那鹅黄衫子的女子一怔,打量她们二人一眼,兰夕见她身上是水绸染得黄色,便知是风尘女子才穿的颜色,语气里便多了几分不屑:“姑娘只要能割爱,银两不必担心。”那女子闻言只冷笑道:“不巧,这琴不能让。”说着再不理二人上前要去取琴。兰夕见她这般傲气,心中顿怒,正欲发作,上官漫抬手止住她,对那女子笑道:“婢子无理,还请姑娘海涵,只是我确喜极这琴,不知姑娘可否割爱。”
那女子听她说的客气,又见她举止不俗,不由又打量她一番,半晌才迟疑道:“小姐不知,此琴是我家公子花了许多心思做成,小女子却是做不了主的。”
上官漫不禁蹙眉,虽是不甘,到底夺人所爱让人不齿,勉强笑道:“是么,那便可惜了。”遂带了兰夕离店,人流如洪,兰夕低低抱怨:“这样多的人,不知我们殿下去了哪里。”面上并无焦急的样子。
上官漫晒然,昭阳为了将她支开她,这样煞费苦心,倒不知那人是如何想的。兀自失神,只听身后有人唤她:“小姐,那位小姐。”
回首便见方才女子气喘吁吁提裙赶来,道:“我们公子说了,若小姐自信能为此琴之主,请奏的一曲来,若小姐赢了,我们公子心甘相赠,并不收小姐一文,如何?”
兰夕闻言脱口就要拒绝,上官漫已笑着开口:“好。”兰夕惊诧看她:“殿……小姐!”她环顾四周,悄声道:“咱们便装出来,可不能引起什么动静,你若出了什么差错,奴婢可担当不起。”上官漫笑道:“若是找到他们,也不是没有法子。”兰夕略见慌乱,惊诧看她,上官漫转头问道:“不知何处抚琴?”
映红道:“小姐不必担心,房间早已备好。”
一张琴桌,一鼎香炉,漫天银雪,倒也极是风雅,因房中只有她们二人,兰夕帮她卸了风帽,她在桌下坐下,调了调音,越发觉的喜爱,暗自沉吟,一曲《小重山》
花院深疑无路通。
碧纱窗影下,玉芙蓉。
当时偏恨五更钟。
分携处,斜月小帘栊。
楚楚冷沉踪。
一双金缕枕,半床空。
画桥临水凤城东。
楼前柳,憔悴几秋风。
脑中不知为何突浮现那人眉目,深邃犀利的目光,难以猜测的神情,他执杯轻啜,夜色阑珊,灯光里唯见他侧脸分明的轮廓,举手投足不经意流露的慵懒风流……她琴技并不算精湛,此曲却是用尽了十分力气,他若有心,定能记得那晚那曲,唯为一人而弹,定会前来找她,若他无情,只管与昭阳独处,又何来顾及她。
“铮”
一曲弹罢。
两人收拾停当,开了门不觉一惊,门外不知何时聚了数千人,站的人山人海,只将御音阁围的水泄不通,见她出来,不由自主的纷纷让路,映红端了琴来面有不甘的递给兰夕。
上官漫心中自知,不由蹙眉:“这是……”
映红道:“我们公子说了,小姐弹琴,贵在心诚,此琴便送给小姐了。”
无功不受禄,上官漫胜之不武,并不打算接受,谁知那映红极大地脾气,气道:“说实话,小姐琴技平平,糊弄这些外人倒还可以,我跟随公子多年,自是听得出来,但小姐弹琴之时,能够置身度外倒也难为可贵,我们公子以琴相赠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收下就是。”
这映红好生没有规矩,兰夕无名火起,本欲与她争辩,上官漫倒是有些喜欢这映红的直性子,况再推辞倒矫情了,亲自接了琴递给兰夕,映红一扭身,渐渐消失人人流之中。
“小姐……”
刚走几步,却有人唤她,回头却见一个书生打扮的模样,生的倒是眉清目秀,只见他拱手作揖,抬起脸来却是满面疑红,只听他道:“敢问小姐芳名……”
兰夕本就不耐,闻言闻言不由好气又好笑,面若冰霜斥道:“你这书生真是好笑,小姐名讳怎能轻易告知与你。”
此话落地,周围便是一阵哄笑,那书生脸上又是一红,见兰夕抱着琴,上官漫微微驻足侧脸,面纱直直垂下,偶有风来,隐约可见尖可削葱的白皙下巴,顿时心跳如鼓,又叫道:“小姐……”
上官漫身子一顿,蹙眉转过头来看他。
他憋红着脸弯身长长一揖:“小生范如清,请小姐告……告知……小生芳名。”原他一紧张便会结巴。
她不由笑了,薄如蝉翼的面纱下影幢的一抹弧度,似是冰魄里缓缓绽开的一株雪莲,霎时灼目生辉,那书生顿时痴痴愣在那里。
天色渐暗,登高看下去,街道宽如苍穹,街上行人仍不见散去,皆携了家人前来看灯,华灯一盏盏亮起,似是天际璀璨星河闪烁。街上极是热闹,哄乱的一片笑声叫嚷声,人与人挤到一处,明灭里可见咧到腮边的嘴角,如此热闹,反衬的这里寂静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昭阳卸去斗篷,只着了轻柔薄透的银纹绣百蝶度花裙,帖服玲珑身姿,越发衬得肌肤如玉,优雅斟了酒,灯下一双手白皙细嫩,她指节并不修长,却因保养极好,十指若葱,她尚不满足,想来是因见过上官漫一双要比自己的纤细好看许多,自此暗藏了恼嫉……她含笑递到赫连瑜跟前,夜色下一双美目似是潋滟秋水:“不知是谁,弹得倒还好听。”
却见赫连瑜抱臂倚在窗扇旁眯眼远望,夜风寒凉,他脑后黑发狂舞,幽暗夜色里他面容白皙,五官如玉雕冰砌,深邃眼窝暗影浅浅,深睫掩住幽蓝眼眸,似已沉浸在自己思绪里。
昭阳不知不觉看得呆了。
觉察她的目光,赫连瑜漫不经心的看他一眼,昭阳面上发热,忙将酒盏递上,他指尖亦是修长,只捏着杯身轻轻把玩,转过头来并不说话,不知想到什么,突微微弯唇,道:“确实不错。”
语气这般柔暖,平日里并不曾听见,昭阳蓦然一悸,竟不知他说什么,半晌才回想起来,刚要接话,赫连瑜冷酷关窗,大步走向门外
昭阳只来及仓促开口:“大人,你去哪里?”
赫连瑜与昭阳一前一后从房内出来,守在门外的青瑞和杜明很是吃惊,青瑞一向沉默,杜明难掩语气中的惊诧:“老大,怎突要到出去。”
赫连瑜头也不回,疾步下楼:“不愿去就在这里呆着。”
昭阳慌乱抓了斗篷跟下去,她长裙曳地,疾步行走并不方便,只急得香汗淋淋,也不看两人,边追边喊:“大人,等等我。”
杜明傻眼:“老大突然怎么了,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关上房门直接推到……唔……唔”嘴突然被青瑞重重捂住,所有音节都变成简单的“唔”字,杜明挥手蹬足愤愤瞪他,青瑞才放手,蹙眉道:“粗俗。”
杜明嘿嘿笑道:“粗俗真么了,人家公主殿下求之不得……不过”他疑惑捏下巴:“老大棋局已布,也按步就搬走到现在,本该强了昭阳,好戏也就开始了,今天怎么……说起来,老大自从宫里回来,总觉与从前不一样了……”话未说完,青瑞道:“去看看。”
冬日的夜色总是亮如白昼,反衬的天际漆黑如墨连绵延伸到尽头,撒泼到宣纸一般的雪色大地,街上彩灯鲜裳,这自然画卷才鲜活起来,人流如洪,即使不是本意,也忍不住跟随人流渐渐远去,待回首,身后物换人移,她已不在原地。
兰夕冷冷低斥:“这秀才好生无礼,现在还跟在咱们后头呢!”
上官漫微诧往人群中一望,那书生果垂首立在人群之中,看到上官漫朝这里回首,面红耳赤忙又扫地一揖。
心中也不知如何想的,竟是开口问:“母后为我选的夫婿可是个什么样的人。”
兰夕未料她有此一问,怔了片刻,很快流利答道:“听说是个读过几年书的秀才,人品家世都是不错……”
“可曾娶妻?”
兰夕又是一愣:“未曾。”
上官漫微微挑眉,不再说话。兰夕却是暗忖,虽未娶妻,也尚年轻,但听闻读了几年书,一直未曾高中,只怕以也无出头之日,何皇后怕在众人前留下口舌,因此才选了年轻俊朗的。不禁小心问道:“殿下要去看看么?”只闻上官漫一声轻笑,再无它话,她竟不敢再说了。
两人举步,那书生踌躇跟了上来,兰夕恼了,上前道:“这位公子,你要跟我们到什么时候?”她嗓音清脆,语气抑扬顿挫,在宫里呆的久了,威仪油然而生,行人均循声望过来,书生窘迫当地,连连作揖:“姑娘着实冤枉了小生,两位姑娘身边无壮丁相伴,万一遇上歹人如何自保,小生……小生只想护送两位姑娘回去。”
兰夕闻言不屑,一双漂亮眼睛上下打量他:“便是公子这身板,要护我们回去?”众人闻言大笑,恰时锣鼓声响,似在为兰夕助威,那书生面色已成酱紫,卑微垂头,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