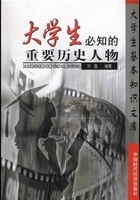第二卷34
谢尔巴茨基公爵离开卡尔斯巴德之后,又去巴敦和启星根看望了几位俄国朋友,正如他所说,为的是感受一下俄罗斯氛围,直到温泉疗养季节快要结束了,他才回到家人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的生活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公爵夫人认为国外的一切都是好的,尽管她在俄国社会有其稳固的地位,可是她在国外尽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欧洲太太,可是装又装不像,因为她本来是一个俄国贵夫人嘛,所以她常常感到别扭。公爵和她相反,认为国外的一切都不好,过欧洲式的生活,使人很不自在,使人感到很累。他始终保持着俄国的生活习惯,他在国外实际上也像个欧洲人,但他尽量做得使别人看他不像个欧洲人。
公爵比以前瘦了,两腮的肌肉也搭拉下来了,但情绪很好,很愉快。他看到基蒂的病完全好了,他就更加高兴了。公爵夫人告诉他,基蒂跟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建立了友谊关系,基蒂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公爵听了很是不安,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常有的忌妒心理,他觉得女儿从此就不再听他的了,他担心女儿会脱离开他的影响,在思想上步入一个他所陌生的新领域。不过这不愉快的消息很快就淹没在和善和欢乐的海洋里了,因为他秉性如此,是个乐天派,特别是从卡尔斯巴德温泉疗养地回来以后。
公爵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同女儿一起高高兴兴地朝温泉走去,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脸上露着深深的皱纹,挺括的硬领子托着他那略带虚肿的两颊。
这是一个晴和日丽的早晨。那一座座整洁、敞亮和带小花园的楼房,那一个个面色红润、手也红润、喝够了啤酒、高高兴兴地走来走去的德国侍女,那明媚的阳光,都令人赏心悦目。他们走得离温泉越近,遇到的病人也就越多。在这优越的德国生活的正常条件下,病人的样子就显得更加可怜。这种反差已经不再使基蒂感到吃惊。在基蒂看来,明媚的阳光,翠绿的草木,音乐的声音,是她所熟悉的这些人的天然背景,是她所密切关心的他们的病情恶化还是好转的天然背景。但是在公爵看来,晴和日丽的六月的早晨,乐队演奏的流行的快活的华尔兹乐曲声,特别是那些走来走去的健康的侍女,跟这些从欧洲各地来到这里的、情绪沮丧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有伤大雅,似乎有点不谐调。
当爱女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很得意,好像又回到了青春时代,可是当他现在迈着矫健的步伐,当他摆动着肥胖的四肢,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很难为情。他现在的感觉和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穿衣服的人的感觉一样。
“你把你的新朋友介绍给我吧!”他用胳膊肘夹了夹女儿的胳膊说。“我现在也喜欢上这讨厌的苏登温泉了,因为它治好了你的病。只是你们这儿的气氛不好,使人有愁闷感。这人是谁?”
基蒂给他介绍了他们遇到的一些他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在花园门口,他们遇见了盲妇人伯尔特夫人和给她带路的人。公爵看到,这位法国老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马上就露出激动的表情,非常高兴。她立刻表现出法国人的那种极大的热情,和公爵攀谈起来。她夸奖他有这样一位好女儿,她当面说了许多赞扬基蒂的话,说她是一颗金光闪闪的珍宝,说她是安慰天使。
“哦,那她就是第二天使了。”公爵笑着说。“她把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天使。”
“啊,瓦莲卡小姐嘛,那可是一位真正的天使,这还用说!”伯尔特夫人应声说。
他们在游廊里遇见了瓦莲卡。她提着一个雅致的红色手提包,急匆匆迎着他们走来。
“瞧,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就像做其他事一样,朴实、自然地做了一个个介乎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然后就像跟其他人谈话一样,立刻朴实、自然地跟公爵攀谈起来。
“我当然知道您,知道您的很多情况。”公爵笑着对她说。基蒂从父亲的笑容中看出来父亲很喜欢她的这位朋友,基蒂心里很高兴。“您这样匆忙,是到哪儿去呀?”
“妈妈在这儿,”她对基蒂说,“她一夜都没有睡,医生劝她到户外待会儿。我给她送针线活去。”
“她可真是第一天使!”等瓦莲卡走了以后,公爵说。
基蒂看得出来,他很想取笑瓦莲卡,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喜欢她。
“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见到你的所有朋友了。”他补充说。“也能见到施塔尔夫人了,如果她肯赏光的话。”
“您难道认识她,爸爸?”基蒂发现父亲提到施塔尔夫人时,眼睛里露出嘲笑的意思,所以惶恐地问道。
“我认识她丈夫,所以也多少认识她一点儿,那还是她成为虔诚派教徒以前。”
“什么是虔诚派教徒,爸爸?”基蒂问道。基蒂认为她如此看重的施塔尔夫人身上那种高尚的品格居然还有一个名称,所以她觉得很吃惊。
“我也不很清楚。我只知道,她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感谢上帝,不管遇到什么灾难,即使丈夫死了,她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好笑,他们总是合不来。”
“这是谁?瞧他那样子多可怜!”公爵问道。他发现长凳上坐着一位病人,个子不高,穿一件棕褐色大衣,白色的裤腿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腿上打出一些奇怪的褶儿。
这位先生把自己的草帽举到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高高的、被帽子勒红了的前额。
“这位是彼得罗夫,是位画家。”基蒂红着脸回答说。“这位是他的妻子。”她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补充说。此时,当他们快走近时,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故意去追一个顺着小路跑开的孩子。
“真可怜!他的那张脸多讨人喜欢!”公爵说。“你怎么不过去?他想对你说什么吧?”
“好吧,咱们都过去吧。”基蒂说着,立刻转过身去。“您今天身体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拄着手杖站起来,羞怯地看了看公爵。
“她是我女儿。”公爵说。“咱们认识一下吧!”
画家点了点头,笑了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等上您了,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歪斜了一下,然后又歪斜了一下,他竭力表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是想来的,可是瓦莲卡告诉我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派人来说过,你们不去了。”
“我们怎么会不去呢?”彼得罗夫脸涨得通红,顿时咳嗽不止,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寻找妻子。“安娜!安娜!”他大声叫道,在他那又白又细的脖子上,一条条青筋像一根根绷得紧紧的绳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叫人告诉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用嘶哑的声音生气地对她说。
“您好,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笑着说,不过她的笑是装出来的,和她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很高兴认识您。”她对公爵说。“我们早就盼着您了,公爵。”
“你怎么叫人告诉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用嘶哑的声音又说了一遍,而且更加生气了,当然也因为嗓子不听他使唤,他不能用声音充分表达他想表达的感情。
“哎呀,我的天,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说。
“怎么会呢,什么时候……”他又咳嗽起来,摆了一下手。
公爵摘了一下帽子,表示再见,就和女儿一起走开了。
“唉呀!”公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家人真不幸啊!”
“是的,爸爸。”基蒂回答说。“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呢,一个佣人也没有,几乎没有什么钱。他只能从画院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她兴致勃勃地说着,尽量压制着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突然对她莫名其妙地改变态度而产生的不安情绪。
“瞧,这就是施塔尔太太。”基蒂指着一辆轮椅说。施塔尔太太躺在轮椅里,头部用枕头围着,穿着浅灰色衣服,上面支着阳伞。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后面站着一位表情忧郁、身体健壮的德国佣工,是给夫人推轮椅的。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站在旁边,基蒂知道他的名字。轮椅周围还逗留着几个病人,他们用奇异的目光看着这位太太。
公爵走到她跟前。基蒂立刻就发现父亲眼睛里流露出嘲笑的神气。他走到施塔尔太太跟前,用出色的法语——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人不多了——极其谦恭和极其亲切地和她攀谈起来。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记得,但是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一番热忱,我必须提一提自己。”他对她说,他摘下帽子,一直没有再戴。
“您是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太太一边说,一边抬起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他,基蒂发现,在她的眼睛里含着某种不满情绪。“我非常高兴,我太喜欢您的女儿了。”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吗?”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说道。她给公爵和瑞典伯爵做了介绍。
“您变化不大。”公爵对她说。“我有10年或者11年没有看见您了,甚为遗憾。”
“是啊,上帝赐给人们苦难,同时也赐给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我常常觉得奇怪,这条命拖下去还有什么用……往那边盖一盖!”她生气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用毯子给她盖腿没有盖好。
“可能是为了做善事吧。”公爵两眼眯缝起来笑着说。
“这不由我们来评判。”施塔尔已经注意到了公爵脸上的表情。“您把那本书给我送来吗,亲爱的伯爵?我非常感谢您。”她对那位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莫斯科上校,就突然叫了一声,他向施塔尔夫人点了点头,就带着女儿同莫斯科上校一起走开了。
“她是我们这里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因为施塔尔夫人不肯跟他结识,所以对她很不满意,于是就有意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她这人就这样。”公爵回答说。
“那么,公爵,您是不是在她生病前就认识她?也就是说在她病倒在床上以前您就认识她?”
“是的,我看着她病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在病床上躺了10年了。”
“她起不来,因为她腿短。她的体形很难看……”
“爸爸,这不可能!”基蒂大声说道。
“这都是那些喜欢制造谣言的人说的,我的好女儿。反正够你的瓦莲卡受的。”他补充说。“唉,这些生病的太太!”
“你说得不对,爸爸!”基蒂激烈反驳说。“瓦莲卡非常爱她。况且她做了很多好事!谁不知道呢!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
“也许是这样吧!”他用胳膊肘夹了夹她的手说。“不过,如果做了好事,又不要别人回报,又不要别人知道,那就更好。”
基蒂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她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她不想对父亲敞开自己的思想。但是,说来也奇怪,虽然她不愿屈从于父亲的看法,不愿让父亲踏进自己的心中圣地,可她感觉到,她一个月来保留在心中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的形象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就像是用一件被扔掉的衣服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当你一旦明白过来,这只不过是件衣服时,人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在她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短腿的妇人,她所以老躺着,是因为她的身体难看,她责备百依百顺的瓦莲卡,就因为瓦莲卡没有把毯子给她盖好。基蒂努力想恢复施塔尔太太在自己心中的过去的形象,但已经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