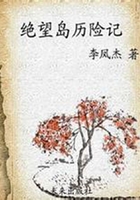第四卷18
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过话之后,弗龙斯基就走出来,到了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停了下来,好不容易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应当到哪儿去。他感到自己受到奚落和侮辱,感到自己有罪,并且失掉了洗涮掉自己屈辱的可能性。他感到自己好像被抛出了那条迄今为止自己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过来的轨道。他生活的一切习惯和准则从前似乎是那么坚定不移,现在突然间显得虚伪和用不上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位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偶然的,并且是稍带滑稽的障碍,现在突然被她亲自召来,被抬到令人顶礼膜拜的高度,这个丈夫在这个高度上显得不再凶恶,不再虚伪,不再可笑,而倒显得善良,平凡和伟大了。弗龙斯基不能不感觉到这点。他俩的角色突然换了一下。
弗龙斯基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鄙,他的正确和自己的荒谬。他感到她的丈夫虽然痛苦,但却是以宽大为怀的,而他自己在搞欺骗时是卑鄙和渺小的。但是他在他自己无端地蔑视的人面前感到自己卑鄙,这只不过是构成了他的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如今感到自己悲痛难言的是,他觉得在最近他对安娜渐渐冷却的热情,现在当他知道了将永远失去她的时候,竟然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了。在她生病期间,他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他仿佛感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了解了她,而且像恋人应当爱的那样爱上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到人的奚落,永久失去了她,只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对自己的可耻的回忆。最为难堪的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双手从他那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的那种可笑的,无地自容的状态。他茫然若失地站在卡列宁家的台阶上,而且不知如何是好。
“要叫辆马车吗?”看门人问。
“好的,叫一辆吧。”
弗龙斯基度过三个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衣服也没脱,就伏在沙发上,双手一合,把头枕在手上。他觉得头很重。回忆和各种奇怪的念头异常迅速、清晰地一一浮上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药水,药水溢出茶匙,时而是那位助产士的白嫩的双手,时而又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跪在病人床前的那种奇怪的姿态。
“睡一觉,忘掉这一切吧!”他就像一位健康的人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相信如果自己累了想睡觉就可以立刻入睡似的。的确,在一瞬间,他的脑袋开始昏昏沉沉的,他开始堕入一种忘却一切的深渊。一种无意识的生活的海浪开始冲击他的头脑,突然间,他的浑身仿佛通过一股极强的电流,他猛地抖动了一下,整个身子都让沙发的弹簧弹了起来,他用双手撑着,恐怖地跪在那里。他的两眼大睁着,仿佛他从来没有睡似的。他刚才还感到头昏脑胀和四肢乏力,现在顿时都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踏入一堆污泥之中,”他仿佛又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这句话,而且看到他就在眼前,他仿佛看见安娜的那张满面红晕的脸,她那双明亮闪光的眼睛正含情脉脉地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不是望着他;他仿佛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的脸上拉开他的双手时自己的那种愚蠢而可笑的样子。他又伸直两腿,以原先的姿势躺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应睡一觉啦!快睡着吧!”他反复地对自己说。但是他一闭上眼睛,却更加清晰地看见赛马前夕的那个难忘的晚上安娜留在他记忆中的那张面孔。
“如今这已不存在了,而且再不会有了,她希望把这一切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可是我没有她就活不下去。我俩怎样才能和好呢?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和解呢?”他大声地说,而且下意识地反复说着这句话。这句反复说的话阻止了堆在他脑海里的新的形象和新的回忆的出现,然而这句话的重复却没有长久地阻止住他的想象。他的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和不久前他受到的侮辱,又一个接一个地异常飞快地在他的心头掠过。“把他的手拉开,”这是安娜的声音。他拿开双手,感到自己脸上有一种惭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依旧躺在那里,尽量想睡着,尽管他感到无丝毫睡着的希望,而且总是低声地重复着由于某种念头而随便出口的话,希望以此去阻止新形象的出现。他凝神静听着,而且仿佛听到了有人用一种奇怪的、疯狂的喃喃声重复着说“我不善于珍惜,也不善于享用;我不善于珍惜,也不善于享用。”
“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我要疯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是。人们究竟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要自杀?”他自己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之后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头边是嫂子瓦里娅亲手缝的绣花枕头。他用手摸了摸枕头的花边,试图回想一下瓦里娅,回想一下他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但是回顾这种不相干的事情是痛苦的。“不,我真应当睡一觉!”他把枕头往上拉了拉,头紧紧地贴在上面,但是要想闭上眼睛还需要作一番努力。他跳起来,坐在那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呢?”他迅速地回想了一遍他同安娜的爱情生活以外的生活的各方面。
“是虚荣心吗?是谢尔晋霍夫斯科伊吗?是社交界吗?是宫廷吗?”他对任何问题都无法认真思考。这一切从前曾有过意义,但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脱掉上衣,解开皮带,露出了长满汗毛的胸脯,以便呼吸得自如些,之后便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们就是这样变成疯子的,”他反复说,“就是这样自杀的……为的是不感到羞愧,”他慢吞吞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凝神屏气,咬紧牙关,走到桌边,拿起手枪,看了一下,把装上子弹的枪口翻过来对着自己,这时陷入了沉思。他面带苦苦思索的表情,低着头,有两分钟时间他手里握着手枪,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思索着。“当然。”他对自己说,仿佛经过一种合乎逻辑的、持续不断的、令人信服的思维过程,他得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结论。实际上,他所确信无疑的这个“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了这样一个回忆和想象的圈子的结果,这个圈子在这一个钟头内在他的脑海里已兜了几十个来回。无非是回忆那些永远逝去的幸福,无非是考虑到毫无意义的未来生活,无非是觉得自己受了奚落,无非是这些思想和感情的不断重复。
“当然,”当他的思绪第三次按照令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圈子转下去的时候,他重复说,于是把手枪贴住了左部的胸膛,用手使劲地攥了一下,好像突然把手攥成拳头似的,他扣了板机。但没有听到枪声,可是他的胸部受到猛烈的一击,他站不住了。他丢掉手枪,本想抓住桌边站住,他的身体晃了一下,便坐在地上,他惊讶地环顾着自己的周围。他仰望着弯曲的桌腿,纸篓和那张虎皮垫子,竟连自己的房间也认不出了。他的仆人急匆匆穿过客厅的脚步声使他醒悟过来。他努力想了一下,才知道自己坐在地板上,看到那块虎皮垫子上和自己手上的鲜血,才明白自己是开枪自杀了。
“真是笨啊!没有打中要害!”他的手一边去摸着找手枪,一边说道,其实手枪就在他的身边,可是他却到远处去找。为了继续找枪,他的身子向另外的方向探过去,他由于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便倒了下去,血流了出来。
那位蓄着络腮胡子、举止文雅的仆人,过去经常向自己的熟人们抱怨自己的神经脆弱,这时他一见自己的老爷躺在地板上,便吓得魂不附体,竟丢下还在流着血的老爷,跑去求救。一小时后,他的嫂子瓦里娅来了,还同时带来了三位她四方求救请来的医生,在医生的帮助下,她把受伤的弗龙斯基抬到床上,留在他身边照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