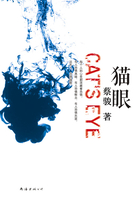第四卷2
回家后,弗龙斯基在家里看到安娜写来的一个纸条。她写道:“我生病了,内心很痛苦。我不能够出门,但也不能不再见到您。请您今晚来我这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七点钟去开会,十点钟前才回来。”他乍一想有点奇怪,她为什么不顾丈夫不让她在家里接待他的要求,而叫他直接去她家,结果他还是决定去一趟。
弗龙斯基在今年冬天晋升了上校,离开了团部,一人独居。吃罢早饭,他立刻躺在沙发上。他回忆着最近几天里目击的一些丑恶的场面,这些回忆与安娜的形象和在猎熊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的形象联系交织在一起,5分钟后,他便睡着了。他醒来已到暮色时分,吓得浑身发抖,他赶紧点着一支蜡烛。“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啦?我梦见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噢,是的。那个胡子乱糟糟的,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农夫好像弯下腰去干什么,突然他用法语说出某些奇怪的词来。是的,此外我什么也再没有梦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梦为什么这么可怕呢?”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那位农夫和他说出的那几个令人费解的法语单词,一阵恐怖又让他的后背感到冰凉。
“多么荒唐啊!”弗龙斯基心里想了想,同时看了一眼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摇铃叫来仆人,急忙穿好衣服,走到台阶上,全然把那场梦抛到脑后,只是担心要去迟了。当他的车停在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前时,他又看看表,知道离9点还差10分钟。门口正停着一辆套好一对灰马的又高又窄的马车。他认出这是安娜的马车。“她这是要去我那里,”弗龙斯基想,“这样最好不过了。我真反感走进这幢房子。但是反正一样,我又不能躲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之后他带着从小养成的无所顾忌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下了雪橇,向门口走去。门开着,看门人一只胳膊上搭着毛毯,叫马车驶近点。弗龙斯基从不注意琐碎小事,然而却在此时发现了看门人看他那一眼时流露出来的惊讶神情。弗龙斯基在门口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几乎撞了个满怀。煤气灯口直接照着卡列宁的那张头戴黑帽下的没有血色的、两颊凹陷的脸和那条从海狸皮大衣开口处尤为显眼的白色领带。卡列宁的两眼目光呆滞,死死地盯着弗龙斯基的脸。弗龙斯基鞠了一躬,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咬咬嘴唇,用手往上掀了一下帽子以打招呼,之后就走了过去。弗龙斯基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坐进马车,从车窗口接过了毛毯和望远镜,就消逝了。弗龙斯基走进前厅,他紧皱着眉头,眼睛闪着一种凶狠而傲慢的光芒。
“瞧,是这种处境!”他想,“假如他为维护自己的名声与我争斗的话,我还能够反击一番,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但是这种软弱或是卑鄙……他置我于骗子的处境,那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想这样。”
自从在弗列达花园与安娜表白之后,弗龙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由自主地屈从于安娜的怯弱,安娜已完全委身于他,只等待着他来决定她的命运,并准备好屈服一切,而弗龙斯基也早已不像他曾经想过的那样,希望这种关系结束。他的追求虚荣的计划又退到次要地位,而且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走出了那个一切都界限分明的活动圈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感情中,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他愈来愈强烈地眷恋着她。
他在前厅里就已听到她那渐渐走远的脚步声。他明白了,她曾在这里等着他,倾心听着他来的动静,现在,她返回客厅去了。
“不行!”她一见到他就喊了一声,她刚喊出声,双眼里就涌满了泪水,“不行,如果关系这样继续下去,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发展得更快!”
“怎么啦,我亲爱的?”
“你说怎么啦?我苦苦地等了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与你争吵。当然,你是不能来。不,我不能再这样了!”
她把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用热忱深情的,同时又像是探询的目光久久地看着他。她琢磨着他那张她这段时间里没看见过的脸。她就像每次幽会时一样,总是把想象中的他(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在现实中不可能有的形象)与从前的他联想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