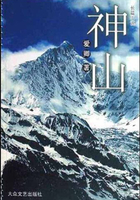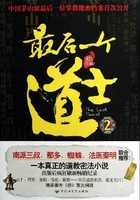第五章 婚 筵 (2)
摩莱尔知道再抗辩也是无用,一个佩了执命绶带的军官已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一尊冷酷无情的法律的化身。但老邓蒂斯却急向警官走去,——因为有些事情是一个父亲或母亲的心所无法了解的,他拼命求情,他的恳求和眼泪虽然毫无用处,但他那极度的失望却引起了警官的同情。“先生,”他说,“请你冷静一点,令郎大概是疏忽了一些海关方面或者检疫方面的条例,极可能在回答几个问题以后就释放的。”
“是怎么回事?”卡德罗斯横眉怒目地问邓格拉斯,后者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他答道,“我像你一样,对于目前这件事根本莫名其妙,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懂。”卡德罗斯于是四顾寻找弗南,但弗南趁混乱时溜走了。
前一天的情景现在极清晰地回到脑子里来,他现在目击的这场滔天横祸使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哼!”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向邓格拉斯说,“这个,我想是你昨天那套把戏里的一部分吧?假若如此,玩把戏的那个家伙真该死!这种行为太下流了。”
“废话!”邓格拉斯反驳道,“你明明知道我把那张纸撕得粉碎了的。”
“不,你没有!”卡德罗斯答道,“你只把它抛在一边,后来肯定有人捡起来了。我看见它被抛在一个角落。”
“住嘴!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你那时喝醉了!”
“弗南到哪儿了?“卡德罗斯问。
“我怎么知道?”邓格拉斯回答,“大概是照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吧,不管他在哪儿,我们且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邓蒂斯和他的朋友一一握手,然后走到那官员身边,说:“请诸位放心,我去解释一些小误会,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
“唔,一定!”邓格拉斯接着说,他现在已走到大家面前,“我相信只不过是一点误会而已。”
邓蒂斯夹在警官和士兵的中间走下楼去。门口有一辆马车在等候他。他钻入车里,接着进去两个兵和那警官,马车就向马赛那方面驶去。
“再见,再见,最亲爱的爱德蒙!”美茜蒂丝在走廊上伸出手臂大声对他喊着。
最后的那一声呼喊对囚徒来说就像他未婚妻粉碎的芳心里所发出的一阵呜咽。他从车厢中伸出头来喊道:“再见,美茜蒂丝。”于是马车转过圣?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不见了。
“你们每个人就在这儿等我!”摩莱尔先生喊道,“我这就找一辆马车赶往马赛去,等我的消息吧!”
“太好了!”许多声音异口同声地说道,“快去快回。”
摩莱尔先生离开以后,那留下的人都吓呆了。老爹和美茜蒂丝木然地呆立着,但最后,这两遭受同一打击的可怜的牺牲者终于抬起他们的双眼,百感交集地拥在一起。
这时弗南又出现了,他用一只手颤抖的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急急地吞了下去,然后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美茜蒂丝这时已从老人的怀抱里半昏迷地倒在一张椅子上。弗南的座位就在她的旁边,他本能地把椅子拖后一点。
“是他!”卡德罗斯低声对邓格拉斯说,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弗南。
“我倒不这么认为,”另一个回答,“他太蠢了,绝想不出这样的一个计谋。我只希望那个造孽的人自作自受。”
“你怎么不说出那个出谋划策的人!”卡德罗斯说。
“当然了,”邓格拉斯说,“一个人随便讲的话可不能全都叫他负责!”
“哼,随便讲话的就得首先负责。”
这时,关于被捕这件事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讨论着。
“邓格拉斯,”其中有一人说,“你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想,”邓格拉斯说,“可能是邓蒂斯的船上被搜出了违禁的小东西。”
“假如他这样做,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邓格拉斯,你是船上的押运员呀!”
“我只负责船上所装的货物,我知道船上装着棉花,是从亚历山大港潘斯德里先生的货仓和士麦那潘斯考先生的货仓里装上船,我所必须知道的不过这些,至于别的东西,不归我的管辖范围。”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可怜的老爹说,“我的孩子昨天告诉我,说有一小盒咖啡和一点烟草带给我!”
“你看,可不是!”邓格拉斯宣称说,“现在把祸根找出来了,一定是海关关员当我不在的时候搜船,发现可怜的邓蒂斯所藏着的宝贝了。”
但美茜蒂丝不相信她爱人被捕的这种解释。她一直努力克制着哀愁,现在猛然地爆发成歇斯底里的呜咽。
“来,来,”老人说,“心放开些,我可怜的孩子,邓蒂斯不会有事的。”
“有希望!”邓格拉斯也说。
“有希望!”弗南想说,但他却梗住了。他的嘴唇在动,但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好消息!好消息!”站在走廊上的人中有一个喊道,“摩莱尔先生回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那位朋友已经释放了。”
美茜蒂丝和老人冲出去迎接船主,在门口碰到了他,摩莱尔先生的脸色非常苍白。
“情况如何?”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唉,诸位,”摩莱尔先生发愁地摇摇头回答,“事情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得多。”
“啊,他可是无辜的呀?”美茜蒂丝说。
“那我相信!”摩莱尔先生回答说,“可是他依旧被控为——”
“什么罪名?”老邓蒂斯问。
“指控他是拿破仑的信使。”
我们的读者定能记得,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罪名是多么可怕。美茜蒂丝苍白的嘴唇里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而心碎的父亲则奄奄一息地倒在一张椅子里。
“邓格拉斯!”卡德罗斯低声说,“你骗了我。——昨天晚上你说的那个把戏真的玩出来了,我知道了,但我不忍心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头子和一个美丽无辜的姑娘被你活活逼死。我决定要把这一切告诉他们。”
“别作声,你这傻瓜!”邓格拉斯抓住他的手臂狠狠地说,“不然我不负责你本身的安全。谁能说邓蒂斯究竟是无罪还是有罪?船的确靠过爱尔巴岛,他曾离船在岛上过了一整天。现在,假如在他身上找到有关的信件或其他文件,那凡是帮他说话的人都要算作他的从犯办理。”
凭着天生见风使舵的自私心,卡德罗斯立刻觉察到这一番话的分量。他用充满恐惧和忧虑的眼睛望望邓格拉斯,然后采取了进一步退二步的态度。
“那么,我们等着瞧吧。”他轻声地说。
“当然罗,”邓格拉斯回答。“我们等着瞧吧。假如他是无辜的,当然就会释放,假如的确有罪,那么也犯不上为他的阴谋受牵连。”
“那么我们走吧,我实在受不了。”
“同意。”邓格拉斯回答。他能找到一个一同退场的同伴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别管这件事,其余那些人走不走我可管不着。”
他们离开以后,弗南携了美茜蒂丝的手,领她回迦太兰村去,他现在又成了那位青年姑娘的保护人了,而邓蒂斯的一些朋友则护送那心碎的父亲回家。
爱德蒙被控为拿破仑党专使而被捕的消息在城里迅速流传开来
“你能不能相信这种事情,我亲爱的邓格拉斯?”摩莱尔先生问,他在回城后打听邓蒂斯的新消息途中,追上了他的押运员和卡德罗斯,“你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噢,您知道,我已经告诉过您,”邓格拉斯回答说,“我认为他在爱尔巴岛下锚这件事是非常可疑的。”
“你这种怀疑除了对我以外没有对别人提起过?”
“当然没有!”邓格拉斯回答。然后又低声耳语道,“你知道,因为令叔波立卡?摩莱尔先生曾在先朝当过官,而且关于这件事又不怎么隐讳,所以您也蒙着莫大的嫌疑,人家以为您也不满于拿破仑的被废。假如我向人透露了我心中的怀疑,我得顾忌到会伤害到爱德蒙和您。我很明白,像我这样做属下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先通知船主,有许多事情他实在应该极小心地掩饰,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
“很好,邓格拉斯,很好!”摩莱尔先生答道,“你是一条好汉子,本来,假如那可怜的爱德蒙做了船长,我也为你打算过了。”
“怎么样,先生?”
“我事前曾问过邓蒂斯,问他对你的意见如何,是否不大愿意让你继续任职,——因为我已经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怎么样。”
“他怎么说?”
“他觉得你是有可抱怨之处,至于为了哪一件事,他可没有明说,但他说不论是谁,只要得船主的信任,他也必定予以尊敬。”
“伪君子!”邓格拉斯低声地骂了一声。
“可怜的邓蒂斯!”卡德罗斯说,“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呵!”
“但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形势之下,”摩莱尔先生继续说,“我们不能忘记埃及王号现在还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之中。”
“噢!”邓格拉斯回答说,“反正我们三个月之内还不会离开这个港口,但愿在出海之前邓蒂斯能释放出来。”
“那我当然毫无异议,但在这期间我们怎么办呢?”
“哦,这期间有我在这儿,摩莱尔先生,”邓格拉斯答道,“你知道,我管理船只的本领,并不亚于经验最丰富的现任船长。假如您接受我的效劳,对您也是很有利的,因为邓蒂斯一旦获释,埃及王号上的人事就不必调动,只要邓蒂斯和我各做本职工作就行了。”
“谢谢,我的好朋友,谢谢你这个好主意。——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立刻授命你担任埃及王号的指挥,并监督卸货,不论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业务总不能让它受损害。”
“请相信我的热心和谨慎吧,摩莱尔先生,但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被允许到狱中去探望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呢?”
“我见到维尔福先生以后,就马上可以让你知道,我会尽力使他庇护爱德蒙。我明白他是一个激烈的保王党。但是,除了这点和他那检察官的地位以外,他也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我想还不至于是一个坏人。”
“或许不是坏人,”邓格拉斯道,“但我听说,他野心极大,而野心是最会使人心变硬的!”
“好吧,好吧,”摩莱尔先生说,“我们瞧吧,你赶快到船上去吧。我到船上来找你好了。”说着那位可敬的船主就离开那两位朋友,向法院方向走去。
“你看,”邓格拉斯对卡德罗斯说,“事情变化了吧。你现在觉得还有什么要为他辩护的没有?”
“虽然没有,但我觉得开玩笑一样地让人遭受如此下场,简直太可怕了。”
“但我倒要问问,是谁把开玩笑的话传出去的?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弗南。你当然很清楚,我当时把那张纸丢在房子里的角落里的。——真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它撕碎了呢。”
“噢,不!”卡德罗斯答道,“那一点我倒可以答复你,你没有。我明明白白看见它是揉皱了丢在凉棚角落里的,我希望现在还能在那儿看见它。”
“嗯,如果你的确看到过,那个就算了吧,一定是弗南把它拾了起来,另外抄写了一遍,或许就把那封信抄都懒得抄。现在我记起来了,天哪!他或许就把那封信送去了!我真运气,那笔迹是伪装过的。”
“那么,你知道邓蒂斯是参与造反的吗?”
“不,我早说过,我认为这件事只是开玩笑,再没有其它的意思,但似乎是像哈里昆一样,我倒在玩笑中道出了实情。”
“可是,”卡德罗斯驳道,“我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或至少应与我无关。你瞧吧,邓格拉斯,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个都倒霉的。”
“瞎说,”邓格拉斯用冷峻的眼光盯住卡德罗斯,“假如这件事会带来什么祸,那就应该落到罪人头上,而那个人,你知道,是弗南。我们怎么会卷在里面呢?我们只要自己保守秘密,不声不响地,对这件事不要泄露一个字就得了,你可以看到那风波就会过去,而我们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好吧!”卡德罗斯应了一声,就挥手告别邓格拉斯,迈步向米兰港走去,他的头晃晃的,一面走一面嘴里念念有词,看来好像在动脑筋。
“好了,现在,”邓格拉斯自言自语道,“一切都已遂了我的心愿了,我已临时当上了船长,而且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只要卡德罗斯那个傻瓜能听话不多嘴就好了。我只怕邓蒂斯会放出来,但,呸!他已经落到法院的手里了。”他又带着微笑说,“而法院自有公道。”说着,他就跳进一只小艇,吩咐摇到埃及王号上去,因为摩莱尔先生会在那儿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