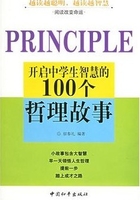第十九章 又发病了 (2)
“你说得没错。相信我,我肯定能把你救活的!而且,尽管你很难过,但我认为你好像没有上次那么痛苦。”
“别弄错了!我没有那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来忍受了。在你这种年龄,对生命是有信心的。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但老年人对死看得比较清楚。噢!来了!来了——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理智也消失了!你的手呢?邓蒂斯!再会!——再会了!”于是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抬起身来,说,“基督山!别忘了基督山!”然后他倒了下去。这一场发作真厉害。在那张痛苦的床上,只见扭曲的四肢,肿胀的眼皮,带血的白沫和一个毫无生气的躯体——那个刚刚还躺在那里的聪明人就这样走了。
邓蒂斯拿起那盏灯,把它放到床头一块凸出的石头上,颤抖的火苗把它那稀奇古怪的光芒倾泻到那失了常态的面孔和那一动不动的僵硬的身体上。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等待那施用救命良药的时机到来。
当他认为时机到来了的时候,他拿起小刀撬开牙齿,这一次没有像上次咬得那么紧,他一滴一滴地滴下去,直到第十二滴,然后等着。瓶里大约还有两倍于滴下去那么多的数量。十分钟,一刻钟,半个小时过去了,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他浑身直冒冷汗,用他的心跳来计算时间。然后他想起该做最后一试了,他把瓶子放到法利亚紫色的嘴唇上,牙齿仍然开着,他把全部药水都倒进了他的喉咙。
药水使老人像遭受了电击一样。老人的四肢开始猛烈地抖,他的眼睛渐渐地瞪大,让人看了禁不住害怕。他尖叫了一声,然后又一动不动了,只剩下眼睛仍然大张着。
半小时,一个小时,又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这时,万分悲痛的爱德蒙斜靠在长老身上,用手按住他的心脏,觉得那身体在一点一点地冷却下去,心脏跳动也越来越缓慢,终于完全停止。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时,那脸就变成了青灰色,眼睛依然张着,但目光无神。这时是早晨六点钟,天刚蒙蒙亮,微弱的晨曦穿入黑牢,使那将熄的灯光变成了苍白色。死人的脸部本来浮动着奇怪的阴影,让人看上去觉得还有点生气,现在连阴影都消失了。在这日夜交接的时刻,邓蒂斯还有点怀疑,但一到白天彻底到来时,他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和一具尸体在一起,于是,一种极端的恐怖笼罩了他,他不敢去碰那挂在床沿外面的手,也不敢再去看那双茫然的眼睛——他曾多次想使它合上,但是无济于事,它始终还是开着。他把灯熄掉,小心地把它藏好,然后就离开了这里,尽可能把他进入秘密地道的那块大石头盖好。
好险!因为狱卒刚好过来了。这一次,他先到邓蒂斯的地牢,然后向法利亚的黑牢走去,手里端着早饭和一件衬衣。很明显,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邓蒂斯的心里焦急起来,迫切地想知道在他的朋友的黑牢里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于是他又钻进地道,当他到达那一端时,恰好听到那狱卒的尖叫声,在喊人来帮忙,又有几个狱卒跑了过来,接着又听到那种均匀的步伐,显然是有士兵过来了,他们的后面是堡长。
爱德蒙听到床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他们在搬动尸体,又听到堡长叫人把水洒到犯人脸上的声音,看到这些都无效后,就派人去请医生。然后堡长走了,邓蒂斯听到了几句怜悯的话,还夹着残酷的哄笑。
“好了,好了!”一个狱卒说,“这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啦,祝他一路顺风!”
“他虽富有百万,但却连买件寿衣的钱都没有!”另一个说。
“噢,”第三个接上一句,“伊夫堡的寿衣并不贵!”
“可能,”先前说过话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个说,“因为他是长老,他们也有可能会多破费一些。”
“他们可能会赐给他一个布袋。”
爱德蒙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但却弄不懂其中的涵义,说话声很快就停止了,那些人似乎都离开了,但他还是不敢贸然进去,他担心他们会留下一个人看守尸体。所以他仍旧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一小时过去了,他又听到有人过来了,这是堡长和医生还有随从回来了。房间里沉寂了片刻,显然医生在检查尸体,不久,问话就开始了。
医生分析了病人的情况,宣布他已经死了。接着就传来了一阵漠不关心的问答,使得邓蒂斯非常气愤,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他一样怜爱那长老。
“我觉得非常遗憾,”在医生断定老人真的死了之后,堡长答道,“他是一个不声不响,安份守己,傻里傻气地自寻开心的犯人,简直用不着看守。”
狱卒接着说,“完全用不着看守,我敢肯定,他在这儿住上五十年也不会逃走。”
“但是,”堡长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办的,并不是说您的诊断不确实,也不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医学,只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对于犯人的死亡断定得十分确实。”
房间里又静了下来,邓蒂斯还在偷听,他猜测医生又在检查尸体。
“您放心吧,”医生说,“我敢担保他确实是死了。”
“您知道,阁下,”堡长坚持说,“单凭检验我们是不能满足的。不管外表看上去如何,还是请您按法律所规定的正式手续办理来了结您的责任吧。”
“好吧,去烧块烙铁来,”医生说,“但实在没必要这么做。”
这个命令不禁使邓蒂斯浑身发冷。他听到匆忙的脚步声,门的格格声,人们的来去声。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狱卒进来说:“火盆来啦,烧着啦。”
房间里又静了下来,然后有烙肉的声音,那种令人作呕的怪味甚至穿透了墙壁,直传到邓蒂斯的鼻孔里。一闻到这种气味,青年的额头上挂满了冷汗,差点儿没昏过去。
“您看,阁下,他真是死了,”医生说,“烧脚跟最厉害,这个可怜虫这样倒治好了他的傻病,,他从监狱生活里解脱出来啦。”
“这人是叫法利亚吗?”一个陪堡长同来的官员问道。
“不错,先生。据他来说,这是一个古人的名字,他的学问倒是满大的,而且只要不提他的宝藏,他的理智也很清楚。但一提这件事,他就固执得要命。”
“这种病在医学上叫做偏执狂。”医生说。
“你没有听到他抱怨什么吗?”堡长对负责管理长老的狱卒说。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大人,”狱卒回答道,“从来没有。相反,有时他还给我讲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老婆病了,他给我开了一张药方,果然把她医好了。”
“哦,哦!”医生说,“我倒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位同行与我竞争呢,但我希望,堡长阁下,您尽可能地把他的后事办好一些。”
“这您尽管放心。我们尽可能找一只最新的布袋来装他。这样您满意吗?”
“我们是否必须当着您的面把最后的手续办好,大人?”一个狱卒问。
“那是自然。但是要尽快!我可不能整天留在这儿。”于是进进出出的声音又响起来。过了一会儿,一阵揉蹭麻布的声音传到了邓蒂斯的耳朵,床板咯吱咯吱地响,地上响起一个人举起一样东西的脚步声,然后床又受压咯吱地叫了一声。
“就在今天晚上。”堡长说。
“要举行弥撒吗?”随从之中有一个人问。
“那可不行了,”堡长答道,“堡里的神父昨天请假去耶尔旅行了,要过一个时期才能回来。我告诉他,在他离职的这段日子里,我会照顾犯人的。这位可怜的长老要不是急着要走,他是可以享受安灵祭的。”
“呸,呸!”医生说,干他这一行的大多数都不信鬼神,“他本来就是个神父。上帝会尊重他的职业,不会派一个神父来给他送葬,和他开这么一个鬼玩笑的。”这残酷的玩笑后面是一阵大笑。这时,人们仍在继续包缝尸体。
“就在今天晚上。”堡长在工作完毕之后说。
“几点钟?”一个狱卒问。
“十点或十一点钟。”
“我们要看守尸体吗?”
“没有那个必要。只要把牢门关上,就当他还活着吧。”
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门链格格地响了一声,然后是上锁的声音,以后就是一片静寂了——死的寂静,它拥抱了一切,甚至拥抱了那年青人冰冷了的灵魂。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用头把那块大石顶了起来,仔细地环顾室内。室内一个人也没有,邓蒂斯于是离开地道,跳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