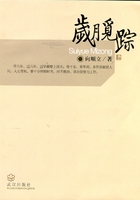第一部第三章 (1)
到了街上,杜洛华又没主意,不知该干什么才好。
他真想痛痛快快地跑一阵,尽情地挥洒一阵。他于是一面信步向前,一面憧憬着未来,呼吸着夏夜清凉的空气,然而,瓦尔特老头要他写文章一事,始终索绕在他的脑海,于是,他决定立刻回家,投入工作。
他大步向回走,沿着环城大街,一直向自己住的布尔索街走去。他住在一栋七层的楼房里,一共二十户,住的全是工人和一般市民。楼梯一团漆黑,他只好划着火柴照明。楼梯上到处是纸屑、烟头、菜帮子,脏极了。看到这样子,他一阵恶心,真想马上搬出去,搬到有钱人住的、铺地毯的干净住宅区去。现在住的这栋楼里,上上下下有一种浓浊的怪味,有饭菜味、厕所味、油味,以及旧墙壁的发霉味儿,再大的穿堂风也吹之不散。
他的房间在六楼,窗子正对着西城路宽宽的阴沟,下面恰好是巴蒂廖尔车站附近的隧道口,俯首下望,如临深渊。此刻,他正打开窗子,靠在生锈的栏杆上。
黑漆漆的隧道口,亮着三盏红色的信号灯,一动不动,像猛兽的三只大眼。稍远又有几盏,再远,又是几盏。断断续续的汽笛声,有的很清晰,有时又几乎听不见。汽笛声抑扬变化,有时像人在喊口令。其中一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亮,猛的,一道巨大的黄光,轰隆轰隆地奔过来了。一列长长的车厢冲进了隧道。
于是,杜洛华自语道:“行了,工作去吧!”他把油灯放在桌上,正想动手写,猛地发现家里只有一叠信纸了。
也好,就用它吧!他把信纸摊开,拿起笔蘸好了墨水,用他漂亮的笔体工工整整写下了题目:
非洲从军行
之后,他开始思考第一句话从何说起。
他手托前额,两眼盯住面前铺开的白纸。
写什么呢?宴会上讲过的一切,现在他全忘光了。法国也好,趣事也好,统统消失了。他忽然眼前一亮“我应该从动身时说起”。于是,他写道:“公元1874年5月15日前后,疲惫不堪的法兰西历经了天灾人祸的磨难(指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失地赔款以及巴黎公社起义一段岁月。),正在修养生息……”
他又停了下来,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引出自己上船的情形。沿途见闻,以及最初感受。
考虑了十分钟,他决定把这段开场白放到明天再写,还是先把阿尔巴尼亚描写一番吧!
于是,他又在纸上写道:“阿尔及尔是一座洁白的城市……”他忽然又写不下去了。他脑海里又浮现出了这座阳光明媚的美丽城市,低矮的平房像瀑布一样,从山顶一直伸展到海滨。可是,他殚思极虑,却找不出任何文字可以表达当时所见所闻和内心所感。
又呆了一会儿,他才想出一句:“城市的居民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他突然把笔往桌上一扔,站了起来。
他看见自己每天穿的衣服,口袋空空的,又皱又瘪,肮脏又俗气,像殓尸房的旧衣服一样杂乱地堆在他睡的小床上,铁床中间已被他的身体压凹了。他那顶惟一的丝质礼帽正仰口朝天地躺在藤椅上,仿佛在等待布施。
房间的墙上糊着灰底蓝花的壁纸,斑斑驳驳,满是油渍,由于年代久远,谁也搞不清这些油污到底是怎么弄的,也许是按死在上面的虫蚁,或者溅上去的油珠,或者是染了发蜡的指印甲,也可能是涮洗时从脸盆里飞出去的泡沫。巴黎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大都这副样子。一切都显得那么寒酸,让人无地自容。看着自己生活的如此潦倒,不禁怒火中烧,心想,非立刻摆脱这种境况不可,从明天起,一切都该结束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猛地又涌起一股子工作激情,于是又坐回到写字桌旁,苦苦地寻词摘句,想把阿尔及尔那美妙而奇特的风光描述一番。阿尔及尔是非洲的一个门户,非洲是一个辽阔而神奇的大洲,那里有游牧的阿拉伯人,还有黑人,非洲又是一个人迹罕至、风情怪异的大洲,那里生活着似乎专门为神话故事而创造出来的珍禽怪兽,那庞大的鸵鸟,神妙的羚羊,形状怪异、长相可笑的长颈鹿,稳重的骆驼,丑陋的河马,凶猛沉重的犀牛,人类的表兄弟大猩猩,等等,这些家伙我们有时在动物园里可以看到。
他隐隐约约又有了一些眉目,然而,要他口头叙述一番还可以,可落在纸上却难了。他怨天怨地,心急如焚,却又一筹莫展。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手心里全是汗,血液在太阳穴里突突直跳。
他的目光落在了洗衣服的账单上,那是当天晚上洗衣房送上来的。刹那间,喜悦的心情,远大的报负,对前途的信念,一切统统崩溃了,他感到一阵绝望,完了,一切全完了,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不可能成为人物的。他感到自己贫乏,无能,毫无用途,注定要被淘汰的。
他又回到窗前,凭栏远眺。恰在此时,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火车隆隆地钻出了隧道,穿过原野,驶向大海。杜洛华不禁想起了远方的父母。
这列火车将会在离他故居十几里的地方经过,他仿佛又看见了父母的那间小屋,在康特勒村口的山坡上,俯瞰着卢昂(塞纳河下游的大的市场。)和辽阔的塞纳河平原。
他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酒店,名曰:“美景酒店”。每逢周末,附近的中产阶级都会到这里来用午餐。父母一心盼儿子出人头地,所以送他上了中学,毕业之后,他没有通过全国会考,便又去当了兵,打算将来当上军官,上校,直至将军。然而,五年的服役期还未结束,他便厌倦了军旅生涯,只身来到巴黎碰运气。
他父母对他的各种盼望早已破灭,只希望他能留在父母身旁,然而他服役期一满,便来到巴黎,以为会混个前程。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时势会造就他的胜利,然而究竟是何种时势,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他相信自己能赢得机遇。
他在戍地的团队里一直很顺手,运气也不错,在有身份的上层社会里也曾有过几次艳遇。他曾经勾引到一个收税官的女儿,这姑娘宁愿丢下一切与他私奔。他还与一个牧师的妻子有一手,这个女人被他遗弃后,失望之余,差点投河自尽。
他的同伴谈起他时,都说他是一个“聪明,狡猾,遇事总有办法的家伙。”他自己也一心要成为一个“聪明、狡猾、什么也难不住的人”。
他在部队驻地每天过着单调的生活,耳闻目睹了在非洲发生的抢劫行为和非法谋利,尔虞我诈的风气,军队里的荣誉观念和假充好汉的行为,爱国主义的感情,士官间的哥们义气,以及军人的虚荣心等,这一切不断熏陶、鞭策、深化着他那诺曼底人的性格,使他的脑子成了一个三层杂物箱,里面什么都有。
然而,在他的心灵中,控制一切的却是向上爬的欲望。
每天晚上,他都会不知不觉地想入非非,幻想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一位银行家或其他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对他一见钟情,结为眷属,于是他的梦想一下子会成为现实。
突然,一声刺耳的汽笛声划破了他的梦境,一辆机车像离穴的大兔子,猛地窜出隧道,沿着铁轨飞速地奔向停车场,到那里睡觉去了。
他带着始终徘徊在脑海中的模糊而甜美的希望,向黑暗中一阵乱飞吻。这是他给幻想中的多情美女所送上的爱情之吻,给他梦里的飞黄腾达送上的贪欲之吻。然后,他关上窗口锁好,一边脱衣服,一边自我妄想道:
“算了,明天再说吧,今晚脑子太乱。再说,喝了那么多酒,怪不得没有思路呢!”
他上了床,熄了灯,差不多立刻便睡着了。第二天,他很早就醒了。一个心中有事的人总是醒得很早的。他下了床,推开窗子,用他的话讲,是喝上几杯新鲜空气。
对面,宽阔的壕沟一侧,马罗街的房子沐浴着早上的阳光,仿佛上了一层白色的油彩,闪闪发亮。右面,远处,浅灰色的晨雾,仿佛飘在地平线上的一块面纱,模糊而又透明。薄雾后面,是阿让特丘陵,萨努瓦高地,还有奥尔热的民房朦胧的身影。
杜洛华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过了好几分钟才喃喃说道:“这样好的天气,那边风光肯定错不了。”他忽然又想起自己工作在身,而且拖延不得,于是,他给门房的儿子十个苏,叫他到自己办公室去请个假。
他又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拿起笔,蘸好墨水,继续苦苦思索,半晌,依旧什么也想不出来。
然而他并不放弃,心想:“没什么,这不过从未接触过而已,干记者也跟其他行业一样,得先入了门儿才成。头几次怎么也得让别人指导一下……我这就去找福雷斯蒂埃,不出十分钟他就能给我理出个头绪来。”
想到这儿,他穿好了衣服。
走在大街上,他忽然想起,他朋友昨夜一定睡得很晚,这时候去造访,未免太早了。于是,他沿着环城大街,在树下慢慢地散步一会儿。
9点还不到,他来到索挽公园。公园里刚洒过水,空气清新宜人。
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又开始想入非非了。一个衣着华贵的小伙子在他面前来回走着,仿佛在等一个约会。
那位女士来了,带着面纱,步履匆匆,和那个小伙子握了握手,两个人便挽起手臂,一起走了。
突然,爱情的渴望,像汹涌的波涛,冲进了杜洛华的心,他需要一种名门闺秀式的浪漫高贵的爱情。他又站起来,继续向前走,脑子里又浮现出福雷斯蒂埃,这小子可真走运!
来朋友家时,朋友正准备出门。
“是你呀!现在登门,有什么事吗?”
杜洛华见他正要走,顿觉一阵不好意思。喃喃地说:
“是这样……那篇文章……瓦尔特先生让我写的那篇……我一时写不出来,你知道,这很正常,因为我从未写过,干什么都得先熟悉了,然后才成……将来我一定会干好,我很有信心,可我现在一筹莫展……想法我是有的可就是无法表达在纸上……”
说到这儿,他便停下来,更加犹豫。福雷斯蒂埃狡黠地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