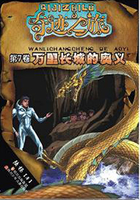第二部第二章 (1)
杜洛华夫妇回巴黎已经两天了。新闻记者一直重操旧业,一边忙着准备离开社会新闻编辑部专攻政治,以便把福雷斯蒂埃的职务全部接转过来。
一天晚上,他兴冲冲地往住过的寓所里赶,他迫不及待的 拥吻她的妻子。他已完全拜倒在他妻子的石榴裙下,不知不觉已对她百依百顺。在路过洛雷特圣母街一家花店时,忽然他又想给玛德莱娜买一束花,于是他买了一大把刚开的玫瑰和一堆香喷喷的花蕾。
上楼走向新居的路上,每经过一层楼都要停下来,得意的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看见镜子就不禁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这房子的情景。
他按了门铃,他忘了带钥匙。那个仆人来给他开门,当初他是听妻子劝告才把这个仆人留下来。
乔治问:“太太回来了吗?”
“回来了,先生。”
经过饭厅的时候,他发现摆了三份刀叉,好生奇怪,客厅的门帘没有放下来,玛德莱娜正把手里拿着的玫瑰往壁炉上的一个花瓶里放。巧的是那束玫瑰与他刚买的一模一样。他一肚子烦燥,似乎有谁故意拎着向他妻子献殷勤,夺走他期待的一切欢乐。
他走进去问道:“今晚有客人?”
玛德莱娜头也没回,边摆弄着花,边答:“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我的老朋友沃德雷克伯爵今晚要来,这已是惯例,每星期他一定会到这里吃晚饭。”
杜洛华有点发愣;“是吗?好极了!”
他真想把手里那束玫瑰藏起来,甚至扔掉,可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你看,我送你一束玫瑰花。”
玛德莱娜霍的转身过来,脸上堆满笑容:
“噢!你真好!你竟能想到给我买花!”
说着,她就展开双臂,把嘴唇凑了过去。杜洛华见到她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方才稍感宽心。
她闻了闻玫瑰,兴高采烈地马上把花插在一个还空着的花瓶里,就在刚才那个花瓶前面。插好后,好像还爱不释手,喃喃的说:
“我真高兴!你瞧,我的壁炉现在可漂亮了。”
门铃响人到。伯爵缓步走进来,仿佛走进自己家里,毫无拘束。他先是很洒脱地吻了吻少妇的手,然后转身热情的把手伸给她的丈夫,客气的问候:
“你好吗?亲爱的杜洛华?”
新闻记者吃了一惊,他原来一直态度生硬,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眼前的他和蔼可亲,杜洛华赶紧挤出笑脸。不屑五分钟,两人似乎就已经相识了十年,成了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
见此情景,玛德莱娜也容光焕发的说:
“你们两人聊吧,我去厨房看看。”
两个男人目送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
她回来时,发现他们正在谈戏剧,讨论一幕新戏。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彼此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分岐,二人却觉得相见恨晚。
晚餐十分丰盛,气氛也亲切而融洽。伯爵兴致勃勃,一直到深夜才告辞,也许他觉得这所房子里的一对新婚夫妇漂亮可爱。和他们在一起,无异于一种享受。
他走后,玛德莱娜马上对丈夫说:
“他很不错,是吗?而且和他接触越深就越觉得他好,这个朋友幽默、踏实、热情、忠诚。唉,要不是他……”
杜洛华没等她说完就接过话题:
“是啊,我也感觉他很有魅力,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很合得来。”
她马上接下去说:“我告诉你吧,今晚睡觉以前,咱们还要做个工作,本来该早告诉你这件事情,但刚才沃德雷克马上就要到了。没来得及。刚才我得知了一条来自摩洛哥的重要消息。是现在的众议员,原来的部长拉罗舍——马蒂厄提供给我的,我们应该写一篇文章,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这里有事实和数据。我们立刻动手。来,你拿灯。”
杜洛华拿着灯,两人走进工作间。
书橱里的摆设仍和以前一样。书橱上面,现在又放上了福雷斯蒂埃去世前在于昂湾买的那三个花瓶。桌子下面,摆放的暖脚炉正期待着杜洛华的双脚。他一坐下来,就拿起那支象牙制的,笔杆上还留着福雷斯蒂埃咬过痕迹的蘸水笔。
玛德莱娜斜靠着壁炉,燃上一支烟,先告诉杜洛华她所知的新闻,然后又说出自己的观点,拟订她打算写的那篇文章的大纲。
杜洛华一边仔细听着,一面匆匆记录。玛德莱娜说完后,他也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后又重归正题,把问题扩大并加以发挥。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大纲,而是在心里盘算,怎样掀起一场反对目前内阁的运动。这次攻击是个象征。妻子被他的过激攻击所吸引,放下手里的烟。随着丈夫的思路,她的脑海里也思绪翻滚,看得更深、更远。
她不时的喃喃自语:“……对……不错……很好……好极了……很有份量。”
“现在咱们动手写吧。”
可是文章的开头使杜洛华很为难,他只好冥思苦想。玛德莱娜看见他愁闷的样子就转身走来,俯身在他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不时提醒几句。
有时,她也征询丈夫的意见,问道: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杜洛华总是答道:“对,正是这样。”
她言词泼辣,用女人特有的刻毒言语中伤总理,从他的相貌,到他的服饰一并嘲弄,诙谐幽默、令人捧腹,且观察细致、扣人心弦。
杜洛华偶尔也是添上几句,扩大攻击的范围,显得更加有力。另外他写本地新闻时,还锻炼出一种狠毒的旁敲侧击的本领。玛德莱娜每说出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总觉得不太可靠,引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巧妙的让读者自己揣摩,使他们不得不相信,这种欲说还止的做法比直截了当显得更有力量。
文章写好后,乔治从头检查,并高声朗读一遍,两人都觉得满意,彼此会心而笑,感到又惊又喜,原来两人配合竟然如此默契。他俩惺惺相惜,含情脉脉的你看我,我看你。从灵魂到肉体闪过的忽然冲动,使他们狂然拥抱起来。
杜洛华拿起桌上的灯,目光灼人的说:“现在,咱们去睡吧。”
玛德莱娜回答说:“您既然拿着灯,那您就先走吧,我的主人。”
就这样,杜洛华和妻子一前一后往房间走去,她时而还用手指尖轻轻挠着杜洛华脖子上衣领和头发间裸露的地方,催他快走,而杜洛华最怕的就是别人这样挠他。
文章以乔治?杜洛华、德?康泰尔的名义发表以后,轰动了整个众议院,引起轩然大波。瓦尔特老头对作者表示欣喜,提升他为《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编辑部主任。布瓦斯协纳仍然负责本地新闻。
由此,该报开始了一场对内阁巧妙而又猛烈的攻击。抨击的文章接二连三,像连环炮一样,打得又准又狠,使人惊讶不已。这些文章写得很高明,举出大量事实,嬉笑怒骂中完成了使命。其他报纸也不断援引《法兰西生活报》的文章,整段整段的转载。高官们手忙脚乱,想把这个顽固而又素不相识的敌人封为省长,以此堵住他的嘴。
逐渐的杜洛华在政治集团中崭露头角。他以别人向他脱帽致意的姿志以及别人和他握手使用的力量,感到自己的地位确实提升了。但是他却对其妻子敏捷的思维,灵通的消息来源,渊博的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无论什么时候回家,总会发现客厅里有客人,不是一位参议员,就是一名众议员,要不就是一个法官,再不就是一位将军。他们的态度严肃而又亲切,对玛德莱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她是在哪里认识他们的呢?据她说是在社交场合。但杜洛华很想知道,她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人的信任并博得他们欢心的呢?
他心里嘀咕:“她真是一个能干的社交家。”
她回来时几乎都过了吃饭的时间。急匆匆的样子,满脸通红,身子还激烈发颤。常常是来不及摘下帽子,就说:“今天可有好吃的,你知道吗?司法部长刚任命了两个参加过混合委员会的法官。咱们给他一闷棍,好让他永远也忘不了。”
他们果然用文章恶毒攻击了部长,连续三天每天都是对部长的闷棍。每星期二都到封丹街吃晚饭的那位众议员拉罗舍?马蒂厄(沃德雷克伯爵是每星期一来)紧紧握住他们夫妇的手,欢天喜地的不住的说:“好家伙,攻击真有效果。这样,我们能不成功吗?”
其实,他对外交部长这个职务早已窥视很久很久了。
他是个清楚的政客,没有政治信仰,也没有什么本事,既没魄力,更谈不上真知灼见。他生性狡猾 ,原先是外省的律师,还算地方上的一个风流人物。他在各个极端的党派间搞折衷,伪装成拥护共和的耶稣会会员,是个可疑的自由自义者。这次利用普选的机会沉渣泛起,利用家粪堆里生的毒菌战成群结队的钻进了政界。
他用那种乡下人善于钻营的手段使他在集体中,在那些所有得过且过、一事无成的众议员中,俨然成为一个强者。他衣着很讲究,神情也大方得体,亲切而又和蔼,因而是左右逢源,在社交界和鱼龙混杂、粗野不文的达官显宦之中颇为吃香。
人们在普遍议论:“拉罗舍将来一定是个部长。”他也和大家一样,坚信自己是个未来的部长。
除此之外,他还是瓦尔特老头的主要股东,也是瓦尔特老头的同行,两人还曾合伙做过不少钱庄买卖。
杜洛华一如即往的支持他,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这样下去会有好处的。而且,杜洛华现在只不过在完成福雷斯蒂埃未竟的事业。拉罗舍曾给福雷斯蒂埃许诺,只要自己当上了部长,就授予他十字勋章。现在,这枚勋章将要带在玛德莱娜的新丈夫的胸前,而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
同仁们也知道情况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总开杜洛华的玩笑。杜洛华对此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
而且,大家竟然直呼他福雷斯蒂埃,似乎忘了他的真名。
他一到报馆,就常常听人叫唤:“喂,福雷斯蒂埃。”他只好装着没有听见,径直去信格里取自己的信件。可刚才的声音似乎更响了:“喂 ,福雷斯蒂埃。”其他人再也憋不住了,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
杜洛华向办公室走去,可刚才那个不识趣的家伙拦住他说:“哎,对不起,我刚才叫的是你,真糟糕,我总是分不清你和可怜的福雷斯蒂埃,因为你的文章和他的文章风格太像了,简直出自一人的手。”
杜洛华憋着一肚子火,他什么也不说,只好往死者身上出气。
无论是在文风上,还是构思上,大家觉得这位新任政治编辑的专栏文章都和他的前任没有多大差别。有的人提及这一点,并表示不可理解时,瓦尔特老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是啊,的确有的像福雷斯蒂埃的文章,只不过文章的内容更加充实,更显泼辣了。”又有一次,杜洛华偶然打开放毕尔波克木球的那个柜子,发现他前任使用过的木球拍上裹上了块黑纱,而自己当初在圣波坦手下工作时玩的那个木球拍上却缠上了条粉红色的缎带。所有木球按体积大小整齐的放好,上面有一块常见的木牌。木牌上写着:此处展出的木球乃福雷斯蒂埃及其同人之珍藏,全归政府正式认可的继承人福雷斯蒂埃——杜洛华所有。此球经久耐用,用途广泛,居家旅行,无不适宜。
杜洛华一面不动声色的将柜子关上,一面大声叫道:
“怎么到处都是愚蠢的笨蛋和嫉妒鬼。”
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真真切切的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管是普通的记者,还是伟大的诗人,只要其自尊心和虚荣心受到损伤,就会经常处于多疑和脆弱的状态,几乎无一例外。
他的耳朵一听到“福雷斯蒂埃”就剧痛,他怕听到这个名字,一听见脸就红。
他感到,这个名字实在是一种辛辣的嘲讽。甚至比嘲讽还厉害,简直就是辱骂。仿佛就在他耳边大喊:
“都是你老婆帮你的工作。她现在就像帮她的前夫那样在帮你的忙,没有她,你将一无是处。”
他完全相信,如果不是玛德莱娜,福雷斯蒂埃什么也不是,可是自己呢?他懒得去想这些了。
回到家后,他仍然在受着这些想法的折磨。现在,整幢房子,所有的家具和陈设,一切他所接触的东西都无不使他想起死去的那个人。虽然最初他一直不注意这种小事情,也不太考虑这种事,但同事们的玩笑在他心里划了一条抹不去的痕迹,这个伤疤随时被刺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