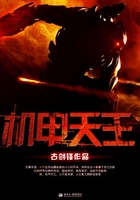第32章宣誓 (1)
莫里斯浑身颤栗,他向圣一雅克街伸出手去。
“火!”他说道,“火!”
“嗯,对,”洛兰说道,“是火,那又怎样?”
“啊!天主啊!假如她又转身回家了呢?”
“谁?”
“热纳维也芙。”
“热纳维也芙,她就是迪克斯梅夫人是么?”
“是的,是她。”
“她不会回来了,因为她不是为回来而出走的。”
“洛兰,我要找到她,我要报仇。”
“噢!噢!”洛兰说道:
“爱情是天神与鬼的主宰,
不再是香火摆上你的祭坛。”
“你帮助我找到她是么,洛兰?”
“当然啦!这又不难。”
“怎么不难?”
“假如你真的如我想象的那样,对迪克斯梅女公民的命运感兴趣的话,就肯定能找到;你应该认识她,既然你认识她,你就应该知道她最新的朋友都是哪些人;她没离开巴黎,因为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呆下去的;她一定是躲到某个知情女友家去了,明天早上你就会从某个萝丝(泛指女人)和某个马尔东(泛指男人)手上接过一张小纸条,上面大致写着这么几句话:
“倘若玛尔斯(战神。)愿意再见西代雷(不详。估计是玛尔斯的情人。)请他向夜神借她的蓝色披巾。
“然后他去某街某号上门去找门房,求见三星夫人(三星符号,用以代替不指名道姓的人。),这就样。”
“我们不会找到她了。”他喃喃道。
“请允许我对你说一件事,莫里斯,”洛兰说道。
“什么事?”
“即便我们找不到她,也不等于大难临头。”
“倘若我们不找到她,洛兰,我会死的。”莫里斯说道。
“活见鬼!”年轻人说道,“难道就是为了这码子爱情你就痛不欲生吗?”
“是的。”莫里斯答道。
洛兰沉思了一会儿。
“莫里斯,”他说道,“差不多十一点钟了,街上行人稀少,那儿有一张石凳,似乎专为两个朋友而设的。请给我一点面子,让我们私下谈谈吧,如同旧体制下通常说的那样,我向你保证,我再不用诗表达了。”
莫里斯向四周看看,坐到他的朋友身边。
“说吧,”莫里斯说道,把脑袋沉沉地垂到手掌心里。
“听着,亲爱的朋友,我不开玩笑,不绕弯子,不添油加醋,但我要对你说,我们完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你让我们完了。”
“此话怎讲?”莫里斯问道。
“好朋友呀,”洛兰接着说道,“公安委员会有条文规定,与敌人有关系者以叛国罪论处。呃!你知道这个条文吗?”
“当然,”莫里斯答道。
“你知道?”
“是的。”
“那好。依我看你就够叛国的罪名了。像芒利乌斯(芒利乌斯:罗马将军。被人从岩石上推下坠亡。)说的那样,你作何感想?”
“洛兰!”
“就是如此嘛,除非你把给红屋骑士提供食宿的人也看成是热爱祖国的;我看,红屋骑士不是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他也没被指控为九月事件(指1792年9月保皇党在黎暴动。)的制造者。”
“啊!洛兰!”莫里斯叹一口气说道。
“所以说嘛,”道德家继续说道,“你以前,乃至现在似乎仍然与国家的敌人过于亲近些了。哦,哦,别生气,亲爱的朋友;你如同昂斯拉德(传说中巨人,攻击奥林比斯山诸神,被女神压在西西里岛的巨石下。他发火时,西西里就发生地震。),只要一翻身,就地动山摇了。我再对你说一遍,别生气,干脆承认你已不再是一个忠实信徒了吧。”
洛兰说这些时口气尽可能婉转些,而且还运用了西塞罗(古罗马的诡辩家。)式的语言技巧。
莫里斯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以示抗议。
不过这个手势完全无效,洛兰继续说了下去:
“啊!倘若我们生活在温室里,温度适中,按照植物学上的要求,温度表总是指着十六度的话,我会对你说,亲爱的莫里斯,这就很合适,很舒适;你哪怕时不时地多少流露出一点儿贵族化倾向,也无大碍,给人感觉不错;可是今天我们是处在三十五度到四十度的热气下烘烤,隔热板灼热烫人,而我们只是温温的,相比之下,显得太冷了;而人一旦热度不够便要受到怀疑,这点你明白,莫里斯;一旦受到怀疑,你很聪明,亲爱的莫里斯,你自然会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好啊!让他们把我杀掉好啦,一了百了,”莫里斯大声说道,“我对生活也厌烦透了。”
“一刻钟以来,”洛兰说道,“真的,我一直在阻止你自暴自弃;再说,即便今天就去死,你得明白,也要作共和党人的鬼,而你很可能被看成是贵族的殉葬人呢。”
“哦!哦!”莫里斯嚷道,他因意识到自己的过失而痛苦不堪,变得极度焦灼不安,“哦!哦,你想得太多了,好友。”
“我还要说下去哩,我要告诉你,倘若你站在贵族这一边……”
“你要揭发我么?”
“去你的,不会,我倒先会把你关进一个地窖,然后让人击鼓四处找你,就如找一个失落的东西那样;然后,我宣称贵族知道你对他们的威胁,把你捕获,对你施以酷刑,让你挨饿;最后你如同埃里?德?波蒙大法官、拉杜特先生(拉杜特(1725—1805):法国冒险家。一生共坐狱35年,多次企图越狱,大革命时斯获释。)和其他人那样,当你重见天日后,你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中央菜市场的婆娘们和维克多区分部的那帮捡破烂的人戴上荣誉桂冠。于是你就赶快回头再当你的阿里斯迪特(阿里斯迪特(公元前550—公元前467):希腊将军,政治家。),从此,你就一马平川了。”
“洛兰呀洛兰,我觉得你言之有理,可我已不能自拔了。我在坡上一直往下滑。命运使然,你会憎恨我么?”
“我不怨你,但我要与你争辩。回想一下皮拉特每天和奥莱斯特(皮拉特是奥莱斯特的日耳曼血统兄弟的朋友。这两位英雄都在宫廷长大,前者帮助后者为父复仇,并娶其妹为妻。他俩的友谊成为美谈,在不少文学作品里都有表现。)吵架的场面吧,他们之间的关系雄辩地证明了友谊只是一个矛盾结合体,那两个模范朋友从早到晚争论不休。”
“你放弃我吧,洛兰,这样对你更好些。”
“决不!”
“那么让我去爱,去发疯,甚至成为罪犯吧,因为我如再见到她,我会把她杀了的。”
“要不你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啊!莫里斯居然爱上了个女贵族,我怎么也没料到。你现在就像可怜的奥莱林爱上了夏尔尼侯爵夫人(大仲马的另一部分《夏尔尼伯爵夫人》中的两个主人公。书名上是“伯爵”,不是“侯爵”。)了。”
“别说了,洛兰,我求求你了。”
“莫里斯,我会治愈你的,要不就让魔鬼把我掳去。我不愿意你‘中了神圣的断头机彩’,就像朗巴尔街卖杂货的人那样说的。要留神呀,莫里斯,你快让我绝望了。莫里斯,你会让我饮血。莫里斯,我恨不得放一把火把圣路易岛(巴黎塞纳河里的一个岛。)烧掉;一支火炬,一个火把!
“啊,不,我的努力是白费功夫,
又向谁去要一支火炬,一个火把?
你本人就是一束美丽的火焰,莫里斯,
照亮你的心灵、周围及整个巴黎。”
莫里斯也忍俊不禁。
“我们不是讲好不用诗代替说话的么?”他说道。
“可这是因为你发疯才让我走投无路的呀,”洛兰说道,“这也是因为……听着,喝酒吧,莫里斯;让我们变成酒鬼,胡闹一番,或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万万不要像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箭那样去恋爱吧,让我们仅仅珍惜自由自在的生活吧。”
“或是理智。”
“啊!一点也不错,女神说了你不少好话哩,并且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凡夫俗子。”
“你不嫉妒吗?”
“莫里斯,为了拯救一个朋友,我可以作出任何牺牲。”
“多谢了,可怜的洛兰,我非常看后果你的忠诚;不过安慰我的最好的方法便是让我饱爱痛苦。再见吧,洛兰;你会会阿尔泰米斯吧。”
“你呢,你上哪儿?”
“我回家。”
说完,莫里斯向桥迈了几步。
“你现在住圣—雅克老街那头吗?
“不是,但我愿意上那边去。”
“为了再目睹一次你那没良心的女人住过的地方吗?”
“为了看看她是否回到了我等她的那个地方。她是知道的。呵,热纳维也芙!热纳维也芙!我决不认为你会做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情来!”
“莫里斯,曾有一个暴君对女性有着深刻的见解,因为他就是爱得过深而死的。他说道:
‘女人常常多变,
疯子才会相信。’”
莫里斯叹了一口气,这两个朋友转回到圣—雅克老街的那条路上去了。
两个朋友走近那里时,他们听见一片喧嚷声,并且看见灯火通明,还传来了爱国歌声;如在阳光明媚的白昼,在战斗的炽热气氛下,唱这类歌曲大有赞美英雄的气势,可是眼下是夜晚,在火光映照下,倒像食人者喝醉后有气无力地打哼哼了。
“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莫里斯说道,他忘了天主已经被废除了。
他一直往前走,额上沁出汗珠。
洛兰看他步履匆匆,牙齿间又轻轻吐出两行诗句:
“爱情,爱情,一旦抓住我们,
便可对谨慎小心道声再见。”
似乎所有巴黎人都汇聚在我们刚才叙述的那些事情的舞台上了。莫里斯不得不穿越投掷兵的防线、区民兵的队伍和密集的人群,这些人永远怒气冲冲,时刻戒备着,哪里出事便吼叫着往哪里冲,这是当时的风尚。
莫里斯焦灼不安,越走越急。洛兰苦苦地紧跟在后,他太喜欢莫里斯了,在这关键时刻,不能让他单身一人行事。
一切接近尾声;士兵把燃烧的火把扔进敞棚,烈火又从那里烧到用木板拼装、留出很大间隙,以便让空气流通的一间间工场;货物都烧起来,房子本身也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