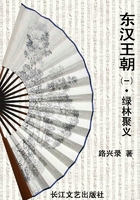第30章康乃馨和地道
第一次打击是沉重的,莫里斯得使出全部解数才能向洛兰隐藏他身心俱焚的表象;然而,一旦到了花园里,只身一人,在宁静的夜晚里,他的心就要平静多了,他的头脑也不再紊乱如麻,而是变得有条理,能受理智控制了。
什么!他怀着最大的喜悦常常登门的这幢房子,他看之为人间天堂的这幢房子,难道是一个血腥阴谋的巢穴!对他友好而热情的欢迎,只是虚伪么!热纳维也芙的全部爱情,只是恐惧的表现!
读者熟悉这个花园的布局,因为他们已不止一次跟随我们这帮年轻人在里面转悠了。莫里斯从一个树丛钻进另一个树丛,一直走到一间类似花房的阴影里,避开了月光的照射,记得那一天他进入这幢房子时就在关这间屋子里的。
这个花房与热纳维也芙住的楼阁遥遥相对。
可是这天晚上,少妇的房间非但没有孤灯朗照,清明澄净,而是灯火在窗户之间摇曳不定。莫里斯隔着半卷起的窗帘望去,看见了热纳维也芙,她正匆匆忙忙地把东西塞进行囊里,并且惊讶地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把闪闪发亮的手枪。
他爬到一根大柱上,以便更清楚地看清房里的一切。一束大火从壁炉里窜起,引起他的注意;那里热纳维也芙在焚烧文件。
这时,一道门打开了,一个年轻人走进热纳维也芙房间。
莫里斯首先想到是迪克斯梅。
少妇向他奔去,握住他的双手,两个人四目相注片刻,仿佛都很激动。激动缘何而来?莫里斯猜不透,他也听不见他俩的说话声。
突然,莫里斯目测起此人身高来了。
“不是迪克斯梅。”他喃喃自语道。
果然,刚刚走进去的那个人又矮又瘦,而迪克斯梅却又高又壮。
嫉妒是一贴兴奋剂;莫里斯用不了一分钟就估量出来者的身高,判断出她丈夫的身高。
“不是迪克斯梅。”他轻声说道,仿佛他不得不向自己再说一遍,以确信热纳维也芙背信弃义了。
他移近窗户,可是他愈靠近,愈是看不清,因为他的头上在冒火。
他的脚触到一架梯子;窗高七八尺,他扶起梯子,把它支在墙上。
他登上梯子,把眼睛贴在窗帘缝中。
热纳维也芙闺房里的陌生人约摸在二十七八岁上下,蓝眼睛,温文尔雅;他握住少妇的双手,一边与她说什么,一边擦拭着热纳维也芙迷人的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
莫里斯发也了轻微响声,年轻人轻头转向窗子那边。
莫里斯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认出此人便是在夏特莱广场上那神秘的救命恩人。
这时,热纳维也芙把双手从陌生人手里抽出来,向壁炉迈出几步,看看文件是否都已烧毁。
莫里斯再也控制不住了,困拢着人的所有情感:爱情、复仇、嫉妒都似烈火般地噬咬着他的心。他刻不容缓,猛地推开关得不严合的百页窗,跳进屋里。
与此同时,两支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
热纳维也芙听见声音转过身子,看见莫里斯不声不响地站着。
“先生,”年轻的共和党人冷冷地对那曾两次用枪口决定他生命的人说道,“先生,您就是红屋骑士吗?”
“是又怎样?”骑士问答。
“啊!倘若是,您就是一个勇敢而沉着的人,我要对您说几句话。”
“说吧。”骑士说道,枪口仍对着他。
“您可以杀死我,可您不要在我叫喊之前把我杀掉,更确切地说,我没叫喊之前我不该死。倘若我喊出了声,包围这幢房子的上千个人在十分钟之内便会把你们化为齑粉。因此,请放下手枪,听我对夫人说几句话。”
“对热纳维也芙?”骑士问道。
“对我?”少妇喃喃道。
“是的,对您。”
热纳维也芙的脸色像一具雕塑那样白,她抓住莫里斯的胳膊,年轻人把她推开。
“您记得您对我立的那句肯定的话么,夫人,”莫里斯带着极为轻蔑的口吻说道,“现在我明白您说的话没错。果然,您不爱莫朗先生。”
“莫里斯,请听我说!”热纳维也芙大声说道。
“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夫人,”莫里斯说道,“您欺骗了我;您一下子把系在我们两颗心之间的纽带都切断了。您说您不爱莫朗先生,可您没有对我说您还爱着另一个人。”
“先生,”骑士说道,“您说莫朗什么了,或者说您说哪一个莫朗?”
“说的是化学家莫朗。”
“化学家莫朗就在您面前。化学家莫朗和红屋骑士本是一人。”
他把手伸向邻近一张桌子,迅速戴上黑色发套,年轻的共和党人看见他变了一个人。
“啊,是的,”莫里斯更加轻蔑地说道,“是的,我明白了,您爱的不是莫朗,既然莫朗根本不存在;不过偷梁换柱的手法纵然加倍狡猾,也还可鄙的。”
骑士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
“先生,”莫里斯继续说道,“请让我与夫人谈一小会儿;甚至如果您愿意,请您帮助促成这次会谈,时间不会长的,我向您保证。”
热纳维也芙做了一个手势让红屋骑士耐心些。
“就这样,”莫里斯继续说道,“就这样,热纳维也芙,您使我成了我朋友的笑柄!我的战友憎恶的对象!我瞎了眼睛,您在我无知的情况下,让我成了你们所有阴谋的帮凶!您利用我就如利用一件工具似的!请听着:这是无耻的行为!您将要为此受到惩罚,夫人,因为这位先生将要当着您的面杀死我了!但不出五分钟,他也会在这里躺卧在您的脚下;反之,即便他还活着,那也只能把脑袋送到断头机上去。”
“他要死?”热纳维也芙说道,“他把脑袋送进断头机?可莫里斯,他是我的保护人,我全家的保护人;我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倘若他死了,我也会死去;倘若您是对我的爱情所在;那么他就是我的宗教寄托,您知道么?”
“啊!”莫里斯说道,“您大概还要对我说您爱我吧。说真的,女人真是太懦弱,太胆小了。”
接着,他又转过身子。
“来吧,先生,”他对年轻的保王分子说道,“不是把我杀死就是你自己死。”
“为什么?”
“因为倘若您不杀死我,我就要逮捕您。”
莫里斯伸出手抓住他的衣领。
“我不与您争夺我这条命,”红屋骑士说道,“拿去吧。”
说完,他把手枪一齐扔到扶手椅上。
“为什么您不向我争取一条活路呢?”
“因为我的一生里不愿让自己后悔杀死过一个多情男子,再说,更为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热纳维也芙爱您。”
“啊!”少妇合起双手大声说道,“啊!您总是那么善良、伟大、忠贞、慷慨大度,阿尔芒!”
莫里斯看着他俩,惊得几乎发呆了。
“听着,”骑士说道,“我回房去了,我以荣誉担保,我决不是想溜掉,而是去收藏一帧肖像。”
莫里斯迅速向热纳维也芙的肖像扫了一眼,它仍在原处。
也许红屋骑士猜出莫里斯在想什么,也许他想把从容大度推向极至。
“谈谈吧。”他说道,“您是共和党人,可我也知道您是一个纯洁忠诚的人。我向您全盘托出吧:瞧!”
说完,他从胸间抽出一张小小画像,是王后。
莫里斯低下头,把手放在额上。
“我等候您的吩咐,先生,”红屋骑士说道,“倘若您想逮捕我,您就敲这扇门,说明我自首的时候到了。既然拯救王后无望,我的生命无所寄托,我也弃如敝履了。”
骑士走了出去,莫里斯没有任何挽留他的意思。
他刚刚走出房门,热纳维也芙便匍匐在年轻人的脚下。
“请原谅,”她说道,“莫里斯,请原谅我对您做的一切坏事;请原谅我的欺骗行为,看在我的痛苦的眼泪的份上原谅我吧,因为,我可向您起誓,我哭得很伤心,我受够了痛苦。啊,我的丈夫今晨出门了,我不知他上哪儿,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眼下我只有一个朋友了,不仅是一个朋友,而且一个兄弟,可您却要让人把他杀死。开开恩吧,莫里斯,开开恩!”
莫里斯挽起了少妇。
“您想要什么,”他说道,“这是命运;时下,所有人都拿生命来赌博;红屋骑士也像其他人一样在赌,可是他输了;现在,他得偿付代价。”
“如果我听明白您说的话,那就是他得去死。”
“是的。”
“他得去死,是您在对我说这样的话吗?”
“不是我,热纳维也芙,是命运。”
“在这件事情上命运没有最终决定,因为您还能救出他。”
“以我言而无信,从而名誉丧尽为代价吧。我心里明白,热纳维也芙。”
“请闭上眼睛吧,莫里斯,这就是我的全部请求,一个女人所能表示感激的,我答应您,我都能做到。”
“我闭上眼睛也没有用,夫人;有一个口令,没有口令,任何人也出不去,因为整幢房子已被包围,我再说一遍。”
“您知道口令么?”
“我当然知道。”
“莫里斯!”
“什么事?”
“我的朋友,我亲受的莫里斯,请把口令告诉我吧,我需要知道。”
“热纳维也芙,”莫里斯大声说道,“热纳维也芙!您究竟是谁可以来这样对我说:‘莫里斯,看在我爱你的份上,言而无信,名誉扫地吧;背叛你的事业,否定你的理论吧。’您这样劝导我,那么您又为我献出什么以换取这一切呢?”
“啊!莫里斯,救出他,先救出他,然后,您再索取我的生命。”
“热纳维也芙,”莫里斯忧郁地说道,“请听着:我已经有一只脚踏在无耻的行径上了;欲要整个儿踏上此路,我至少要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热纳维也芙,请对我发誓,您不爱红屋骑士……”
“我像一个妹妹,一个朋友那样爱红屋骑士,而不是其他方式,我可以向您起誓!”
“热纳维也芙,您爱我么?”
“莫里斯,我爱您,与上天听见我说的话一样真实。”
“倘若我满足您的要求,您能放弃亲属、朋友和祖国,与叛徒一起私奔么?”
“莫里斯!莫里斯!”
“她犹豫了……啊!她犹豫了!”
说着,莫里斯带着极度鄙夷的神色往后退缩。
热纳维也芙原半靠在他身上,突然感到失去支撑,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莫里斯,”她身体向后仰去,搓着双手说道,“莫里斯,我满足你的一切愿望,我发誓;命令吧,我服从。”
“你将属于我的,热纳维也芙?”
“只要你要求。”
“向基督起誓吧!”
热纳维也芙伸长胳膊,说道:
“我的天主,您已经赦免过不贞的女人,我希望您将宽恕我。”
说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她的双颊滚下,落地披散在她胸前的长长的秀发上。
“啊!别这样,别这样起誓,”莫里斯说道,“否则我不接受您的誓言。”
“我的天主啊!”她接着说道,“我发誓把余生献给莫里斯,与他共生死,如果需要,为他而死,只要他救出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兄弟——红屋骑士就行。”
“好吧,他将得救。”莫里斯说道。
他走向另一间房间。
“先生,”他说道,“穿上制革匠莫朗的工作服吧。我改变主意了,你自由了。”
“而您,夫人,”他对热纳维也芙说道,“口令是:康乃馨和地道。”
他说出这句口令时等于承认自己叛变了,他仿佛不想再在这间出卖自己的房间里久留似的,便打开窗户,从屋内跳到花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