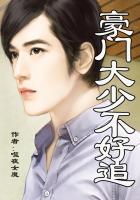第十章 新生3 (1)
离别使得爱的魔力更强了。我们心里惦记的,只是爱人身上那最为可贵的部分。远行的友人传来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些庄严的回声,那回声在寂静中颤动。
克利斯朵夫跟葛拉齐亚的通信中,语气变得有些深沉、有些含蓄,就像是一对曾经备受爱情折磨的夫妇,由于度过了难关,手牵着手走着,对于自己的前途和脚力,他们已经相当自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强,足够去支持对方,去指导对方;也都有一定的弱,渴望对方给予支持,给予领导。
克利斯朵夫回到了巴黎。他原本不喜欢再去的,可自己心里的这些愿望又有什么用啊!他明白在那里依然可以找得到葛拉齐亚的影子。情势继续向前发展,就像和他内心的愿望联在一起,将意志推翻,这让他知道在巴黎还有一个使命。高兰德的消息很灵通,她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的小朋友耶南正在胡闹呢,就连一向溺爱儿子的雅葛丽纳也想放手不管了。在精神上,她也曾经经历过一个苦闷的阶段,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更别提去管儿子了。
自从她的婚姻和奥里维的生活被那次可鄙的情变给毁掉以后,雅葛丽纳就从不出门,一直过着安静、平稳的生活。虚伪的巴黎社会把她排挤出来,就像隔离瘟疫一样,现在又过来接近她,被她拒绝了。她不觉得在这些人面前应该惭愧,也觉得没必要向他们负责:因为他们做得还不如她。她做事坦荡,有一半她所认识的女子都是偷偷摸摸的,是戴着假面具做的。她只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痛苦的,那就是把她最好的朋友害了,那是她惟一的爱人。她无法原谅自己,在这样一个冷漠贫瘠的世界上失去了像他那样真实深沉的爱。
当所有的遗憾、痛苦渐渐地淡下来时,剩下来的就只有一种郁闷,还有的便是母爱。她把没处发泄的全部的爱全部倾泻到母爱中去,对于儿子,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更无法抵抗他的任性。她逼着自己去相信这是向奥里维赎罪,目的是为了更了解自己的懦弱。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儿子非常温柔,但很快就厌倦了,继而不管不问;她时而用着苛刻的、过分罗嗦的爱和乔治形影不离;时而又觉得腻烦了,任由他随便去做。她知道自己并不善于教导儿子,所以心中甚是懊恼,但是她并不改变方法。等到她忽然觉得应该要把如何做人按着奥里维的精神改进一下的时候,结果更是让人失望;奥里维主张悲观主义,这对于她母子俩来说都不合适。她只是想要用感情来控制儿子。
这无疑是正确的,无论两个人怎么相像,除了感情以外,毕竟是没什么可联系的。乔治?耶南深深地被母亲吸引着,喜欢她的声音,她的姿态,她的动作,她的柔媚,她的爱。但在精神上,他认为她是那么陌生。在母亲这方面,以至于当青春期的风已将儿子都吹远了,她才感觉到这一切。于是她惊讶,她愤怒,她觉得是因为别的女性的影响才使他疏远,于是便很笨拙地试图摆脱那些影响,然而这样却导致了使他更加疏远的后果。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向都是各有各的想法,对于双方的分歧点视而不见,原因是两个人好恶相同。但若到了孩子从暖昧的,带有女性气息的阶段向成年人阶段转变的时候,那些共有的情感就不存在了。雅葛丽纳不无心酸地对儿子说:“我不明白你到底像谁,你既不像你父亲,也不像我。”
这样她可以让他更加体会到两个人的差异,他暗暗地为之自豪,同时也有些不安。
当他还没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答案的人的时候,他就等得不耐烦了。父亲可以用毕生精力来追求真理以获得满足,而他却不能这样。他需要消耗烦躁的、年轻的精力,无论有没有理由,他都要做出决定,去行动,去消耗他的精力。首先是旅行和艺术,特别是那些他拼命吸取的音乐,已经成了他间断的如痴如醉的消遣。他人长得倒蛮俊的,而且早熟,并接受了许多诱惑,早就感觉到了外表看似非常诱人的爱情天地,于是就满怀诗情画意的、贪婪的、激动的心情闯进去。可是这个少年非常钟情,天真与贪婪的程度简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很快就开始厌倦女人了,又想要行动去了。于是着迷于体育了:什么都想要试试,什么都想要玩玩。只要是斗剑和拳击的比赛,他没有不参加的,而且还是赛跑和跳高的全国冠军,担任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他和一些跟他类似的青年疯子,有钱而捣乱的家伙,在汽车比赛中赛勇气;那荒唐、兴奋的样子就等于在比谁死得快。然后他又去弄些新玩艺儿,把一切丢到一旁。他被群众的飞机狂给传染了,兰姆斯举行了一次航空大会,在这期间,他跟着三十万人一块儿呐喊着,高兴得哭了,感觉到在这个欢庆热闹的场合中,自己和全人类结合了。在他们的头上,人和鸟一样地飞过,将他们的心也带飞了。自从大革命的黎明时期以来,这是首次。这些老百姓抬头望着天空,看到的是被打开的另一个世界……年轻的耶南说想要加入到征服天空的队伍,这让母亲十分吃惊。她苦苦地哀求他,甚至去命令他,让他放弃这个恐怖的野心;可他却不管不顾,独断专行。雅葛丽纳觉得克利斯朵夫怎么也会和她意见一致,但没想到他只是告诉孩子当心一点儿;其它的话,他确信乔治肯定不会听。如果处在乔治位置上的那人是他,他也一样不会听,他想即便是能够,也没办法去阻碍那些年轻的力量,不让他们有健康的、正常的活动:如果是照这样办了,他们很可能就会回来摧毁自己。
雅葛丽纳无法这样听任自己的儿子逃出自己的控制。她确实是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爱情,但一点儿用也没有,她仍然减少不了对爱情的幻想;她一切的情感,一切的行动,都沾染有爱的色彩。很多做了母亲的人,她们都把那些无法在夫妇之间或者情人之间发泄的热情转移到儿子的身上;一旦她们觉察出儿子对自己竟然毫不在意,也不再需要自己时,那种精神上的痛苦跟情人的欺骗以及爱情的毁灭没什么两样。——这可是对雅葛丽纳的又一个新的刺激,但乔治一点儿也不这么觉得。年青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周围发生着什么样的感情悲剧的:他们来不及看到,他们那自私的本能会让他们一直往前冲,连头也不会回。
雅葛丽纳只能独自将这个新的痛苦埋在心里。直到时间长了,心中的痛苦也渐渐地变淡了,她才获得了解脱。同时,她的爱也随之变淡了。当然,她会一直爱儿子的;但那是一种毫无幻想、遥远的爱,因为明明知道这情爱没有用处,所以她也不在意自己的感情和儿子了。她就这样郁郁寡欢地熬过了一年,他却没有注意。之后,这颗屡遭不幸的心不能放弃爱独自活下去,只能创造出一个爱的对象。因此,忽然间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热情;而这种情形是某些女性经常会发生的,尤其是一般很高尚且最不易接近的心灵,到了成熟的时期还没有得到人生的收获的那些女性。她结识了一个女子,只不过惊鸿一瞥就被对方那神秘的吸引力抓住了。
那是一个与她的年龄相仿,专门做救济事业的女修士。人长得虽有点儿臃肿,但很高大、强壮;有着一头褐色的长发,脸上还有着很好看、很鲜明的线条;眼睛非常有神,嘴巴阔大而且线条细腻,并总是微笑着,其下巴长得也很有代表性,一看就知此人个性专制。她非常聪明,丝毫没有伤感的意思,就像乡下的女人那样狡猾,精通于实际的事务,再加上南方人的爱幻想的传统,目光远大,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把尺度看得很准。她习惯支配人,而且支配得摸不着头绪。雅葛丽纳很快就被她给吸引住了,对救济事业十分感兴趣,并且非常热心,至少她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女修士安日尔明白这种热情是为了谁,她原本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挑起这一类的情绪,虽然说表面上假装对对方的热情毫无察觉,但其实她却非常冷静地把它拿走,去献给她的上帝和她的救济事业。金钱、意志、感情,这些统统都被雅葛丽纳奉献出来,她因为需要爱而变得有信仰了,比以前更加慈悲了。
她着了魔,大家很快就感觉到了,但是她自己并没发觉。乔治的监护人已经开始担忧了。连从来都不在乎金钱,而且很慷慨、糊涂的乔治都注意到母亲被人利用了,甚是恼火。他希望能和她恢复往日的亲密,但已经晚了;他们两个人已经被一重幕隔开了。他认为这样的情形是妖术在作怪,他对那个他管她叫阴谋家的女人,甚至是对于母亲,公开地表示极为恼怒。他觉得母亲的爱就像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旁人侵占,而他并没想到这侵占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放弃。此时的他不仅不知怎么样才能把它抢过来,反而应付得很笨拙,令人难堪。
因为母子二人均是脾气急躁、个性激烈的人,总免不了说些难听的话,这样也就使原有的裂痕更深了,而安日尔摆布雅葛丽纳的力量却反而因此更加巩固了。乔治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只顾着向外跑,只想着去玩儿。他因为赌博,输掉了很多钱;他还一边乱搞,一边到处招摇,不仅为了好玩,也是为了给母亲的糊涂一个报复。他跟史丹芬?台莱斯拉特家里的人一直有来往:高兰德对这个漂亮英俊的青年人早就有所企图,想要在他的身上试试她那风韵犹存的魅力。她觉得乔治的那一些荒谬的事儿挺有意思的。她虽然表面上有些轻浮,但人却还比较通情达理,也确实很善良,因为这两点,她感觉到了这样一个痴狂的青年正处于危险边缘。她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是救不了他的,所以就通知了克利斯朵夫。他一收到信,就马上赶来了。
对年轻的耶南还能施加影响的人就是克利斯朵夫。虽然影响并不深,也不是连续的,但因为一种很奇怪的原因,所以这影响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过去的那一代的,就是乔治和他的同伙们正强烈反抗的那一代。克利斯朵夫也是那个充满暴风骤雨的时代的最高代表之一,可对于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青年人都存有猜疑和敌意。只要是新的《福音书》,小型的先知和老魔术师嘴里的符咒,向老实憨厚的年轻人传递的,包括罗马、法国,全世界都能给予拯救的如神般灵验的秘方,这些均跟克利斯朵夫没有关联。他忠诚地信仰自由,任何宗教都束缚不了他,任何党派也影响不了他,任何国家也限制不了他,——然而这样的信仰已经过时了,或者也许还没有重新流行。最后,虽然他已经彻底地摆脱了国家的问题了,但在巴黎仍是感觉自己个外人,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会将外国人看成是野蛮未开化的人。
耶南是年轻的,他轻浮、快乐,痛恨扫兴的人,他总是寻欢找乐,喜欢做过激的游戏。由于身强体壮,思想又懒惰,所以他倾向于法兰西行动派的暴力主义,同时他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一个保王党,一个帝国主义者,(他连自己都弄不明白)。但他衷心佩服的却只有一个人:克利斯朵夫。根据自己那早熟的经验,还有那来自于母亲的敏感,他早就断定了克利斯朵夫是个伟大的人,而他所在的社会简直不值一提,虽然仍旧有些舍不得这个社会,也不会因为它的低俗而降低自己的兴趣。他用运动和行动来让自己麻醉,这种做法是徒劳的,终究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遗传。他经常会有一阵莫名其妙的不安突然出现,感觉到自己应该给自己的所作所为定一个目标:这是从奥里维那里遗传的。他还从奥里维身上得到一种本能,那就是使他能够去靠近奥里维曾经爱过的人的那种神秘的本能。
他去看望克利斯朵夫。他生来就话多,以至于有点儿絮叨,还特别愿意讲些自己的故事,也不管克利斯朵夫是否有时间听。克利斯朵夫当然要听,而且一点儿也不耐烦。但如果此时正赶上乔治突然赶来,把他的工作打断了,他便有些走神了。他可以把胸中的作品再反复推敲一番,让自己稍微溜溜神儿,再回到乔治身边。他认为这样的情形很有意思,就好像一个人轻手轻脚回到屋里,没有人听见。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次,被乔治发现了,于是乔治气愤地说:“你为什么不听我说?”
这样克利斯朵夫便有些难为情,立刻变得非常温柔,而且又格外全神贯注地听下去,以此来表示歉意。乔治所讲的故事总有些滑稽,每当克利斯朵夫听到一些荒唐的事儿时,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乔治什么都讲,那种坦白的程度令人对他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