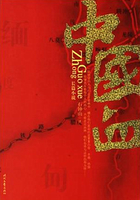第七章 户内2 (9)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为什么两个国家不能像他们一样相亲相爱。这股新觉醒的怒恨,令两个人都莫名其妙,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以一个德国人的身分,他无法去想象去恨一个曾败给自己的对手。他一方面对同胞们的骄傲和狂妄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他正如绝大部分德国人一样,不明白为何法国不站在德国这一边,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相当多的理由站在统一的战线上,同时又有那么多重大的事情需要两国共同去做。所以,他们的仇视令他大为恼火,他亦认为法国在这场误会中要负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战败对法国确实沉痛,但这被他归为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想到自尊心。他从没仔细考虑过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自小学起,他就把吞并阿尔萨斯一洛林的行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认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前被异族统治后,夺回德国的土地罢了。所以当他发现朋友把这看成是一种罪行时,他就糊涂了——他从来未和他说过这件事,满以为奥里维同意自己,不料他印象中胸襟宽大的奥里维,不胜悲苦地对他说,一个民族可以放弃对这种事可以的报复行为,但他却依然认为这罪行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在这一问题是极其地不能相互了解,奥里维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阿尔萨斯—洛林是法国的领工,同样地,克利斯朵夫亦可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但无论哪一种,都有许多理由。——克利斯朵夫之所以会重视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重视个人感情,其实关键的问题并非阿尔萨斯—洛林人的国籍,关键的是他们愿归属哪个国家,谁都可以说:这个民族是属我的,因为我们是兄弟。但如果这位兄弟不认他的话又如何呢?纵使这种否认是很不应该的,但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或利诱对方跟他走,甚至在公廉的德国当局在推行德政时,阿尔萨斯人始终不肯作为德国人,而纵使他们迫于压力只能让步时,心中也永怀有背井离乡、逃亡异地的痛苦和那种教人没法忍受沉痛的“枷锁”。
克利斯朵夫坦率地承认自己未观测这方面的问题,心里马上就难过起来了,正如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常常非常坦率,但他们却很有自尊心。固然,历史上所有民族都有过这类罪行,但克利斯朵夫却绝对不会去拿那些国家来作为原谅这种行为的借口:他太高傲了,他不去找别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进步,会带来更可怕的罪恶。但他也知道,如果法国胜利了,也不见得会比德国更节制,一定也会在这个罪恶上画上浓重的一笔,这样,悲痛会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的文明精华受到损伤。
克利斯朵夫难受,可奥里维心里更加难受。可悲的不只是两国厮杀,更可悲的是国内的两部分人也正在厮杀。和平运动和反军国主义运动一直在连续不断地继续下去,政府,只要他们不损害他的本质利益,他就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民族其实最危险的并不是在公开一种最危险的主义,相反,是听之任之让危险主义潜伏在民族血脉中,等政府开始作战的时候来破坏它,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自由、友好、公平、和平的欧罗巴,由它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有人性的德国;一方面,它也要迎合自私自利的小人,因为这帮人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可以干——这些反战思想感染了奥里维及许多人。
有一两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这种谈话不禁吓了一大跳,那位好心的莫克一读起反战思想便是语气相当柔和,眼睛都弯了,满脑子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他甚至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煽动士兵造反,教他们向长官开枪。而工程师他们则说,若发生战争,他们要先解决了国内的敌人,再上前线。而安特莱却支持莫克。有一天,两兄弟还为这事争得相当激烈,甚至拿起枪相互威吓,虽然现在这些带杀气的话是开玩笑时说的,可真地发生他定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个怪异的国家,仿佛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着为思想而杀戳。真是疯子,头脑中有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个人的思想,不到极端不到终点,永远不会后退。而且,他们所消灭的是有思想差异的,——爱国主义向人道主义攻击,人道主义向爱国主义开火,而这时敌人来了,所有一切民族、国家、主义全灭亡了。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向哀斯白闭说,“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呢?”
“反正总有人做先锋,那就让我们来好了,反正我们素来如此,就找我们来发信号吧!”
“要是得不到响应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商量好,有没有制定计划?”
“用不着制定,什么都比不过我们的力量!”
“这可是在说战术。你想想,如果你们要消灭战争,就要利用战争,在两国交战之前,首先要订的是战略计划,把你们在德国和法国同时行动的时间定下来,倘若你们心存侥幸,结果会怎么样,你我很清楚,一方是没有预谋地碰运气,一方则是有组织有气魄的强大力量——你们会被镇压的!”
可哀斯白闭根本听不进去,只是说要是把一颗砂子放在要害的地方,比如放在机器里的齿轮里就会破坏机器。
但,世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从容不迫谈理论是一回事,而行动起来就不同了,尤其是需要果断的时候。那正如一个人以为是自由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自己思想的主宰,当狂风巨浪在心里卷过,觉得自己好像不由自主地被别的东西拖着的时候,你的心中就会有一股模糊的力量让你违背本意,你那时就会发现,那思想中存在一股陌生的主宰,驱策着人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是头脑清醒信仰坚定的人也会束手无策,而走到一条和自己意志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去,反教自己大吃一惊。现在,法国遇到了这种情形,在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群中,有些人感觉到自己的爱国和热情突然上涨起来,而这些热情和责任并不相悖。克利斯朵夫看见许多人,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都是如此,他开始还未把此事看得很重要,还用德国人固有的冒失态度和安特莱说,该实行理论了——要是他不喜欢德国把法国灭亡的话,谁知,安特莱怒道:
“等着瞧吧……你们这批混蛋不过有个‘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的选举人,你们没勇气推翻你们的皇帝,砸碎你们的枷锁——我们会替你们摆脱的,我们一定会!吞没我们,没门儿,我们会打败你们!……”
越要等下去,人们的心里便愈加烦躁,仿佛骚乱正在不停地凝聚浑身的力量。安特莱也很痛苦,明知道自己的信仰是对的,然而骚乱的意志却使自己无法保护,他同时感觉到骚乱的精神气息——那种集体思想的强烈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产生重大影响——大家逐渐远离他,彼此之间不再说话了,再没有欢乐可言了!
但行动的怒潮没有使迟疑不决的心绪拖延下去,而把他们推上了战争的最前线——加入不同的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那是最后一夜——两国所有的军力都到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时,克利斯朵夫发现大家的选择已经完全定了下来。一切敌对的党派都加入了遭它们蔑视的政府一边去了,无论是颓废的艺术大师和美学家,还是犹太人,他们都要为他们的土地而战。而爱国主义则像传染病一样,传遍法国的大街小巷,哈密顿一听到国旗两字便会落泪,而所有的人都是真诚的热烈的。
安特莱?哀斯白闭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和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更加疯狂地作了政府的工具——在形势的逼迫下,提出了他最痛恨的主张,他们心怀阴郁的怒意打定了主意——也正是这种心绪使他们更疯狂。而电机工人奥贝,在后天的人道主义和排外思想的交替中,经过痛苦的挣扎,打定了主意:认为法国代表全人类。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和克利斯朵夫打招呼——所有的朋友都对克利斯朵夫不理不睬——连和气的亚诺夫妇亦如此。虽然,他们日夜沉浸在音乐之中,想忘掉那件大众的事,但他们做不到,并且会时时刻刻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见到克利斯朵夫时,都会和他热烈握手,可是都是急匆匆地带着躲闪的神色,倘使在同一天里,克利斯朵夫又碰到夫妇两人,他们就窘得赶忙行个礼,都不会站住。相反,多年不交谈的哀斯白闭夫妇却和少校相互接触起来——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终于联盟——有天晚上,奥里维要克利斯朵夫向下望,他看见少校和哀斯白闭一家正在园子里闲聊。
克利斯朵夫对人们在一夜之间的这种转变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况且,他自己的问题的确也够他自己操心和头痛的了,他感到无比惶惑,简直无法控制,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现象。而比他软弱的奥里维却比他镇定多了,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这种传染病所污染的人,尽管一边面临即将到来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两派分裂,但无论怎样,他都知道,对两个迟早需要一战的两个信仰之间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也知道法国即将成为人类进步的实验地,而新的思想就必须用法国自己的思想来灌溉,让它茁壮成长。但他自己却不愿身陷其中:对于人类的互相残杀,他只想用安提戈涅的名言来表达: “我生而为爱,不是为恨。” ——对了,为了爱,更为了理解,那也是爱。在这个人们准备互相仇恨的时期,他认为自己有在大风暴中用理性去保持他和克利斯朵夫继续相爱的责任,——歌德对德国一八一三年的仇法运动也是拒绝的。
但,克利斯朵夫却无法保持安静,虽然,他可以感觉到奥里维的良苦用心;但在某种意义上,被德国抛弃的他不能回去,他就像苏兹一样,脑中全是十八世纪那些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可是,他心中依旧有一股热情,不知会引他走向何方,而且,他并不想把这种思想告诉奥里维,只是偷偷地收拾东西,准备随时回去,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他不再保持理性,他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热血。奥里维却只有悄悄地注意着,猜到了他的心思却不敢轻易地动问。此刻的他们,彼此间更需要心灵的相互接近,事实上也更加相爱,但他们却怕谈话,恐怕两人会在思想上存在分歧而导致两人的分离,当四目相对,他们体会到对方淡淡的不安,好像是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只能什么也不说,心中万分苦闷。
但是,在天井对面那正在建造的房屋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依然顶着阴雨专心地敲着最后的几下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爱嘲弄的工人,远远地对他笑着:“瞧,我们盖好了!”
幸而这阵风雨很快散去。宫廷中半官方性质的广告向人们报告,明天天气即将好转后,刚才还在舆论界吵吵嚷嚷的狗就安静下来,重新回到窝里去了。几小时过后,人们紧绷的神经终于松驰下来了。那是一个夏夜,克利斯朵夫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奥里维这个天大的喜讯。他们都痛快地猛吸几口气,然后,奥里维微笑着看着他,小心翼翼地不敢将自己心中埋藏了许久的问题提出来,他只是含蓄地对克利斯朵夫说:“哦!你看,那些总闹脾气的人们,现在不也团结起来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对此报以微笑,“你们可真能开玩笑!彼此骂骂咧咧地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闹到最后原来都是一样的见解。”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我干嘛不满意?因为他们用我去换取彼此的团结吗?……得了吧!我可不会那么软弱,经历一次反对自己的高潮,看着这些恶魔在心里复苏,我倒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可是怕死了,”奥里维说,“我宁愿让他们孤独着,也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换取团结。”
他们都不再出声了,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提到彼此都慌张的问题。最后还是奥里维鼓起了勇气,他沙哑着嗓子问克利斯朵夫:
“老实说,克利斯朵夫,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要走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虽然答案是意料之中的,但奥里维听后心中仍然不免一震,他呐呐道:“克利斯朵夫,你竟然……”
克利斯朵夫用手拍了拍脑门,说:“我们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去想这些。”
奥里维痛苦万分,他继续追问克利斯朵夫:“你准备和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不愿去想。”
“可是你早已打定了主意,是不是?”
“没错。”克利斯朵夫回答。
“和我开战?”
“与你?不,永不!你是我的。不论我身处何方,我总是跟你站在一起的。”
“那么是对我的国家开战了?”
“为了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