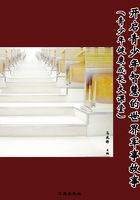第七章 户内1 (4)
十余年来足迹遍布欧洲,据说现在领导着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所以他在流亡四年后看到从前的同志成为掌握政权的人物,且干着丑陋的勾当时,便退出了党派,安静地坚守自己纯洁的信念,可是,他保持着较高的声誉。那个女孩则是他收养的孤儿:她长着淡淡的黄头发,黄眼睛,脸色苍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弱,满脸的病容,面无表情。华德莱之所以会收留她,是因为他对贫苦的儿童非常喜爱,仿佛是他那神秘的温情作怪似的。他学过医,预备帮助人家。他最难过的莫过于看到儿童有病受苦,当他看到他替那些儿童解除了痛苦,他们削瘦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时,他愉快极了。房东的女人却对那些穷苦的工人——在她的眼中就是无政府党——的进出很不满意,看到那么多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很气恼,对华德莱颇有责备,甚至说出些难听的话来。可是,华德莱不愿搬家:他有副古怪脾气,于是便不再理会房东的言语。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华德莱先生这才对他略有好感。克利斯朵夫发觉这个小女孩有点儿像萨皮纳的小女儿,这令他心中总有些暖意。但出于一种关爱,他很关心这稍嫌阴郁的女孩:她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也不爱说话,只是安静孤单地自己玩儿或拿着玩具娃娃编故事。华德莱却没有注意到她对人很冷淡和总是不安的神气,只是一味爱她,当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儿介绍给她认识时,他得到了两方家长客气而肯定的回绝。这些人,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三楼上的大公寓没人住,房东留给自己住,但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出门在外,冬天出去过冬,夏天在英国避暑。他以前是个商人,钱挣到一定的数目后,就洗手不干了。现在只是靠利息过日子,反正他又不花什么大钱。
三楼边上那个较小的公寓住的是亚诺夫妇。亚诺四十出头,是一位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和抄写。为此,他根本没时间来写博士毕业论文。他妻子比他年轻,比他小十岁,人相当和气,只是怕羞。因为没有工作,她呆在家里,但这贤惠的女人从不埋怨,尽量找事做:看书,或为丈夫预备笔记。抄写笔记,或是补衣服、做帽子。他俩相对来说都比较聪颖。因为没有熟人,他们亦从不出门,有时,做妻子的亦会想去看看戏,但后来却因为丈夫没兴趣——他太忙太累了——而取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俩非常爱音乐,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对那些音乐家的生平知之甚详,亦对他们充满同情。可是丈夫不会弹琴,妻子会弹却极度怕羞:她即使在丈夫面前弹琴也会像一个初学琴的小姑娘。而即使仅这一点,两人也心满意足了。他们两个人也热爱文学,但好的篇章在那时太少了。他们的生活平和、快乐,虽然有些伤感——亚诺先生的思想相当有深度——这也使这对孤独的夫妇的人品远高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却没有勇气和空闲把它写出来——他认为那些只是虚名,他经常把所有的钱用来买书:这使他们那美丽的意大利之旅永远不能成行。因为他们很明白,他们自己是不会积蓄的。亚诺的妻子理解他,因为她也爱书,这让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和自己共同分担勤苦的生活很幸福。他们没有孩子,这一点反而使他们更相爱,亚诺太太心地极好,非常乐意与工程师一家交往,但却因为别人未表示而不敢去接触。关于克利斯朵夫,他遥远的乐声已令他们陶醉,故当克利斯朵夫去结识他们,正是他们乐意之至的——要不然,他们才不愿首先迈出第一步,因为那太唐突。
住在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是一对有钱的犹太人夫妇,但却没有儿女。与其说他们住在这儿,还不如说他们是这儿的过客,因为他们一年到头有六个月住在乡下。他们虽然因为习惯使然而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但由于从不和邻居交谈,人们对他们的事并不比他们搬来的时候了解得更多。虽然他们夫妇为人善良,喜欢帮助人家,在做慈善事业,可是,他们却不受欢迎,因为韦尔先生嘲弄别人的天性太难抑制了。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因为在他面前觉得自己可笑而不肯原谅他们。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
六十岁的韦尔是个亚述考古学家,因为中亚细亚的发掘而享有盛名。他厌倦了远东的发掘工作,他就不做了,而且也没接受任何公司的职务。他生在有钱人的家里,没法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而且,他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决不满足于自己的专业学问,他对所有的学问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平时注意着很多事:美术、数学、社会问题及一切思想界的运动。但他却从未为了任何一门而入迷:他很聪明,反而不受约束。他的妻子有着坚定的道德信仰,富有同情心,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们两人很相爱。
最底下那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和他的女儿。他叫夏勃朗,是个少校,以前驻扎在殖民地,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立过显赫的战功。他现在每天只是散着步,看着花坛,吹着技巧永远没有进步的笛子。要不然,他就笨拙地按着那气喘吁吁的风琴,呜啊呜的,令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愤。但有时,他会埋怨政治,埋怨他疼爱的女儿,但他女儿却用清脆的声音,和善地回答他。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十分可爱,为了孝顺她的父亲,她没有出嫁,她大半天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发呆,或收拾园子,每天高高兴兴地陪着父亲。反正,他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
所有的这些人,孤独地在这个花园里住着,外界的风根本吹拂不到他们平静的生活。虽然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和梦幻淹没了,但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怀疑的老学者、失望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傲慢的还是悲观的,都在工作,而泥水匠还边唱歌边工作,只有克利斯朵夫因为感情丰富,用他们所不知的、洞察一切的同情心去体味他们,虽然他不了解他们。他不能像奥里维那样熟悉法国,但他却爱着他们,自然而然能为他们着想,想象他们的处境,他终于静静地参悟了一切,听着这些心灵无声的音乐:这屋子周围,尽是一些精神上孤独的人群——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或已结成团体的人。
奥里维为了进一步引导他,他经常拿着他想发表文章的那份杂志——《伊索》给克利斯朵夫看,它以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的:
“有人去市场上卖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买主问第一个奴隶能做些什么,他卖力地吹嘘了一通,问到第二个,回答比第一个还能干。轮到伊索时,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能做一切事;我自然不会的。”
这是蒙丹对所谓“以拥有知识的自夸自大之徒”的讽刺,《伊索》被称为怀疑派,但却拥有更深刻的信仰。当然,因为群众喜欢一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学,或者是一些没有破绽的谎言,所以,这个讥讽的面目对群众没有影响。
奥里维他们却不顾这些。因为法国的民主化加速了他思想的贵族化,除了那些入门的人外,科学让人难以接近。而像奥里维那种更关注行动和思想道德的文人,也带着明显的贵族气息,纵使像艺术——至少是尊重美的那一种——也对人紧闭门扉,瞧不起群众。他们也无所谓,他们要的似乎是保持内心的纯洁,而不是教育别人,他要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只求证实。
他们这些作家里也有大众艺术家,即使是在最真诚的人里亦有些人在传播无政府主义,传播一些现在只能让人的心灵受到折磨、受到伤害,却要在一百年或几千年后才能证实的未来真理。另外,还有些人却写些沉痛或讽刺的戏剧——是让人悲伤的戏剧。克利斯朵夫读后,认为本来想暂时忘掉痛苦的观众在经历这份消遣后定会抑郁不欢,从而觉得他们可怜。
“你们给民众看这个吗?那会让他们窒息的。”
“放心,”奥里维道,“大众根本不看。”
“那是理智的!你们简直疯了,难道你们要让他们丧失生活的勇气吗?”
“为什么不呢?让大众意识到生活的悲惨面后,仍旧打起精神去面对它,去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任,这难道不应该吗?”
“打起精神?我根本不会相信,最恰当的应该是毫无兴趣,而当一个人的生活乐趣被完全拿走了后,我相信他就完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不能扭曲真理吧!”
“可是也不能全说出来!”
“我真不敢相信这话竟然是你所说的,你不是要永远追求真理,爱真理高于一切吗?”
“是的,对于我,对于那些坚强到足能忍受的人,我们可以把真理给他,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把真理传给他们简直是胡闹,是一种残忍行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本国看不到的东西:我喜欢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敢和爽快,但却厌恶你们的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不顾后果地把它往社会上一摔。我们德国人却不会这样,他们注意生活,谨慎小心地只看想看见的事。倘若你们是为爱真理而牺牲,我会很尊敬你们而无话可说;然而你们却为了爱真理而让别人痛苦,那却不行,那太残忍了。我认为,爱真理应当胜过爱自己,而爱别人还在真理之上!”
“难道为了这个还要说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了奥里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