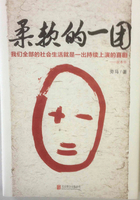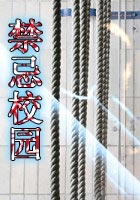第六章 安多纳德 (1)
耶南是那种血统纯正且踞守内地的世家之一。在经过众多的社会变革后,这种世家出乎意料地在法国依然众多,更重要的是,世家与乡土之间有一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深的联系。除非出现重大变故,否则,你永远也无法使他们脱离本土。这种依恋情绪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利害关系可言,纵使是因为史迹而怀古,却也仅是少数墨客才会如此。然而,有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感觉一直在所有人心里滋长,仿佛他们是这土地的一分子,与土地息息相关,感受它最细微的变化。总之,它们的心是相连在一起跳动的。要知道,能打动人心的,不是非得是景色怡人,那些最纯朴且最贴心的地方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耶南一家就是住在法国中部的世家,那里没有一点儿胜景,也没有一座纪念建筑或古迹。那里有的只是湿润的土地、静默的小城以及单调的田野、农田、草原、小溪、森林等等总之,它那单调黯淡的面目在那条浑浊静止的运河中暴露无遗。然而,虽然这里一点儿都不能引人入胜,但它那种沉默却有一种吸引力:它那静止的景象及那种静谧的空气,那种单调,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是一种深沉的甜美,是惹人喜爱的,忘不了的,而初次领教的人则会不能忍受。
耶南一家世代就住在此地:因为家中一位稍长的人,一生就在辑录家谱,把一些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人物材料整理起来。所以,耶南人住在城里或乡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在所有人当中,安东尼?耶南的父亲奥古斯丁是较出名的,因为他很会做买卖,又在城里办了一个银行。当然,他非常能干、勤劳,而且做事不太拘泥,做人又挺规矩。但爱享受,又有农夫般的狡猾和顽强。平常,因为他爱开玩笑挖苦人,说话直言不讳,又因他资财雄厚,故颇得人们敬重。他精神饱满,又矮又胖,留着痘疤的红脸上有一双神采熠熠的眼睛,是个典型的南方汉子。另外他很好色——至今还改不了,而且好吃好喝,喜欢讲一些粗野的笑话。当他与推事、公论人及神甫等等(当然,耶南老头儿是瞧不起教士的,但若这个教士能吃的话,又另当别论)几个和他同类的人吃饭时,那么满屋子都是粗野的笑骂,连厨房里的仆役和街场上的邻居都被这快活劲儿给逗乐啦。
后来,在夏季的一个热天里,老奥古斯丁因为去地窖装酒,得了肺炎,当晚便去世了。虽然他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但为避免妇女们的罗嗦,他像那位反教会的布尔奇亚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履行了所有的教会仪式。当然,他对这些手续无所谓;再则,死后之事也说不清……
儿子安东尼继承父业,安东尼如他父亲一样,是个矮胖子,有一张留有鬓角、绯红且欢欢喜喜的脸。他说话短促,语音含糊,声音较响亮,且爱打手势。因为银行的历史悠久,而且又处于发展之中,所以他只需守着这份家业就行啦,因为他很有规律,又很用心去办事,故办事能力还不算坏。只是他没有父亲的理财能力,故对事业的成功没出多大的力。安东尼有一股平民气息:殷勤、爽直,时常真情流露——他不浪费金钱却滥用感情,爱流泪,为任何灾难真心难过——这使受难的人感动,所以无论在何地,他的人缘都较好,并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说,他是个体面人。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个外表激动而心肠温和的老革命党,是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他是个市议员——像所有的同僚一样,他爱捉弄本地区的神甫和宣道师,并以此为乐。而反教会的举动,则永远是他们夫妻争执的内容——正如这个小城的每一个家庭一样。
安东尼爱好文学,像他那时代的内地人一样,他受拉丁文学的影响较深,能背诵其中的一些文章,而且对拉?封丹、布瓦洛、伏尔泰等的格言和十八世纪小品诗人的名句都有所了解,还能摹仿他们写的诗——这个癖好给他带来了声誉:因为在他的圈子里有不少这样的人,他的滑稽诗、四句诗、限韵诗、讥讽诗、歌谣等等被到处传抄。有些虽然很唐突,比如说口腹之欲的神秘,但是,它们却很风趣。
安东尼,这个健康、快乐、活泼的汉子,却有一个与他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性格相反的妻子——吕西?特?维廉哀——她的姓原本只是特维廉哀,后来却不知为什么一分为二,变成为特?维廉哀。吕西?特?维廉哀又瘦又高,比安东尼高出一个头,身段婀娜,又很会打扮,举止大方但有些拘谨,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她很贤惠,但对别人却很严格,不允许有丝毫过失,使大家觉得她很严厉傲慢。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们家世代都是法官,是法国司法界中的人物——这使得他们看重人格尊严,做人诚实不欺,但显得有些迂腐。吕西?特?维廉哀对宗教很虔诚,为了这个,常与安东尼争辩,可是他们却很相爱。对他在实际事务里,两人都不很精明:安东尼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一看到别人对他友善,上当;吕西则因为对商业毫无兴趣,更是从不发表意见。
安东尼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安多纳德,一个儿子叫奥里维,比安多纳德小五岁。
安多纳德是个褐发姑娘,很漂亮,她有一张法国式的娇美的面孔。她的眼睛相当有神,下巴相当秀气,而她的小鼻子长得笔直——用法国一位老肖像家的话来说,是那种清秀的、笔挺的鼻子。她从安东尼那儿遗传来无忧无虑的脾气。
而奥里维则是个娇弱的孩子,头发淡黄——小时候因经常受疾病的光顾而健康状况不好。这一点,也使他赢得了全家的疼爱。但他矮小的身材及虚弱的身子使他很早就成为一个抑郁寡欢、爱幻想、怕死的孩子,他缺乏一点儿勇气:他怕见人,喜欢独自一人,觉得和其他孩子玩儿很不快活,他讨厌他们的游戏,尤其是受不了他们的打架,他挨他们的打——但不敢自卫,怕伤害别人——要不是靠着他父亲的地位,他的小朋友们恐怕会折磨死他。他心软,心思细腻几近病态:只要随便一句硬话,一个同情的表示或埋怨一句,就能使他痛哭一场。于是,他那健全的姐姐安多纳德便叫他泪人儿,并经常嘲笑他。
随着时光的流逝,安多纳德越长越美。别人这样说,她自己也清楚,于是高兴地给自己编未来的梦。而忧郁的奥里维则像女孩子一样需要爱别人,也需要人爱他,一接触外界就不适应,便躲进自己的世界去胡思乱想。他自己造出三个幻想朋友:约翰、哀蒂安、法朗梭阿,他老是和他们在一起,而不和年龄相仿的同伴往来。他睡得多。早晨,家里人叫他起床,他往往呆呆地出神。要不,他会把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更要命的是,双手浸在脸盆里,他也会出神。在书桌上写字或温课的时候,他又会不停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醒来,发现什么都没做。纵使在饭桌上,他也有出神的可能,人家和他说话,他会吓一跳,过了两分钟才回答,回答了半天又不知该说什么。他总是迷迷糊糊地对自己窃窃私语,过着单调的岁月。这周围的一切动静,家里的所有声音,都在他头脑中产生模糊的幻象。他经常像只不声不响的小耗子坐在一角,嘴里吃着东西,拼命地坚着耳朵听,并赋予那些声音和大人谈话的内容以自己的想象。虽然如此,这性格不同的两姐弟却十分相爱。
对奥里维来说,一年最好的季节是春秋时在郊外别墅过的日子。因为在那里一个人都看不到,他可以尽情地幻想,因为姐弟俩秉受了母亲的贵族脾气,故像所有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两个孩子是不接触平民的,他们对奴仆和长工有点儿厌恶,并有点儿害怕。在那儿,奥里维成天骑在一颗树上读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美丽童话,《天方夜潭》,或是游记体的小说——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对外界充满幻想,常渴望出游。当一个小树林把小屋子遮住了,奥里维便幻想他在遥远的地方,心里就很高兴。尽管四周尽是树木,他依然可从树叶的空隙里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和草原上的牛。尖锐的鸣声打破田野的静寂,和咯咯的鸡叫遥相呼应,仓库里传出一阵阵的捣杵声,万物跳跃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一行老是匆匆忙忙的蚂蚁,满载而归的蜜蜂,漂亮的却到处乱撞的黄蜂——所有的这些小生灵都急匆匆的,当他听到安多纳德在花园的那头儿把秋千荡得高高的而使铁钩摇得咯吱咯吱地响时,奥里维就安心地对自己笑笑。
安多纳德也在依着她的方式做梦。因为好奇又贪嘴,她成天在园子里跑:偶尔啄些葡萄,偷偷摘个桃子,爬上枣树,偶尔走过小黄梅树时轻轻摇几下,摇下些小黄梅;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偷偷溜入花园深处,尽情地在醉人的花心中嗅着,随后就把一朵蔷薇一眨眼摘到手,把赃物放在怀中,放在她敞开着的衬衣底下微微隆起的小乳房中间……还有一件被禁止而她却觉得挺有意思的事便是脱掉鞋袜,赤着脚踏在充满凉意的细沙或潮湿草地的小径上,或是踩在阴处冰冷的或是被阳光烤得发烫的石板上,要不然她会用脚、用腿、用膝盖去接触溪水、土地和阳光。要是心血来潮,她会躺在柏树荫下,望着自己近乎通明的手,心不在焉地印上几个吻,然后她会用藤蔓和橡树叶做成冠冕、项链和裙子,把自己装扮成野蛮人的公主,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拼命打转,直到晕眩得倒在草地上,把脸埋进草里,莫名其妙地狂笑不已。
两个孩子就这样打发时光,虽然只隔几步,但却互不干涉——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当安多纳德想捉弄小兄弟时,她便会走过去,把一把松针扔在奥里维的鼻子上。或者摇着他的树,威吓他要把他摔下来,要不突然扑过去,嘴里叫着:“呜!呜……。”
安多纳德有时拼命想与奥里维淘气,为霸占他的位置,谎称母亲在叫他,要他从树上爬下来,然后自己占上去。当然,这个连两分钟也安静不下来的姑娘根本不可能永远待在树上,当她骑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够了,看到奥里维快哭出来时,她就会爬下来、扑倒他用草擦他的鼻子。奥里维根本挣脱不了,只好躺在那里不动,装出一副可怜相,于是,安多纳德就抱他一下儿,笑着跑开,临走还往他嘴里塞一把草。
安多纳德老是笑,即使在夜里作梦也笑。每当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醒着、梦幻着时,安多纳德的傻笑及断断续续的梦话总把奥里维吓一跳,不过也有例外:当外边风把树吹得簌簌响,而猫头鹰又在哭,或者隐隐传来树林深处农家的狗叫声时,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奥里维看到树像幽灵一样在窗前摇曳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让他安心。
受到母亲的影响,安多纳德和奥里维都笃信宗教,特别是奥里维,受影响尤其严重。所以,当两个孩子听到父亲反对宗教的言论时,都很害怕。幸运的是,他们的父亲像多数不信宗教的布尔乔亚人一样,认为家里人信仰也好,故给予了他们自由,他主要是因为他虽不信教,但却信有神,而且必要时还要请神甫——那即使没有好处,也不见得有害,正如一个人不一定因为家里有火才去保火险。更何况,在敌方有些盟友也是好的——将来的事,谁也没有把握,他在自由方面是相当仁慈的。
奥里维很有点儿神秘,温柔和轻信使他需要一种依傍,在平日忏悔的时候,把自己交给可尽情倾诉的无形朋友让他感觉舒服;因为他对你张开双臂,可以完全懂得你的心思,体谅你——他简直失去了自我,他觉得信仰这东西是相当自然的,根本不知别人为何有疑问。他想,要不是别人心存恶意,便是上帝在惩罚他们:奥里维往往在这种谦卑和爱的空气中洗过了澡,认为心灵得到了净化。他还暗自向上帝祷告,求他点化他顽石般的父亲,他父亲有一次参观一所教堂而得到了个十字,使他大感安慰。
奥里维因为长得又瘦又苍白、体弱多病而感到非常痛苦。他特别受不了别人谈他的身体,他在逃避着人生,逃避着自己,沉浸在这个传说与信仰的世界里——他有严重的悲观情绪。但是,他自己完全不觉得,还觉得别人也一样,所以他从不在休息的时候到园子里玩,反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面吃点心,一面写遗嘱。
姐弟俩都有音乐素质——尤其奥里维天赋更高,所有音乐如信仰一样,成为他们可以躲掉白天信仰的避难所。但这仅限于趣味,因为内地人所谓音乐,就是本地铜管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逢节的时候奏的乐曲,或是教堂里管风琴所奏的浪漫曲和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弹不准音的圆舞曲波尔卡,要不就是通俗歌曲的序曲,莫扎特的两三支奏鸣曲。招待宾客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吃过夜饭,懂一点儿的都被请出来献技:他们先推辞,后来在大家的请求下奏一个拿手的曲子——在场的人给予高度赞美——老是那几支,在老地方弹错,因此,没有人在这方面指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