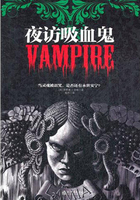斯佳·奥哈拉长得不算漂亮,但是一些被她的魅力迷住的人往往不会理会这一点,就像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那样。她脸上明显体现出父母双方的容貌特征:母亲那种法国沿海地区贵族后裔的优雅;父亲那种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独有的粗野。但这张脸有她吸引行人目光的地方:尖尖的下巴颏儿,方方的牙床骨,不含有一点淡褐色的纯粹的淡绿色眼睛,浓密乌黑的睫毛缀在眼眶,稍微有一点吊眼梢儿,两道又浓又黑的剑眉镶在上面,像在木兰花似的洁白皮肤上描出两道触目惊心的黑线。她那种皮肤倍受南方妇女珍视,她们总是用帽子、面纱和手套小心地将自己保护好,以免被佐治亚的烈日晒黑。
1861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同塔尔顿家两兄弟一起坐在塔拉庄园宅前门廊的阴凉处,那模样就同画中人一样。一件绿花布的新衣裹在身上,裙箍把用料十二码的波浪形裙幅铺展开来,正好跟一双平跟摩洛哥羊皮绿舞鞋相配,那是她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捎来的。她所拥有的三个县里最细的十七英寸的腰身,在衣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纤细;刚刚十六岁就有了非常成熟的乳房,在熨贴过的紧身上衣里十分抢眼;她仪态端庄,长裙舒展,一头乌丝光溜溜的,用发网拢成一个发髻,显出一副温柔贤雅的样子,但这些都难以掩饰她真正的本性。一对绿眼睛在那精心故作娇憨的脸上显得那样地爱动、任性、生机勃勃,与她的庄重截然不同。这副相貌是在母亲一贯的谆谆告诫以及黑人妈妈的严加管教下勉强养成的,真正能显露出她的本色的是她的那双眼睛。
神态悠闲,懒散地靠在她两边椅子上的是那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眯着眼享受着从明亮的长窗里射进来的阳光,齐膝的长靴衬得腿肚子鼓鼓的,悠闲地架着。他们正在闲谈。十九岁的年纪,骨骼高大,肌肉结实,六英尺二英寸的身高,深枣红色头发下是被晒得黝黑的脸庞,眼睛里神采飞扬,射出一股傲气,一般无二的蓝上衣,芥茉色马裤,就像是一模一样的棉桃。
夕阳斜照屋外的院子。在一片新绿背景衬托之下,开着一簇簇饱满的白花的山茱萸被映得闪闪地散着亮光。马车道上拴着哥儿俩的坐骑,都是高头大马,有着和主人头发一般的红色皮毛。一群精瘦、不安于专门猎捕的猎狗围在马腿周围吵闹着,斯图尔特和布伦特不论到哪,都能见到这些猎狗。一条跟随着马车的黑花狗躺在不远处,那神气,就像当上了贵族一样,口鼻全搁在爪子上,不慌不忙地等着哥儿俩回去吃晚饭。
在猎狗、马儿和哥俩之间有一层亲密的关系,就像亲属似的,远比他们那种持久的伙伴关系深。主人的家畜都是那种身体强健,没有其它杂事的幼仔,全部精神饱满,优雅得体,而且油光顺滑,兄弟两个更如那两匹马一样,不仅精力充沛,而且还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是对一种人却例外,那就是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对于那种人,兄弟两个一向是脾气温驯的。
这三个坐在门廊里的人虽然天生过着舒适的庄园生活,一出生就是人们细心呵护的对象,但从他们的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并非脸色苍白,也非细皮嫩肉,他们就如同一辈子在忙乎农活的乡下佬一样生龙活虎。佐治亚州北部的克莱顿县的生活还算新奇,而如果用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等地居民的眼光来看,未免有点俗气。充满严肃,呆板的南部地区的人们对位于内地的佐治亚人很瞧不起,但在佐治亚北部,对几件要紧的事精通后,就可以了,文章理论上的欠缺不算什么。具体地说,种得出好棉花,骑马的好身手,高强的射击本领,轻盈的舞姿,陪伴女士时的潇洒风度,豪爽的酒量而分毫不显醉意,都称得上所谓的要紧事。
对于这些“要紧事”,哥俩当然件件都精通,但书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刑罚,没法接受。他们的无能程度也是同样出众的。他们家的钱、马、奴隶在县里是最多的,可附近大部分穷苦人都比他们腹中的文墨多。
今天下午,正是由于这些,他们两个才会在塔拉庄园宅前门廊里闲坐。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已经是两年内的第四次了,作为他们的兄长的汤姆和博依德也一起回到家中,他们对这所不欢迎他们弟弟的学校不感兴趣。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视这次开除为一个绝好的笑料,斯佳也一样觉得可笑,因为自从上一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她从来都不愿接触书本。
“你们两个和汤姆都不在乎被开除,”她说,“被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赶了出来,如今又是佐治亚大学,一味这样,他可别指望毕业了。”
“噢,他完全能在费耶特维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学习法律,”布伦特满不在乎地答道,“再说,这也没什么,我们总要在学期结束之前赶回家。”
“那是为什么?”
“傻瓜,因为战争呀!这场仗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开始,你认为打起仗来,我们还会留在大学里吗?”
“但根本不会打仗,”斯佳面带傲慢之色,“只不过是传闻罢了。咳,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上礼拜跟爸讲过,我们在华盛顿的官员要同林肯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不管怎样说,北方佬十分怕我们,根本不敢打,也根本打不起来,我早听烦了。”
“根本打不起来?”兄弟俩高声喊道,就像是上当受骗一样。
“我说宝贝儿,仗是一定要打的,”斯图尔特说道,“北方佬可能怕我们,但前天博勒如尔将军用大炮把他们赶出苏奴特堡以后,这仗就非打不可了,不然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它是懦夫。咳,南部邦联。”
斯佳听后十分不耐烦地撇了一下嘴。
“如果我再听见一声‘打仗’,我就到屋里去,关上门。除了‘脱离联邦’这句话之外,最令我厌烦的就是‘打仗’了,父亲早上说,中午说,晚上还要说,来拜访他的老爷们也都喊着什么苏姆特堡呀,州权啊,亚伯·林肯啊,我厌烦得就要喊救命了!小伙子们也似乎都对这个感兴趣,还总谈那个该死的老骑兵连。今年春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宴会有意思,小伙子们都没什么好谈的。如果佐治亚州是在圣诞前脱离联邦的,那么圣诞节也太煞风景了。还有,如果再听见一声‘打仗’,我就回屋去。”
她可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如果别人谈话时不把她作为主题,她是不会高兴的。但她讲话时脸上的笑容依然如故,只是酒窝显得更深了,浓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扇个不停。兄弟两人自然逃不出她的算计,被她迷倒了,一个劲地赔礼,而且说刚才不该扫她的兴致。他们没有因为她缺乏兴趣而鄙视她,相反倒看重她了,打仗嘛,男人的事,不关女人什么事,于是,这种态度被视为她具有女人特性的最好证明。
她的哄骗得手之后,三人又回到了他们现实情况的话题上来。
“你们被开除,你们母亲怎么说?”
一回想起被大学开除后母亲对他们的管教方式,两人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个,”斯图尔特说,“她还没得到机会讲什么,我们和汤姆今儿一大早就出门了。当然了,母亲当时还没起床,汤姆到方丹家去了,而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那你们昨晚回家她说了什么吗?”
“呵,昨天好运气,我们到家时,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种马刚好运到,家里忙坏了。那个大畜生可真威风,你一定要让你父亲去看一眼。运来的半路上那马已经啃掉了马夫一块肉,而且还踩了妈派去接站的两个黑人。我们到家之前,马厩差点让它给踢倒了,还有那匹叫草莓的老种马也被踢了个半死。等我们到家时,妈在厩里,居然用一袋糖把它哄得老老实实的,而那几个没用的黑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吓得要死。可妈却亲手喂它,就像家里人一样和它说话。要说对付马,谁也不如妈。她一见到我们就说:‘天,你们这些家伙又到家里干吗?简直比瘟神都要命!’这时候马又开始喘粗气,而且把后腿立了起来,妈就说:‘滚,没见到把马吓着了吗?明天再找你们算帐!’,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去了,今儿早上溜了出来,留下博依德应付她。”
“她会打博依德吗?”个子矮小的塔尔顿太太经常威吓已经成了大人的儿子,那是同一县里的人都看不惯的。当然也包括斯佳。如果有必要动手的话,她还会用马鞭抽他们呢。
贝特丽斯·塔尔顿是个大忙人,手下除了种植棉花的大庄园,一百个农奴和八个儿女之外,还拥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的脾气火暴,经常被那几个孩子烦得够呛,不时,她还会抽打他们几下,尽管她从不让人抽打奴隶和马。
“博依德当然不会挨揍,因为她从来不打老大,再说了,他是我们中最矮的一个,”斯图尔特很自豪地说道,因为他对自己六英尺二的身高很得意。“所以他才被留在家里,天呀,我们都十九了,老妈为什么还要抽打我们,汤姆都已经二十一了,可她还只当我们是小孩子。”
“明天的烤肉宴会你母亲会骑新马去吗?”
“她要去,可爸说太危险了,况且,几个姐妹坚决不让她去,如果她去,至少她应该像个夫人一样坐马车去。”
“希望明天别下雨,”斯佳说,“瞧那晚霞,我没见过比这更红的了。只要看晚霞就可以知道天气了。”
“没错,明天会热得像六月天一样。”斯图尔特应和道。
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杰拉尔德·奥哈拉那片无边无际的新垦棉田对面红彤彤的地平线上。太阳落到弗林特河那边的山后,映出了一片深红,这温暖的四月也渐显柔和的凉意了。
那一年春天来得格外早,几阵暖洋洋的骤雨之后,粉红的桃花,星点的雪白的山茱萸都绽开了笑脸,暗淡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也花团锦簇。春耕已近尾声,新犁开的佐治亚土地在血红的落日映照下更加红了,它们像饥饿的孩子一样等待着新的棉种。犁沟砂土质的表面现出暗红色,沿沟一带边上随着阴影的变化,分别呈现出朱红、猩红和枣红。白粉砖墙的庄园宅院像是一汪红色海洋中的小岛,这里汪涛滚滚,变幻莫测,出现各种形状:月牙、曲线……这里不存在又长又直的犁沟。像佐治亚中部平原上的黄色土地或沿海地区的黑色土地,随处都是这种犁沟。在佐治亚北部的丘陵地,为了防止肥沃的土壤被冲入河底,人们总是特意把犁沟开得弯弯曲曲的。
这一片红得刺目的沃土,在雨后尤为红艳,旱时便是铺满一地的红粉砖,故而这里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棉场。在这里,有着洁白的房屋,和平时代翻耕过的土地,悠悠流过的黄色河流,但同时也是一个阳光灿烂和阴暗深浓形成强烈对比的地方。渴望被种植的空地以及连绵数英里的棉田含笑淋浴在宁静的日光中。一片片的处女林保护着这块田地,即使在炎炎夏日的中午它们也是幽凉的,而且略带神秘,但有着一丝的不友好,那些松树有着极深的涵养,似在轻声警告着:“小心呀!你们以前属于我们,我们随时能把你们收回。”
伴着得得的马蹄声以及奴隶们尖利的嬉笑声,走廊中的三人意识到干活人和骡马都归来了。屋里斯佳母亲爱伦·奥哈拉柔美的声音飘出,她在呼唤一个提篮子的黑女孩儿。“来了,太太。”后者轻脆地答应着,跟着是一阵脚步声,那是她走向薰腊室的声音。爱伦要去给归来的农奴们分食物。跟着就是一阵叮叮咚咚的类似进行曲一类的声音,这是兼管衣着和膳食的男仆向大家发出的晚饭信号。
同时,这些声音也向孪生兄弟二人发出逐客令,可现在家中的母亲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他们便在塔拉农场外不住地徘徊,急切地希望斯佳邀他们留下来共进晚餐。
“咳,斯佳,说一下明天的事吧,”布伦特首先憋不住了,“虽然我们当时不在,不了解具体的事,但不能光凭这点就剥夺我们跳舞的权利,你一定还没和他们说定吧?”
“恰恰相反,我已经和他们说定了,我可不知道两位公子都会回来呀,我可不敢冒那个险专门等着二位回来,等着伺侍两位呀。”
“你会侍候我们!”两人不禁大笑起来。
“看,亲爱的,第一个华尔兹必定由你我完成,而最后一个则是你和斯图的事,之后我们一起进餐,又像上一次一样请金西嬷嬷为我们算命。”
“别提她,我可不喜欢她给我算命,她居然说我会嫁给一个黑头发、长长胡须的男人,要知道,我根本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让我猜,亲爱的斯佳,你一定喜欢红色头发的男人,对吧?”布伦特傻笑道,“现在,你决定只和我们跳舞,并且共进晚餐,对吧?”
“如果你答应的话,作为奖励,我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斯图尔特神秘地说道。
“秘密”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咒语一样一下子使斯佳活跃了起来。
“是不是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消息,你不能说,你应该明白,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你忘了吗?”
“嗯,是皮蒂夫人对我们讲的。”
“哪一位?”
“你应该知道的,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媚兰和查尔斯的姑妈,她就住在亚特兰大的。”
“噢,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呆头呆脑的老太婆,她也许是我今生所见过的最傻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