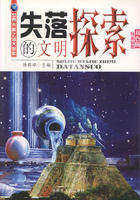最初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线条是古代那斯克人的道路。但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期,考古学家利用飞机多次在荒原上空飞越考察,发现大批分布很广的复杂记号,此说从此被推翻。除了线条,机上考察人员还看到许多巨大长方形和其他几何图形,以及许多种动物的优美线条画,包括猴子、蜘蛛、蜂鸟甚至鲸,也有花朵、手掌和螺旋形图案,每个长约1米至183米不等。这样的线条显然不是道路。
虽然有些线条长达数公里,但不论它们越过哪一种地形,或甚至伸展到山顶,其直线的偏差在1公里内不过1~2米。究竟那斯克人在荒原上留下这样的记号来干什么?这些线条绝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当时那斯克人不可能由高空俯瞰欣赏。同时,这些线条不管在高空摄影照片上显得多么壮观,也不是古代科学或工程杰作;因为只要动员1000名印第安人,费时3个星期,便可把所要移去的石头移去。至于线条何以会笔直,则可能是先排列几根标杆,在其间拉绳索画出直线来。用这种简单办法,如果与远方的一个准则点连合运用,只需要两三根木杆即可。
最使学者感到兴趣的并不是线条如何造成,而是线条有何用途。1941年,美国考古学家科索克首先到那斯克研究,发现许多线条和图案,并且一一记录下来。他的结论是:线条用以观察天文。此一说法引起德国数学家赖歇的兴趣。从1946年开始,她穷毕生精力,企图揭开这些线条的奥秘。赖歇和科索克一样,相信这些线条指向主要星座或太阳,以便那斯克人计算日期。她认为那些动物以及别的图形,也许代表某些星座,因此整个复杂的记号网很可能是一个巨型日历。
赖歇发现许多记号似与太阳或星座排成直线,但缺少确实证据支持她的说法。1968年,华盛顿史密生天体物理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霍金斯,在英国南部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巨形石柱”发现类似的天文定线之后,接着便将注意力转向那斯克线条。霍金斯拥有一种极有利的工具,用以探查那斯克人们的奥秘。这种工具就是电脑。他将彻底考察得到的资料输入电脑,藉以查测每一条直线在过去7000年内,是否曾对准太阳、月亮或一个主要星座。结果显示出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定线。例如,一个名为“大长方形”的图形,在公元610年及其前后各30年内,对准昴星团。这个日期,与现场发现的一根木柱经放射性的碳素测定法鉴定的年代不谋而合。这个办法虽然可证明那些图形年代久远,但电脑仍不能解开线条的奥秘,因为那些似有特殊意义的定线,看来只是巧合而已。
1977年,英国电影制片家莫理林亦加人这项研究。莫理森曾在南美洲拍过几部电视片,其中包括赖歇和霍金斯的研究工作纪录片,因此也对这个谜团深感兴趣,决心要找出答案。莫理森认为要寻求解答,必须明了那斯克人的风俗和宗教。虽然那斯克人早已消失,但在安第斯山脉其他地区,某些地点亦有类似的线条存在,因此他希望居住在那些地点的印第安人,能够透露造这些线条的意图。
莫理森的好奇心受1926年发现这些线条的瑟斯丕启发。瑟斯丕告诉莫理森说,他相信这些线条是印第安人专作宗教用途的路径。瑟斯丕早在1939年就提出这种说法,但苦于找不到证据。莫理森则发现了一点线索,那是一本记载1653年以后事迹的西班牙编年史,里面记载印卡帝国首都库斯科的印第安人如何从太阳神殿出发,踏上伸向四面八方各直线,到沿途安设的神龛参拜。既然那斯克荒原上的线条在一堆堆石头之间,那些石堆不就是笔直的神圣路径连接的神龛吗?
于是,莫理森前往库斯科,希望找到那些神圣路径。他此行没有成功,因为路径的痕迹早已全部湮灭。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到邻国玻利维亚搜寻。1977年6月,莫理森终于在一个艾马拉人聚居的荒僻地区,找到了一整批并非移去荒原上的石块,而是割除灌木形成的线条。这些线条和那斯克荒原的线条一样笔直,也是不顾任何地势阻挡成直线向前伸展的。同时,正是这些线条将用石堆筑的神龛连接起来,而且许多神龛还筑于山顶。
艾马拉印第安膜拜这些石堆,相信石堆里面住着祖先和魂魄或当地神明,常常供奉一些小祭品或古柯叶(一种作用和缓的麻醉剂)。莫理森发现,好几条连接神龛的路线在一座庙宇会合。印第安人即沿着这些路线前往庙宇,途中不时停下来向沿路的神龛参拜。在他们看来,偏离这些路线就会走人妖魔鬼怪领域。艾马拉人还相信,神龛位置超高,其中神灵越具神威,由此可知为什么这里的路径也和那斯克的一样,不避任何险阻而直达山顶。
莫理森在后来所著的《朝圣之途》一书中,以生动笔法叙述他冒险探秘的经历,而且说出他相信那些线条就是“朝圣之途”。他认为那斯克图形可能是代表神灵及动物的精灵,那些已经清除石头的大块土地则可能是宗教集会的地点。至于这些线条的历史年代,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尚无法确定。最多我们只能说那斯克线条可能有1000至2000年的历史。
那斯克线条之谜迄今尚未完全揭晓,莫理森的结论仍然有待证实。而且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有些线条的确像天文学上的定线。目前,那斯克线条受到保护,以供日后研究,因为每一块没有翻起的石头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线索。
不用计算机能证明“四色问题”吗?
1976年有两位年轻的科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应用计算机证明了“四色问题”。当时为世人所震惊。这是依靠计算机证明的惟一的大定理。
“四色问题”也称“四色猜想”。我们在绘制地图时,为了区别一个国家与它的邻国,一个省区与它邻近的省区,总要给不同的国(省区)与它的相邻近的国(省区)画上不同的颜色。当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彩色地图册就会发现,只有四种颜色。也就是说,用四种颜色就可以把各国(省区)区分出来。这就是“四色问题”。更确切地说,在平面上或球面上绘制地图只需要用四种颜色。
提出四色猜想的第一位数学家是德国的莫比乌斯,这是1840年的事。1850年一位英国学生叫葛斯瑞也认为绘制地图四种颜色足够了。其后不久,他给弟弟写信并“证明”这个猜想正确:可惜这个证明被遗失了,许多数学家认为此证明可能也是错的。他的弟弟把葛斯瑞的这一想法写信告诉美国几位有名望的数学家,希望他们证明四色猜想。但直到1879年,其中的凯雷虽然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但他宣布无法证明四色猜想。
继凯雷之后,有一位从事律师工作的肯普在数学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他“证明”了四色问题。可惜,他的证明也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1899年被数学家希伍德指出。而希伍德本人发表了一篇严密论证的文章,但是他只证明五色,没有证明四色。当然,从五色着手改进方法或许能证明四色,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从那以后一百多年以来,许多数学家都想证明四色猜想。开始选择另外的方向,在国家数目上加以限制。首先是费兰克林在1920年证明,当国家的数目≤25时,四色定理成立。1926年国家数提高到27,1936年提高到31,1943年又提高到35,1968年又提高到40。为什么国家数目增加得如此之慢呢?因为每增加一二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关系类型就会变得复杂得多,而证明的关键是必须把地图的所有类型都考虑进去,这就给证明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很长时间内,四色问题未能加以证明。
1976年,阿佩尔和哈肯利用计算机加以证明,前后花了七个月时间。第一步是把所有可能的地图类型归结为有限多个不同的类型,他们归类成1936个。仅这一步就耗时六个月;第二步是证明它们用四色足够,花了一个月时间。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个证明。
但是从1976年以来,有不少数学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不论怎么说,这件事本身说明电子计算机对数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的想法是,能不能找到不依赖电子计算机的人工证明,关于这一关,仍然有数学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但愿功夫不负有心人。
寻找相亲数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有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学派的创始人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这个学派特别喜欢数、推崇数,他们把人性也赋予了数。比如,他们把大于1的奇数象征为男性,起名叫“男人数”;把偶数看做女性,叫“女人数”(也有史书记载,把奇数象征女性,偶数象征男性)。数5是第一个男人数与第一个女人数之和,它象征着结婚或联合。
人之间讲友谊,数之间也有“相亲相爱”可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常说:“谁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会像220和284一样。”为什么220和284象征着好朋友呢?原来220除去本身以外还有11个因数,它们是1、2、4、5、10、11、20、22、44、55、110。这11个因数之和恰好等于284。同样,284的因数除去它本身还有1、2、4、71、142,它们的和也恰好等于220。即
1+2+4+5+10+11+20+22+44+55+110=284;
1+2+4+71+142=220。
这两个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亲相爱,形影不离。古希腊的数学家给具有这样性质的两个数,起名叫“相亲数”或“亲和数”。
220和284是人类发现的第一对“相亲数”,也是最小的一对“相亲数”。17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找到了第二对“相亲数”17296和18416;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法国数学家找到了第三对“相亲数”9363544和9437056。最令人震惊的是,瑞士著名数学家欧拉于1750年一次就公布了60对“相亲数”。数学家惊呼:“欧拉把一切‘相亲数’都找完了!”
谁料想,又过了一个世纪,意大利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巴格尼于1866年公布了一对“相亲数”,它们只比220和284稍大一点,是1184和1210。前面提到的几位大数学家竟无一人找到它们,让这对不大的“相亲数”从鼻子底下轻易地溜走了。
最近,美国数学家在耶鲁大学的电子计算机上,对所有110万以下的数逐一进行了检验,总共找到了42对“相亲数”。下面列出10万以内的13对“相亲数”:
220=2×2×5×11,
284=2×2×71;
1184=2×2×2×2×2×37,
1210=2×5×11×11;
2620=2×2×5×131,
2924=2×2×17×43;
5020=2×2×5×251,
5564=2×2×13×107;
6232=2×2×2×19×41,
6368=2×2×2×2×2×199;
10744=2×2×2×17×79,
10856=2×2×2×23×59;
12285=3×3×3×5×7×13,
14595=3×5×7×139;
17296=2×2×2×2×23×47,
18416=2×2×2×2×1151;
63020=2×2×5×23×137,
76084=2×2×23×827;
66928=2×2×2×2×47×89,
66992=2×2×2×2×53×79;
67095=3×3×3×5×7×71,
71145=3×3×3×5×17×31;
69615=3×3×5×7×13×17,
87633=3×3×7×13×107;
79750=2×5×5×5×11×29,
88730=2×5×19×467。
这里把自然数都分解成质因数的连乘积,有了质因数就可以找出这个数的所有真因数,进而就可以判断两个数是不是相亲数。比如,220=2×2×5×11,284=2×2×71,其中220所含的质因数是2、2、5、11,这时就可以知道220的因数是1、2、2×2、5、2×5、11、2×2×5、2×11、2×2×11、5×11、2×5×11,一共是11个,这11个数相加恰好等于284;而284的质因数是2、2、71,由它们和1组成的因数是1、2、2×2、71、2×71,共5个,这5个真因数之和恰好是220,这样一来就证明了220和284是一对“相亲数”。由上面做法不难看出,把一个数分解为质因数的连乘积是寻找或证明“相亲数”的关键。
目前,找到的“相亲数”已经超过1000对。但是,“相亲数”是不是有无穷多对?它们的分布有什么规律性?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数学家也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这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结束了笔算寻找相亲数的历史。据70年代统计,人们共找到1200多对相亲数,并且,有人还曾有序不漏地用计算机检验与搜寻相亲数,例如近10年来,美国数学家在耶鲁大学先进的计算机上,对所有100万以下的数逐一进行检验,总共找到了42对相亲数,发现10万以下的仅有13对,部分地消除了对欧拉等人列出的相亲数数表的疑虑。但因计算机功能与数学方法的不够,还没有重大突破,越往下去,难度更大。
目前,寻找相亲数还有许多有待探求的问题,如:目前找到的每一对相亲数所含的两个数,总是同时为偶数或同时为奇数,是否存在一个是偶数,而另一个是奇数的相亲数?目前找到的奇相亲数均是3的倍数,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规律?等等。
5000年的人类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浩瀚无边的知识大海。在汪洋大海中最古老也最深沉的是数。数的理论研究成为科学基础的基础。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曾把数的理论置于科学之巅,这一点也不过分。然而,时至今日,这个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威严的“湖夫金字塔”,这里涉及的“亲和数”也是其中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世界难题,有许多谜待揭开,谁揭开谜谁就是英雄好汉。
上面回顾2000多年数学家的不懈努力,发现了1000对以上的相亲数,“看似平凡最崎岖,成如容易确艰辛”,未来的工作正等待着不畏困苦的数学家与计算机专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传说,古代有一个秀才游桂林的斗鸡山,觉得山名有趣,信口说出一句话:
“斗鸡山上山鸡斗。”
他想把这句话作为上联来对一副对联,可是下联自己也对不上来。回家后便请教自己的老师,老师想了一下说:“我不久前游览了龙隐洞,就以此给你对个下联。”老师念道:
“龙隐洞中洞隐龙。”
对得很巧。这是一副回文对联。
古代诗人王融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回文诗:“风朝拂锦幔,月晓照莲池。”反过来读:“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不管怎样读,都是一首诗。
有趣的是,数学家族里的主要成员数中也有回文的,你看数101,正着读倒着读都是101;再看32123,正着读倒着读都是32123。这种正反读都一样的数很多,数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回文式数,简称回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