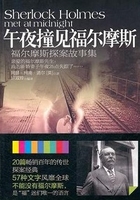第十五卷 (3)
自从成了孩子的父亲,勒内愈发愁眉不展,他终日在树林深处消磨时光。回到家里,他把孩子抱在膝上,又疼爱又失望,突然又把她放回摇篮里,好像不胜厌恶似的。塞留塔扭过头去,不让他看见她偷弹的泪,她把勒内的所为视作对她的憎恶。
勒内半夜归来,对塞留塔讲几句好言好语,塞留塔几乎掩饰不住她的回话的酸涩。白日,勒内走到妻子身边,她抱起女儿避开他;当勒内对塞留塔虚弱的身体表示不安时,她说这是生孩子造成的。她极力装出平静的神气讲动情的话,这种抑制自己,这种贤德和平静,越显她内心的紊乱。
米拉形影不离地追随勒内,她常到勒内家里来,塞留塔总是温和地接待她。
米拉对这位苦恼的妻子说:“如果你是我的母亲,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我听白人武士说过你兄弟的友谊,你也说过他的祖国的故事。我们一起收拾他的床铺吧,等他睡了,我用羽毛扇给他扇凉。”
米拉讲完话,扑到塞留塔的怀里,她是在暴风雨中寻找安宁,在中午的烈焰中寻找清凉。米拉看见塞留塔泪光莹莹的眼睛里露出怜悯,她刺伤了塞留塔的心,而这颗心还保留着对她的友情。
米拉的母亲被女儿的行为惹恼了,威吓女儿要泼水到她的脸上,这是印第安女人惩罚孩子的方法。米拉不甘示弱,她说她要一把火烧了母亲的房子。亲友们都笑了。米拉依然追逐勒内。
一天傍晚,勒内坐在湖边。新世界的丛林里到处有这样的湖,岸边有几棵孤独的凤仙花,鹈鹕缩着脖子,胸前的喙就如仿制品,立在岩顶不动。野雌火鸡在高高的木兰树上扬起沙哑的啼声,湖波平静有如一面镜子,照着如火的夕阳。
米拉跟着来了。“我也来了!”她说,“我承认,我很担心,怕人会骂我。”
“为什么要骂你?”勒内说。
“我不知道。”米拉坐下来,靠着白人武士的膝头。
“你不是怀有心事吧?”勒内问。
“上帝,”米拉大声说,“我会有心事?我喜欢胡思乱想,但我什么也记不住。”
米拉两只玲珑的小手放在勒内的膝盖上面,托着脑袋,望着湖水出神。勒内有点窘,但他没有推开她的勇气。不一会儿,他发现她竟睡着了。
多么天真的年龄啊,就不懂得避嫌疑!这信任别人的年代,你去得多么迅速!勒内低声喃喃道:“米拉!你竟能在这儿安睡,你多么幸福!”
“你说什么?”米拉从酣睡中醒来,“你为什么吵醒我,我正做着好梦呢!”
“与其这样子孩子似地睡觉,不如给我唱支歌。”
“你说得对,等等,我醒了。”她揉揉困倦和泪湿的眼睛。“我记得一首塞留塔的歌了。啊,塞留塔!她多幸福啊!她配有这幸福,她是你的妻子,是吧?”
米拉唱歌,歌声充满天真和快乐,她没唱多久,她记不全歌词。她埋怨自己记不住塞留塔的歌,哭了起来。
米拉母亲跟踪着女儿,发现她靠着勒内的膝头坐,她手拿一束丁香打女儿,米拉逃开,向母亲扔叶子。粗心的母亲怒不可遏,张扬了这件事情,它便四处传开了。米拉还亲口告诉塞留塔,她睡在湖边勒内的膝盖上。塞留塔无须找证人,就了解了自己的不幸。
勒内猜到了米拉对他的感情,但他装做浑然不觉。他对她态度严肃,他的严酷吓坏了天真的小姑娘。被拒的感情只好撤退,在所有爱勒内的人面前撤退:塞留塔,乌杜加米兹这个勇敢无畏,舍己救人,与她亲切游泳的小伙子。米拉常在塞留塔家里遇见他,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喜欢这个英勇幼稚的男子。
有一天她对乌杜加米兹说:“你从火里救了朋友,你真好!我也想做这样的事。”“你难为我了,你饿了吗,我拿吃的来。”小伙子答道。
“好的。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会用双手捧着你的朋友的脑袋,用我的唇暖和他的双目,我会抚他的心,看他的心是否还在跳动。”米拉把手放在乌杜加米兹的心房上面。
“别做这事,你恋爱了吗?”
“不,当然不是,是塞留塔告诉我的。”
青春的灵魂在飞翔。像孩子要尝甜的,苦的酒;青春要尝试各种感情,只有经历了各种感情才了解它们。米拉先是倾心于勒内,不久发现他与她隔着很远的距离,乌杜加米兹才适合米拉。他们的好感一旦表白就会牢固,而这好感快要诞生了。
唉!他们朴素优美的爱情本应在平静的天空下发展,却在暴风雨中形成!不幸的人们啊,你们生活在动乱的年代!爱情,友谊,休息,这些组成别的人的幸福的要素你们却缺乏!你们没有时间去相爱。在一切都是幻想的年龄里,严酷的现实却接踵而来。在一切都是希望的年华里,你们一点希望也得不到,你必须提早折断生活的联系,害怕增加很早就要打断的情结!
勒内离群索居,对四周发生的事不闻不问,他不去辟谣,也听不见有关他的谣言,或不屑理会。而毁谤却越来越严重,造成家人的不幸和担扰。他陷于个人的痛苦的回忆中,因这精神的孤独而变得渐次粗暴,野蛮,不拘小节,忽视职责,把别人的关心视作重负,厌恶温情,只想寻找刺激,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人,要去哪儿,不知道何去何从。他是否为了悔恨的爱情而不安!他隐瞒了他的罪行还是德行?大家都不知道不了解,大家似乎知道他的一切,除了真相。
塞留塔坐在家门口,终日痴痴地候着丈夫。她一点不责备他,只责备自己,她埋怨自己不够美,不够温柔,她的爱情慷慨、宽容。如果勒内有情妇,她相信她可以做这个情人的朋友,但当她怀抱孩子时,却止不住泪水满面。勒内回来时,塞留塔备好饭,她只讲温柔的话,只怕惹他烦,她把笑挂在嘴边,她偷眼看勒内,看见他脸色苍白,不安,她愿意献出生命换取他片刻的安宁。
夏克塔斯有时试图安慰勒内,但他套不出勒内的秘密。“你怎么啦,你喜欢孤独,你还未孤独够吗?你以为你的心是不竭的源泉,泉水流不尽?”
勒内答道:“当一个人发现幸福消失了,谁能不想结束生命?为什么不可分的朋友不能团聚于永乐的世界?”
“我并不比你更眷恋生命,”经验丰富的酋长夏克塔斯说,“你死了,你就被人遗忘了;你活着,你的生存占的位置并不比你的记忆占的位置大,不管我们感受到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意义都不大,为什么你要对转瞬即逝的感情耿耿于怀?你现在要承担对第二祖国的职责,你还有其他的职责要承担。也许你要的东西很快就来临了。”
老人的话就如神谕般灵验。果然,纳契人的灾难正在酝酿,翁杜列派去的信使回来,带来印第安各部落的佳音。法国的司令接收了新兵,不需如费布利亚诺所为那样,而是可以公开攻击勒内、夏克塔斯、阿达利奥了。色帕尔催促翁杜列履行割让土地的诺言,翁杜列答复说,只要摆脱了对手,可以马上着手。
由翁杜列点火,星相家煽风的有关攻击勒内的谣言产生了效果,纳契人相信大逆不道的勒内是法国人派来的奸细,而法国人认为勒内是法国的叛徒。
米拉常上夏克塔斯的家。这一天,一家人正在塞留塔的家里吃早餐,她看见士兵雅克走进来。他捎来中尉达尔塔吉特给勒内的信,如勒内不在,可交给尊敬的酋长夏克塔斯。这信件告诉勒内,逮捕他与阿达利奥的命令已经下达,“你一刻也不能拖延,快避开你的敌人,他们控告你煽动纳契人武装反对法国人,已指定军事顾问团审讯你,他们要关押阿达利奥入牢,除非割让土地,否则就对纳契人动武。他们还不敢动夏克塔斯。”
读了这信,塞留塔怕得发抖。她头一回希望勒内不回家,他已两天没回家了。塞留塔、米拉和乌杜加米兹商妥,跑到林子里寻找勒内,劝他远离村子。夏克塔斯和其他家人赶去阿达利奥家报讯。
阿达利奥拒绝逃走,他摊开一张席子,坐在地上,他不耐烦再听家人的劝说,吼道:“你们不怕丢脸吗?你们劝我什么话!我!叫我躲开歹徒!给年轻人做这种榜样?夏克塔斯,我期待的是祖国之父的另一种感情。”
“你要是被捕或牺牲,对祖国有什么好处?”夏克塔斯劝他,“相反,你若暂且撤退,明天我们也许可以组织自卫,反击那些压迫我们的人,阻挡我们自由的人,但今天我们已来不及了,我不知道是哪个阴险的人调开了大部分青年武士。”
阿达利奥说:“不,我绝不会撤退,我留下你替我报仇。”
阿达利奥操起武器,站了起来。他的家人不敢逆他的意,酋长又坐下来,大家默默无言。
他们听见外面响起一队士兵的脚步声,费布利亚诺带兵抓人来了。阿达利奥的左边是他的儿子,后面是他的老伴,他年轻的女儿怀抱孩子,阿达利奥的前面是拄着白棍的夏克塔斯。
费布利亚诺进来,发布命令,命阿达利奥跟他走。
“好吧,我跟你走,”阿达利奥说,“我看你认不出我了,那天打仗你领教过我的厉害了,你应该记得我的。”
他从席子上扑过去,用投枪头撞费布利亚诺的胸脯。夏克塔斯双目失明,他双手发抖,无法制止冲突,只能讲息事宁人的话。恶徒费布利亚诺后退,士兵冲向前,吼叫声响彻四周。女人们含泪死攥士兵的枪支,“砰”的一声,士兵开了枪,阿达利奥的儿子中弹倒在他身旁。酋长阿达利奥在儿子的尸体后面自卫,一会儿,夏克塔斯倒在地上,被践踏。浓烟滚滚,房子被烧,大家逃出屋子。阿达利奥被费布利亚诺捆绑了双手,和他的妻子、女儿、外孙被抓到罗萨里要塞。与翁杜列同谋的其他刺客,闯入勒内的住屋,却扑了空。
殖民地的居民成群涌到囚犯经过的路上,囚犯引起他们深深的怜悯,囚犯落到仇恨与虐待他们的人手里是很不幸的。中尉达尔塔吉特拒绝带兵到纳契人村里抓人,本人就遭受军事监禁,再不能救这一家人。
色帕尔召开顾问团会议,费布利亚诺宣称阿达利奥持械反抗,藐视国王的命令,他们只好逮捕他。会议持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押送叛乱分子到岛上做苦工,第二种意见是在罗萨里要塞卖掉他与他的家人。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司令选择最粗暴的手段,给纳契人以最沉重最恐怖的打击。心胸狭仄的人常把冷酷和鲁莽当作能干与勇敢。他决定立即公开拍卖阿达利奥一家,给殖民者做苦工。
翁杜列在罗萨里要塞偷偷逗留了几个小时。费布利亚诺把顾问团的判决告诉他,翁杜列很满意,他高兴杀了阿达利奥的儿子,烧了他的房子,他惟一遗憾的是未能首先干掉他的首敌,但他安慰自己,勒内很快就逃不掉厄运。
翁杜列期待纳契人会仇恨法国人,要求复仇,他的估计不错。从罗萨里要塞归来,他来到夏克塔斯召集青年武士开会的地点,自从阿达利奥被捕,他们就在这儿集中部落的人员,即丛林里的湖边,米拉躺在勒内膝盖上的所在。
年轻的武士们刚刚打猎归来,他们义愤填膺,都瞪着翁杜列,大声喊问:“太阳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训示吗?”
这个狡猾的野蛮人装出谦恭的样子,说:“我的意见是听从酋长们的意见。”
酋长们很赞赏他的谦恭,只有夏克塔斯识穿他的虚伪。
大家七嘴八舌说:“请女首领作个解释吧。”
“啊,不幸的纳契人!”犯了罪的亚卡西说:“他竟谋反!”然后不再作声。
“必须迫她讲话!”人群喊。翁杜列说:
“噢,武士们,请注意!据说夏克塔斯的养子是色帕尔要加害的其中一个,但他却逃过了我们的敌人的追捕,阿达利奥却锒铛入狱。酋长们和武士们,你们相信我吗?”
“相信!相信!”无数的声音应道。夏克塔斯的声音被群情激昂的声浪淹没。
“你们肯听我的命令吗?”翁杜列说。
“说吧,我们听你的。”众人说道。
“那好吧!回到你们的家里去,别暴露你们的仇恨,暂且忍耐,忍受不公平的待遇,我答应你们……,现在还不是说这事的时候。主教是复仇之神阿塔昂西克的化身,对,纳契人,我看见阿塔昂西克降临我们的山谷了,她的双眼如同两堆火焰,她的头发在空中飘扬,就如阳光穿过暴风雨的云层,她的躯体庞大无比,难以形容,看到她我毛骨竦然,产生濒临死亡的恐惧,她对我说,‘解放祖国吧,与我的祭坛的仆人商讨一切事务吧……’上帝向我揭示我只能向星相家请教的事,这是可怕的秘密。”
大家颤抖了。主教嚷道:“别怕,阿塔昂西克复仇之神把权力委托给翁杜列了。武士们,太阳的监护人要求你们,通过我的声音听他的命令,解散吧,回去吧,等上天替你们报仇。”
土著们听了这些话,怀着宗教的恐惧四散。丛林的黑暗和寂静增浓了这份恐惧。
翁杜列并不愿动员纳契人武装对抗法国人,纳契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取胜,这一次也与上次的对抗一般缺乏果断。他并不需要公开的合法斗争,他要稳操胜券的、更阴险的一击。而一切的准备尚未就绪,阴谋得逞的那一天为时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