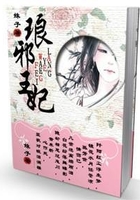第二十七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2)
帅克做了必要的解释,并举了几个例子,这些例子都是从自己遇到的不称心的事情中选出的。少校问他:“在审讯时,你为什么不说明这些情况呢?”帅克答道:“事实上,谁也没问我为什么会穿上俄国军装!而所有的问题只是:‘你承认你是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穿上军装的吗?’”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所以他只好答道:“当然——是——肯定——是这样——毫无疑问。”但毕竟他还是拒绝了审判时说他背叛皇上的令人发怵的控告。
“这是个十足的大白痴,”将军对少校说,“在池塘边随便穿一件俄国军装在自己身上,然后听任别人把他塞到俄国俘虏队里,只有白痴才会做这种事。”
“报告,”帅克说,“有时我仔细掂量过自己,我智力是有点儿低劣,尤其是当天黑的时候。”
“少啰嗦,你这阉牛!”少校边说边转向将军问如何如处置帅克。
“让他们旅去绞死他。”将军似乎拿定了主意。
帅克一小时后被押送兵押往火车站,准备被送到驻扎在沃耶利奇的旅部。
帅克从第三个柱子上掰下一块小木片在墙上刻下他在站前吃过的全部菜汤、调味汁和配菜的清单:这是帅克走后,军狱里留下的一个小小的纪念;或好像是表示对于二十四小时内没给他任何食物的一种抗议。
被连同帅克一起送走的便条上写道:
遵照四六九号电报指示送上十一连逃兵约瑟夫?帅克,请旅部进行详细审理。
这个押送队是由四个不同民族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分别是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捷克人。捷克人是领队,军衔为上士,对于他的同胞犯人总是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吓人地统治着他。到火车站时,帅克请求要小便,上士却精粗暴地说到了旅部才能小便。
“好吧,”帅克不得不同意,“那你立个字据给我,如果我的膀胱出了问题,也可以让人知道这是谁的罪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上士先生。”
这膀胱一下就吓住了上士这个木头疙瘩,于是在火车站上整个押送队如临大敌似的押着帅克上厕所。上士一路上神气得像明天至少能捞上个军团司令干干似的,总是扮演着残忍的角色。
当他们坐在普舍米斯尔到希罗夫去的火车上时,帅克对他说:“上士先生,当我一看到您,就马上联想起一个在特里顿特服役名叫博兹巴的上士。他当上上士的第一天就开始发胖,脸也鼓了起来,第二天肚子胀得就无法再穿下公家发的军裤了。最糟糕的是他的耳朵,也一直往长里长,只好把他送到病房,据队里医生说,所有的上士都有这种情况,刚开始是胀大起来,有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他的病情却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到最后,只好扯下来他那颗星星,他这才消瘦下来。”
自此以后,无论帅克怎样竭尽心机,这位上士都不理会他,而帅克还友好地向上士说明,为什么通常都说上士是连队的魔障。上士不回答,只是很阴沉地威胁帅克说,到了连部倒看谁笑到最后。一句话,他对这位同胞犯人不再理睬。当帅克向他打听他的家在什么地方时,他只淡淡地回答说不关他的事。
帅克想尽各种方法与他交谈,还告诉他,虽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押送了,但每次都跟押送队员相处得很愉快。
上士仍然保持着缄默,帅克接着说:“上士先生,我觉得,如果您忘掉了语言,就会在世上遇到不幸。虽然我认识许多悲哀的上士,但是,上士先生,像您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应该告诉我使您那么难受的事,大概我能帮您想想办法,因为通常一个被押送的士兵往往比看守阅历深些。不然的话,上士先生,您跟我们谈点儿什么,以便使路途显得短一点儿。例如,谈谈你们那儿周围的情形呀,有没有池塘呀,或者那儿有个什么古城堡呀,您还可以跟我们讲讲与它有关的一些传说。”
“够了!够了!”上士突然大叫一声。
“您真有福气,”帅克说,“有些人,什么时候也没有个够。”
上士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到了旅部自有人会来教训你的,我犯不着跟你白费力气。”从此就完全地沉默了。
几个押送兵也都闷闷不乐。因为匈牙利人只懂得两个德文字:“Iawohl”和“luas”。所以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就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在聊天,当德国人对匈牙利人讲述点儿什么时,他便点头说“Iawohl”,当德国人什么也不说时,他便问:“luas?”德国人就再重讲一遍。其中的波兰人依然保持着傲慢的贵族风度,从不理睬任何人,只是一个人打发时间。他很自如地用右手的大拇指帮着忙往地上擤鼻涕,接着若有所思地用枪托在地上蹭着,然后又文雅地用裤子擦弄脏了的枪托,边擦边嘟囔着说:“圣母玛利亚!”
“你还不算是个行家,”帅克对他说,“有个叫麦哈切克的清道夫住在战场街的一间地下室里,在这方面绝对是个行家,他把鼻涕擦在窗子上,能擦出莉布谢预言布拉格光辉前景的那幅画来。每画出一幅来,他就从他老婆那儿得到一份国家津贴费——嘴巴撑得像个大口袋,可他从不就此罢休,还越画越美。的确是这样,这也是他惟一的乐趣。”
波兰人没理会他。直到后来,整个押送队像送葬队伍正虔诚地在想念着死者似的鸦雀无声。
就这样,他们越来越靠近在沃耶利奇的旅队了。
这时,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赫尔比希上校担任旅长。他是一位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人,这一点能从他两条腿上的风湿病上看出来。他与部里一帮有权有势的人相识,靠着他们,他不但没有退休,还在各大军事机构里的参谋部调来调去,得到各种暂时补贴,还提高了薪俸,在他的风湿病未使他失去理智之前,他一直呆在他的职位上,后来,他又有一次调动,理所当然又升了官。他和军官们一起吃饭时,从不谈别的,只谈他肿胀的脚趾头,在肿裂很大时他只好穿上一双特制的皮靴。
吃饭时,他总乐于向别人讲述他的脚趾头如何出汗和流脓,流出来的东西就像变酸的肉汤,所以只得用棉花裹着。
每当他调任别处时,军官们总怀着极大的诚意跟他道别。因为总的来说,他挺和气,对下级也友善。据他说,在没得病以前,他总是能吃能喝的。
根据值日官的指示,他们将帅克和有关文件一起送交赫尔比希上校,当时杜布中尉正坐在上校的办公室里。
杜布中尉在从萨维客开往桑博尔途中又经历了一场冒险。在费尔施泰因,十一先遣连遇上了一个到萨多瓦?维什尼亚的回去的骑兵马队。
不知道怎么回事,杜布中尉竟提出在卢什卡上尉前展现一下自己的骑马技术。他跳上一匹马,那马就带他消失在山谷小溪中,在那儿他牢牢地扎在一个小沼泽里。恐怕连最能干的园丁也不能扎得像他那么笔直。人们用绳索套着他往外拉,杜布中尉没有怨言,只有呻吟得像一头行将断气的牲口。他被带到旅部,安放在小型战地医务室里。
几天后他清醒了,告诉医生再给他背上和肚子上抹两三次碘酒,然后他就大胆地赶队伍去了。
如今他坐在赫尔比希上校这里,讲述各种疾病。
他听说了帅克在费尔施泰因附近的神秘失踪,因此一见到帅克,他便大声喊到:
“又找到你啦!许多人像幽灵一样在外面游荡,又像野兽一样回来,你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必须再补充一下:在骑马冒险行动中,杜布中尉得了轻微脑震荡,因此当他走得那么靠近帅克还大声对他喊时,请不要大惊小怪。
“啊,天父,我召唤你,大炮的烟雾遮住了我,枪声可怕地穿过。战争的总管啊,我呼唤你。请你送我到那流氓那儿……你在哪儿呆了那么久,王八蛋?你穿的是谁的军服?”
值得补充,患风湿病的上校不发病时,他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讲民主,并教军官轮着去听他对流脓脚趾头的论述。
他没发病时,各式各样的军官挤满他的办公室。这时他非常快活,而且健谈,喜欢有人围着他,听他讲龋龊的笑话。他讲得津津有味,别人只能勉强笑笑,这些老掉牙的笑话在劳登将军时期就有了。
这时候,为他服务很轻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各种盗窃和胡闹事件都伴随着赫尔比希的出现而增加。
今天也是这样。各级军官和帅克一起挤了进去,看上校怎么发落他。这时上校正看着少校由普舍米斯尔写来的公文。
杜布中尉还在与帅克继续着可爱的谈话:“你现还不认识我,哪天你认识我了,你就得吓死!”
上校看了少校的呈文,乱七八糟,显然他写呈文那时,正在喝酒。
但上校兴致很高,因为昨天和今天他的腿都像安静的羔羊,没有疼。
“你到底干了什么?”他的口气如此和缓,使杜布中尉的心像被扎了一下,他说:
“这个兵,上校先生,”他介绍说,“他装疯卖傻以图掩盖罪行。我能想象他准是又干了什么坏事。上校,您要允许我看一下来函,我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个处置方法。”
他转向帅克,用捷克语吼道:“你感觉到了吧,你在喝我的血!”
“在喝!”帅克一本正经地答道。
“您看,上校先生,”杜布中尉用德语说,“您什么也不能从他口里问出来,您没法跟他说话,请允许我,上校先生……”
杜布中尉仔细读着来函,兴高采烈地大叫道:“你完啦,你把军服丢到哪儿去啦?”
“当时我想试试这套破玩意儿,看俄国人是怎么穿的,我自己那套脱在了池塘边,’帅克答道,“这只是个误会。”
帅克开始述说由于这场误会他所吃的一切苦头。等他说完,杜布中尉嚷道:
“你今天才认识我,你知道失去国家财产意味着什么吗?你这笨蛋!”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答道,“我知道,丢了军服的士兵应领一套新的。”
“天哪,”杜布中尉惊叫道,“你这阉牛!你这畜生,你再敢拿我开心,打完仗后你还得再服役一百年!”
一直安安稳稳,惬意地坐在桌旁的赫尔比希上校的脸突然可怕地皱成一团。他安静的脚趾头,由于猝发的痛风,变成了咆哮的老虎,他的四肢就像通过六百伏的电流一样感觉慢慢被击碎。上校擦了一下手,用一个被慢慢炙烤着的人可怕的声音喊到:“都出去,给我去取左轮枪!”
大家都明白,连帅克一起都到了走廊上。杜布中尉留下了,他想趁此良机,给帅克来个落井下石。他对脸部肌肉扭曲得很难看的上校说:“请允许我提醒您,上校先生,那家伙……”
上校嗷嗷直叫,向杜布中尉扔了个墨水瓶,他吓破了胆,行了个军礼便消失在门外。
从上校办公室传出的怒吼和哀号持续了好长时间,最后,呻吟止住了,老虎又变成了羔羊,上校按了一下枪,叫人把帅克再带上来盘问。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上校问帅克,带着疼痛消失后无比的舒适,仿佛此刻正躺在海滩上。
帅克友好地笑了笑,又讲了一遍自己的历险,并说明身为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他的缺席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不便。
上校也笑了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办一个由利沃夫去佐尔坦采站的通行证,从仓库里给他取套新军服,再给他六克朗八十二个哈莱什的伙食费。”
杜布中尉呆呆地看着帅克穿上新军服去火车站,当帅克按军纪向他报告并出示证件时,他惊讶万分。
杜布中尉别无表示,只说了一个字:“Abtretan!”他暗自嘟囔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认识我的……”
在佐尔坦采火车站,扎格纳大尉集合全营,只缺在迁回利沃夫时失踪的后卫。
帅克刚进城时,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因为前线已近在咫尺,所以到处一片繁荣景象。士兵们进进出出,到处是炮兵队和运输车队。在他们中间,士兵中的精华——日耳曼人——高人一等般散发香烟给奥地利人,他们甚至大桶酒喝,士兵们打了啤酒去就中饭和晚饭喝。奥地利人无人过问,馋虫般围着啤酒桶,肚子里却装满了肮脏的甜菊花茶,身着士耳其长袍的聚成一堆,指点着西方的乌云,到处都在嚷着,到处都烧起了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