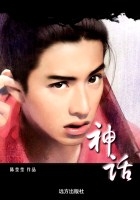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进行 (6)
当他坐着小汽车来到阵地时,他才清楚,原来,军部是派他来当将军的。
只见一架敌机在公路旁燃烧,远处有一支队伍朝前方挺进;村庄在大火中毁灭。比勒的司机朝敌方开去。
比勒使劲儿对着司机大叫:“你知道前面是谁吗?前面是强大的敌人。”
司机不紧不慢地说:“将军先生,趁着这最后一条道路没有被破坏,让咱们多跑点儿路,免得什么路都不能走时,只能让你休息,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火势仍是那么旺,炮弹飞来飞去。
司机非常镇静地对将军说:“太棒了,将军先生,在没上战场之前我都没有像轮子抹了油一样的路上溜过哩。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轮胎肯定会放炮。回不去了,将军先生。”
“嚓!”司机一声紧急刹车,车子猛地跳了一下。
“将军先生,现在你该相信这条路实在是太棒了,刚刚在咱们面前有一颗二十八毫米口径的德制炮弹炸开了,可是车连一丝划痕都没有,要是换条土路,这车肯定报废了。此刻离我们不远的敌人正举起机枪朝这方向扫射呢。”
“我们能开到什么地方?”
“走到路的尽头,肯定会有一个地方。”司机回答说,“只要公路总是像现在这样这么好走,一切我来负责。”
稍微停了几分钟之后,那车又继续前进了。那车简直超过脱缰的野马跑的速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将军先生,快查看一下作战地图。”司机大嚷,“前面有个十字路口,任何一条路都是去敌方阵地,我只想要一条好跑车的路,免得对轮胎损伤太大……将军先生……这样的话咱回去好有个交代是吧。”
比勒打开灯,铺到膝盖上一张一八六四年普奥联军与丹麦争夺石勒苏益格时期黑尔戈兰湾的海域图。
忽然轰地一声巨响,车子腾空而起,车尾已不见了。
“幸亏现在我要你指出路线给我看,”司机说,“否则你早就在车尾不见了。那准是四十二毫米口径的大炮干的。”
“车开到哪儿去?”
“上天去,将军先生,咱们避开这扫帚星,咱们可不能和它碰头啊,它可是厉害着呢。”
“你了解来比锡各民族大战吗?”比勒问道,“那场战役在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四月爆发,一八一三年的十月十九日来比锡陷落了……”
“将军先生,现在要下车走了,这儿是天国大门,车挤不过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都在天堂门口。”
“都是些什么人?要不就轧掉几个,他们就会让路的。”他边对司机嚷嚷,边伸出头来,“猪猡们,快滚开,这些混帐看见将军来了,也不敬礼!”用力睁开眼,比勒这才发现在天国大门口挤来挤去的是因在战争中而丢掉某一身体部位的人,他们都背着从身上掉下的那部分,把它们放在背袋里,像脑啦,头啦,脚啦,也有股屁,眼睛等等。“他们可真比在战场上还有秩序,显然为了顺利通过天国的检阅吧!但我们还要开过来的啊,即使他们脑袋有毛病不知道让路。”
“伟大的皇上和上帝。”比勒将突然记起这句口令,他们才把汽车从天堂门口开了进来。
在经过天堂新兵大本营时,一位长着红眼睛、大翅膀的天使军官告诉比勒将军说,他们必须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将军报到。“简直废话,在天国里,肯定我比他大那么一点儿了,我需要去向他报到吗?”
他们驶过了天使新兵的军训营地,来到了一座大楼底下,楼顶挂的横幅上面写着巨大的标语:“皇家王室上帝大本营”。
在比勒和司机毫无准备下,被一位穿着制服的宪兵一手一个抓下了车,提着他俩的衣服领子,用力一扔,就来到二层楼的走廊门口。
“在上帝面前也这么粗鲁。”他们俩咕哝着,被拉到里面去了。
房间里一幅幅肖像映入眼里,有弗兰西斯丹克尔将军,约瑟夫和德国皇帝威廉,冯?霍森多夫总司令,房子中央是上帝。
“士官生比勒,”上帝声音低沉地问,“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扎格纳大尉,以前你是我的手下。”
比勒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慌。
“士官生比勒,”上帝又严厉地说,“你是不是头脑发胀了,你凭什么自封为将军,你凭什么坐着小汽车穿梭在陆军阵地之间?”
“报告……我……”
“闭嘴,士官生比勒,你现在正在受上帝对你的审查。”
“报告!”比勒又口齿不怎么清地叫了一声。
“怎么你竟敢如此放肆,”上帝大怒,“来人啊,给我把这混蛋拉下去,扔到粪坑里去。”
带着翅膀,翅膀下面夹着冲锋枪的天使一把抓住比勒就往粪坑里扔。
比勒一看就认出了他俩分别是马杜西奇和巴柴尔,只不过现在被臭气包围着,不能和他俩打招呼。
马杜西奇和扎格纳大尉的勤务兵巴柴尔一直迷恋着他们的扑克,对面像猪一样睡着的是比勒。
“怎么会这么臭,那小子肯定是拉了一裤裆屎。”巴柴尔脱口而出。
“这是很正常的的现象,”马杜西奇用哲学家的口吻说,“没关系,打咱们的牌,反正又不是你。”
朝霞在布达佩斯上空,多瑙河上许多探照灯在探寻。
士官生比勒又在做另一个梦了:“它像一些不朽的丰碑在我的心灵树了起来,我们勇敢的部队!”他边说着梦话边又翻身。巴柴尔吐了大大一口唾沫,他已经受不了这一股强烈的臭气了。士官生比勒更不安宁地来回折腾。离奇的梦,正在他脑中继续:他在奥地利境内的防守林里,周围是严密的要塞碉堡、护城屏障和防御工事。在他所在的指挥部成了一所大医院,伤兵遍地可见,他们都一个个捧着肚子,一位传令兵穿过防守林站在人群之最高点,也捧着肚子,对法军大喊:“我们绝不会轻易投降,请转告贵国皇上。……”
一会儿肚子就不疼了。他带着一批人马,最早突出重围,胜利而回。卢卡什上尉挺胸替比勒挡了法国兵一刀。
卢卡什上尉流血不止地躺在地上抱住他的脚说:“上校先生,军队正缺少像您这样的男子汉,您是不能牺牲的啊!我没关系,我是一个普通的上尉,一个废物”。
突然屁股被沙弹打了一下,比勒习惯性地摸了摸裤裆,湿乎乎的。“请叫救护车,请叫救护车!”比勒大叫,接着便摔了下来。……
打牌正热的巴柴尔和马杜西奇用奇怪地眼神望着摔到地板上的比勒,其中马杜西奇赶紧去报告扎格纳大尉这一怪事。
“肯定不是酒喝多的原因,”他说,“绝对是得了霍乱病”。
“马杜西奇,去把十九车厢的大夫叫来,让他给士官生比勒检查检查。”
于是马杜西奇便叫来了老医科大学学生费尔费。他医术不错,是奥匈帝国颇为有名的一位军医,不过习惯了,喝酒,打架样样都会,虽然他上了许多医科学院,但却没拿到博士学位,这其中有很大的一个秘密:他叔叔死亡前曾答应过给费尔费每年的学医助学金,一直帮助他获得博士证书为止,那份助学金不少,大约可以抵上一个医院医生的工资的五倍,这就是费尔费不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的原因了。
这样的举动也惹火了其他的继承者,他们告诫他赶快娶个有钱的女人,或者赶快拿到证书,还大骂他是白痴,如果可行的话,他们恨不得杀了他。但他还是继续念他的书,没有丝毫想拿学位的念头。他还在和他的同学组成的文学社里当主编,并不断有诗歌出版。
但是战争一爆发,等于给了他摧毁性的打击,文学社散了,其中许多学员被抓去当兵了,他也被在军政部的一位遗产继承人巧妙地安排了笔试考试,并且通过了医学博士学位考试,虽然在大量的题目后面他只写上些离题十万八千里的字,什么亲爱的我想死你啦,请和我的脚接吻啦,等等之类,非常不幸的他在三天之后被告之他通过了考试,并且在附属医院上班,军医主任告诉他说他提升的机会很大。
他咬咬牙,就去当了一名军医。而且表现非常不错,他会尽最大力量帮助病人多呆在医院里,而且对待伤病员也特别友好。在赶上上前线高潮时,费尔费大夫被派到了十一先遣连,去前线作贡献了。
当然他是不合群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正式军官,不愿理他,生怕自己和他交往得多了就会脱离正式军官群的范围,即使是后备军官也那样。
扎格纳大尉在这位不知道留了多少级的医学博士面前自然是更加自信了。他瞧不起费尔费医学博士,虽然是他派人去叫他的,他继续着和卢卡什上尉的谈话,什么最近某处产了一个南瓜竟有十八公斤之重等一些毫无意思的事。卢卡什上尉也告诉他,他曾经跟几位家庭背景很差的学生去斯洛伐克,一位教堂牧师给他们做了南瓜配成的肉,又给他们斟了葡萄酒,还口口声声地说:“猪肉配南瓜,再加美酒一杯。”卢卡什上尉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布达佩斯,没有一处让我迷恋,”扎格纳大尉说,“幸亏咱们的列车只停一个半小时。”
“列车正在减速,估计快到军用车站了。”卢卡什上尉说。
医学博士从他俩身旁经过,翻了一下士官生比勒的眼珠。
“‘尊敬’的大夫,请问士官生比勒是什么病?”扎格纳大尉问道。
医学博士费尔费冷笑一声说道:“候补军官、贵营的士官生拉了一裤裆。这没关系,只不过是一般的下泄。贵营的士官生先生太贪喝酒了,酒喝多了就会拉肚子,更何况他吃他妈从家里给他寄的奶油蛋卷儿吃得太多了,真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据我所知,以前他在俱乐部喝得还挺少的,他是个禁酒主义的代表呢。”
费尔费吐了一口唾沫,翻了一下他的嘴唇,“他总是喜欢吃路边小推车上的东西。”
“那不会出人命吧?”扎格纳大尉问费尔费道,“可是出了这样的事总是不太……万一消息传出去……”
卢卡什上尉说:“我实在是佩服有这样的后备军官。”
“让我治治他的病,”费尔费说,“不过得请示营长,士官生比勒需隔离,我们要把他送到地方军医院,他得的是一种传染病,一种痢疾……”
“这是现在解决他的最好办法,”费尔费神秘地笑了笑,“称他为拉一裤子士官生或者痢疾士官生都成。”
扎格纳大尉似乎觉得费尔费正在克制住想要狂笑的欲望,而且是那么的无所谓的态度。一丝惊奇,被很快掠过。
“现在一切办妥了,大尉先生。”费尔费平静地说,“贵营的士官生的裤子在送到新军人传染病医院之前最好扔掉,再换件新的。”
就这样勇敢的士官生比勒在传染病院的一间房间里做着他那伟大胜利的梦想了。
士官生比勒在得知自己得了痢疾时差点儿高兴得手舞足蹈,负伤或生病都一样是为了效忠皇上的出色表现,毫无区别。
士官生比勒虽说患了痢疾病,不过痢疾病患者的病房早已人满为患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医生便把他扔到了霍乱病房里。
士官生比勒在洗完澡之后在他的腋下被放了一支体温表,体温表上显示37°。
“不好!”匈牙利军医叫了一声,“霍乱病最恐惧的是体温的下降,而且现在病人表情僵硬。”
超乎异常的平静的士官生比勒口口声声唠叨着:“反正都一样,都是为皇上效忠。”
比勒的肛门里也塞了一支体温表。
“霍乱相当严重了。”军医作了最后诊断,“身体非常虚弱,头脑不清,在死神的痉挛中微笑。”
这时的比勒在任人摆布之下,一点儿也不反抗,俨然像位英雄,一动不动,脸上挂着笑意。
“不好,霍乱病患者临死之前征兆已经出现,还要检查一下在他的澡盆里是否还有腹泄。”“没有。”卫生兵回答道。
“那更不好,霍乱病在临死之前会停止上吐下泄的病症。”
洗了澡之后的士官生比勒感到冷坏了,四肢无力下垂而且皮肤冰冻牙齿打颤。
“患了霍乱病而嘴唇、指甲没有发黑就死去了的病人,我已经治过三个了。”
“明天就可以和那位少校一起埋了,现在赶快准备死亡证。”
“被……被……被子,给我……给我一床被子……我实在是冷得不行了。”士官生比勒朝着远去的背影大声叫着,很可惜没被听见。
和他同病房里还有更坏的病人,其中有一个是在二十分钟之前断气的。那军医准备让士官生比勒和这位少校死者埋在一起。
士官生比勒终于看到了为了效忠皇上,而得霍乱死的人们,也亲眼目睹了其中两个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语无伦次,那扭动的身体因为难受而憋得慌。
比勒望了望四周,又死了两个,一张床单便把那个全身发紫,舌头外吐,手握得紧紧的死者卷了起来。
光着身子的士官生比勒拍了一下那位老护士的肩膀央求道:“给我一条被子……我冷得不行了。”
不到一刻钟军医又回来了,宣布士官生比勒去塔尔诺夫霍乱病院进行观察。
一个精力充沛的士官生比勒就又一次被送进了那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