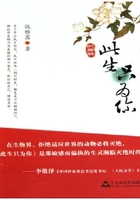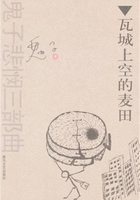第十一章 帅克和随军神父去做战地弥撒 (2)
“您应该明白,您这是在滥用军事物资,”他的话被帅克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哪里有这样的上帝恩赐?!真是只有天才知道!有个叫比沃卡的,住在霍捷博尔,有一次迷迷糊糊地把别人的一头牛连同套子一起牵回来,也说是上帝的恩赐。”
被这些话吓呆了的可怜的老头儿,不敢再为自己申辩什么,只想着赶快穿好衣服了结这件事。
还在睡觉的沃尔舍维采的教区神父被人叫醒之后就骂起人来。他在朦胧的睡意中还以为有人叫他去为哪个能者行祝圣礼。
“即使是举行终傅礼(由神父在天主教徒归天之后傅‘圣油’并为其祈祷,以此来赦免一生的罪过),也得让人安宁一会儿嘛,”他念叨着,一边穿衣服一边发牢骚,“这些人在人家睡得正香的时候又想起去死了!最后,人家还得为那几个手续费而讨价还价。”
他们在前厅就这样相见了。上帝在沃尔舍维采居民和天主教徒中间的代表站在在一边,上帝在人世间的军事机关里的代表站另一边。
总之一句话,这场纠纷发生在军民双方之间。教区神父固执得认为战地经台不该藏在沙发里,而随军神父就这一点而指出,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把它从沙发里取出来送到普通老百姓才去的教堂的圣器室里。
帅克在一旁也说,靠沾军事机关的光让一个穷教堂发财是很容易的,当然,他所说的穷是打了引号的。
最终,他们一起走进了教堂圣器室,在那里,教区神父取出了战地经台和一张收条,上面写着:
今收到战地经台一件,它偶然流失到沃尔舍维采教堂。
随军神父 奥托?卡茨
这个大名鼎鼎的战地经台是由维也纳一家犹太人莫里兹?马勒尔开的公司生产的。各种弥撒和宗教仪式用品,诸如念球珠、圣珠之类,大多是由这家公司专门生产的。由三面折叠而成,上面镀有一层厚厚的假金的战地经台,同所有圣殿一般耀眼夺目。
那三块画板上画的东西的内涵是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所难以辨认的。它的确是个经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个经台似乎连住在赞比西的多神教徒、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族和蒙古族的巫师都可以使用。
经台的颜色就如同用来检验铁路员工是否色盲的彩色板一般耀眼夺目。
突出的只有一个人物。那是个头上顶着灵光的、一丝不挂的赤裸男人,他全身好像一只已经腐烂发臭的鹅屁股那样泛着青。
尽管没有人对这位圣徒有什么行动,但立在他两侧的长着翅膀、代表天使的形象却让人联想到周围的环境把这位裸体圣徒吓得哇哇乱叫。因为画得像是童话中的妖怪的那对天使,是某种介于带翅膀的野猫和《启示录》里的怪物之间的一种东西。
一个体现三位一体形象的图画画在经台的另一面。总体来看,画家的手艺还算不错,他把那只鸽子画成了一只和美国种大白鸡一样的鸽子。
可是天父,却被画成了一部惊险血腥影片中观众所看到的西部荒原上的强盗。
上帝之子却与此相反,被画成了一个快活的青年男子,游泳裤似的东西穿在小肚子上,他手拿十字架,像握着网球拍,那挥洒自如的样子很像一名运动员。
一切从远看都融合成为一体,就像是一列火车刚开进站。
第三幅像所表现的意义简直令人难以捉摸。
在做弥撒时,士兵们总是闹着要猜这张画谜。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幅萨扎折瓦河畔的风景画,但是“圣母玛利亚,耶酥之母,请宽恕我们吧”这样一行字却写在这幅圣像画的下面。
顺利地的把战地经台放进马车的帅克,坐到了马车夫旁边,舒舒服服坐在车厢里的是神父,他正把两条腿搭在象征着三位一体的经台上。
马车夫和帅克聊起了打仗的事儿。
马车夫看起来像是个不轨分子,因为就奥地利军队战无不胜的问题他发表了种种言论,例如“在塞尔维亚方面有所推进”等等。哨兵在马车驶过粮食税务站时问里面装的是什么。
帅克立刻回答说:“噢,哨兵先生,是一架三位一体的战地经台,圣母玛利亚和随军神父。”
各连的新兵到这时候都已经在演习场上等着急了。因为神父和帅克为了借运动奖杯而到魏廷格上尉那里去了一趟,然后又为了借圣体盒、圣饼盒和其它弥撒用品,包括一瓶进圣餐用的酒,去了一趟普谢夫诺夫修道院。由此可见,做一台战地弥撒可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干这号子事我们都是瞎凑合。”帅克对马车夫说。
这话一点儿都没错。直到他们走近演习场那座安有木板和摆战地经台的桌子边时,他们才发现神父忘记找辅祭了。
这个角色过去总是由一名固定的步兵来担任,但现在,那个步兵宁愿上前线去当个通讯兵,也不愿留在这里。
“没关系,没关系,”帅克说,“我能干这活儿。”
“你能行吗?”
“这种事儿我可从来也没干过,”帅克老实地说,“但什么事都得有个第一次。现在是在打仗,人人在战争中都干着自己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您讲完‘上帝赐福给你们’这句经文后,我不过是再加上一句‘与你的灵魂同在’不就行了嘛!我想这没什么难的,绕着您走一圈,给您洗手,再把酒从杯里倒出来……这和一只猫围着一碗烫稀饭绕圈一样简单。”
“那好吧,”神父说,“你最好是在我的第二只杯子里斟上酒,但别替我斟水。你该走在左边还是右边,我会随时告诉你。如果该走右边,我就轻轻地打一声口哨,如果是左边,我就打两声。你也不用为祷文发愁。除此以外,一切都跟儿戏一样,你不紧张吧?”
“这有什么可害怕,神父先生?就连当辅祭也没啥大不了的。”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神父的布道很简单:
“士兵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在上战场之前让我们的心能转向上帝,他会赐予我们胜利,保佑我们平安。不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祝你们平安!”
“稍息!”站在左边的老上校下命令道。
之所以把战地弥撒称为“战地的”,就是因为同战场上的军事战术一样它也要服从于团体的法规。战地弥撒在这三十年战争这漫长的军事行动中,也往往被拖长很多。
军队的行动在现代战术中已变得迅速敏捷,因此战地弥撒也要相应地变得短小精悍。
十分钟就做完了这场弥撒。靠近经台的士兵对神父在做弥撒时还吹口哨深感奇怪。
机灵的帅克掌握了暗号,他嘴里只念着‘与你的灵魂同在’,一会儿走到祭台的左边,一会儿又回到右边。
整个过程看起来像一个印第安人围着祭祀的石头在跳舞。但整体给人以良好印象的仪式把在尘土飞扬的演习场上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一条李子树林荫道和一排军用临时厕所在演习场的后面。那里散发出来的臭气完全把哥特式教堂里的神话般的醇香给代替了。
大家都开心得很,围着上校的军官正讲着笑话。一切运转正常,不时地能在士兵的队伍中听到“给我吸一口吧”的细语声。经台上空所形成的烟雾,正是一缕缕烟草熏出的蓝云,从各个连队直上青天。最后,上校点着了烟卷儿,军官们也跟着抽了起来。
最后神父说了一声:“跪下祈祷。”顿时尘土飞扬,穿灰色军服的士兵组成云阵跪在魏廷格上尉的银杯面前,那是他代表“体育爱好者”俱乐部在维也纳——穆德灵的马拉松长跑中获得的。
神父摆弄着盛满了酒的银杯的结果,用士兵中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被他一饮而尽了。”
又重复了一遍这种表演,随着第二声“跪下祈祷”,管弦乐队奏起了《天主保佑我们》,士兵们整队离开了。
“拾掇一下那些玩意儿,”神父指着经台上的东西对帅克说,“这样咱们好把它们还回去。”
他们坐同一辆马车走了。东西都完好无缺地还给原主了,当然那瓶弥撒酒除外。
他们在到家之后,就立即打发那个倒霉的马车夫到司令部去领这趟长途赶车的车钱。帅克问神父:“报告神父,主人和辅祭应该是同一教派的吧?”
“那是自然的事,”神父说,“要不弥撒就没用了。”
“那么,神父先生,我们刚才就犯了个大错。”帅克说,“我正为我不属于任何教派而发愁呢!”
神父看看帅克,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把瓶子里剩下的那点儿圣酒喝掉,就算是你也入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