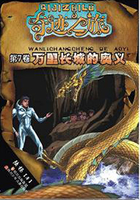第十章 帅克成为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员 (4)
这会儿无论是谁,如果听到了心情抑郁、无精打采的神父的那番言论,都会以为他常去听亚历山大?巴切克博士的演说,仿佛是听他宣称“我们将向酒魔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我们的男儿正是被这魔鬼残杀的”,又仿佛在读他写的《道德散论》。
他的确是有所改变。他说,“如果他喝的不是松子酒,像阿拉伯甜酒,南斯拉夫樱桃酒,白兰地酒那样的高贵饮料就好了。我怎么可能喝得那样津津有味,这可真是让人想不通。其实味道糟糕得很!如果是黑樱桃酒,也要好一些。各种各样的鬼东西人们都把它想出来,然后像喝水一样地来喝它们。这种味道不好,颜色也不好看的松子酒喝了就只会辣嗓子。如果有一点儿纯正的杜松酒也行,就跟上次我在摩拉维亚喝的那种一样。可这次喝的却是用一种木酒精和油熬出来的松子酒。你看,我总是打嗝!俄国白酒就是毒药,”他肯定地说,“只有是真正的原装货,而不是犹太人从什么厂子里用冷却法生产出来的才好喝。纯正的俄国白酒应该跟罗姆酒一样,但是好的罗姆酒也是很少见的。”
“如果真有点儿纯正的胡桃酒就好了,”他叹着气又说,“这会有利于我的胃。这种酒可以在普鲁斯采的施纳布尔大尉那儿找到。”
他开始摸口袋找钱包了。
“我现在只有三十六个克里泽了。卖掉这个沙发好不好?”他想了一下,“你看呢?有人会买吗?对房东我可以骗他说借给别人或者是被人偷走了。不,还是留着沙发吧。你到施纳布尔大尉那里去,叫他借给我一百克朗。前天他玩牌刚赢了钱。如果在那儿你借不着钱,就去沃尔舍维采兵营去找马勒尔上尉;如果那儿也不行,你就到赫拉昌尼找菲舍尔大尉。你就说马料钱让我给喝掉了,让他付给我马料钱。如果连那儿也借不来钱,咱们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把钢琴卖掉。每到一处你都带上我给你写的字条,以免他们随随便便就打发了你。你就对他们说,我现在缺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管你编个什么理由我都不管,只要你别空着手回来就行,否则就等着我送你上前线吧。记着在施纳布尔大尉那儿问一下他的胡桃酒打哪儿买到的,给我买两瓶带回来。”
因为帅克单纯诚挚的外表和老实憨厚的言语使得他去找的那几个人完全相信了他说的话,所以他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为觉得对施纳布尔大尉、菲舍尔大尉和马勒尔上尉说神父没有付马料的钱不太可信,所以他就用神父付不出私生子的津贴来作为借钱的理由,很容易地就弄到了钱。就这样,从每个人那里他都得到了一笔钱。
当帅克拿着借来的三百克朗胜利而归时,已经洗完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的神父大大地吃了一惊。
“只要我一出马,什么事都给你办好了,”帅克说,“这样明天和后天咱们就不用为钱耽心了。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是我得在施纳布尔那儿下跪,那可真是个吝啬的家伙,不过,当他听到我说起私生子津贴的话……”
“私生子津贴?”神父被吓了一跳,又重复了一句。
“是啊!神父先生,所谓的私生子津贴就是付给娘儿们的。不是您说的嘛,随便我怎么编都行的吗?别的理由我当时也想不出来了。因为有个一次要给五个娘儿们付私生子津贴费的鞋匠在我们那儿,弄得很狼狈。谁都知道他手头拮据,因为他总是得靠借钱来打发日子。他们还问起那娘儿们的长相,我说很漂亮也很年轻,还不到二十五岁,他们还要她的地址来看。”
“帅克,瞧你干的好事!”神父边叹气边在房里来回地踱着步。
“多丢人啊。”神父边说边抓脑袋,“我的头都给痛死了!”
“我给他们的是咱们街上一个聋老太婆的地址,”帅克解释说,“因为命令就是命令,所以我必须把事情给弄妥当。既然我必须要从他们那儿借来钱,那我就必须得想一个好法子。现在有人在外边门厅里等着搬那架钢琴,是我叫他们来把它抬到当铺里去的,神父先生。搬走这架钢琴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一来,咱们的屋里可以更宽敞一些,也能多弄到些钱,至少有好几天咱们可以过不愁钱的清静日子了。如果房东问起为什么要搬钢琴,咱们就说因为弄断了几根钢丝弦,所以现在送到乐器修配房去修理。我已经给门房老太太打过招呼了,以免她见到被搬上卡车的钢琴就大惊小怪的。我还找到了沙发的买主,是我认识的一个旧家具商。他下午才来,现在皮沙发的价格还可以。”
“别的你还干了点儿什么,帅克?”神父用一只手撑着脑袋,很沮丧地问。
“报告,神父先生,我不只买了两瓶,我总共买了五瓶您所说的施纳布尔上尉那儿的那种胡桃酒,好让咱们家里有存货可以喝。让他们在当铺关门之前把钢琴抬走吧!”
神父很无奈地搓了搓手。过了一会儿,钢琴就被搬到货车上运走了。
当帅克从当铺回来的时候,神父正坐在一只已经打开了塞子的胡桃酒瓶前面,生气中午吃的煎肉排没有炸透。
神父醉醺醺地对帅克说,他从明天起就要过新的生活了,因为只有粗俗的唯物主义才喝酒精制品,所以必须过一种精神生活。
在他打开第三个瓶塞之前,他发表的哲学宏论足足有半个钟头长,然后家具商就来了。他以最低的价钱买走了沙发。神父想跟家具商聊聊天,可是那人因为还要忙着去买一只床头柜,因此使神父大为不满。
“真可惜我没有这东西,”神父遗憾地说,“不过一个人也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啊。”
神父和帅克在送走旧家具商之后又作了一次友好的消遣,他们在一块儿喝掉了一整瓶酒。神父又对女人和扑克这部分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在一块儿一直坐到黄昏,两人之间仍然进行着友好的谈话。
但是关系在晚上的时候转变了。恢复到昨天那个神气的神父又完全不认识帅克了,并且对他说:“你可绝不能走,辎重队那个棕色头发的见习军官你还记得吗?”
直到帅克对神父说:“够了!你现在给我爬到床上睡觉去吧!听清楚了吗?”这支田园诗式的插曲才结束。
“好,好,亲爱的,我现在就上床,为什么我不爬到床上去呢?”神父念叨着,“我们一同呆在五班,你的希腊文的练习还是我替你做的呢!你在兹布拉斯拉夫有一座可以坐着汽艇游伏尔塔瓦河的别墅,你知道伏尔塔瓦河是什么吧?这一切,你还记得吗?”
神父一边照帅克的指令脱衣脱鞋,一边茫然地对这个陌生人抗议说:
“各位,你们快看呀,”他对着柜子和一盆无花果树说,“这些亲戚对我是多么的严厉啊!”
“这些亲戚我都不要认了!”神父在上床的时候用坚定的口吻说,“即使是天地都不容我,我也不要认他们……”
接着,神父的鼾声就在房间里响起。
四
帅克这几天抽空去看望他的老佣人米勒太太,没想到见到的却是米勒太太的表妹。她向帅克哭诉说,就在他坐轮椅去从军的那一天米勒太太也被逮捕了。老太太不仅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还被他们带走了。就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证据,所以米勒太太被送到斯特因霍夫集中营去了。她寄来一张明信片,拿起这份珍藏品,帅克读道:
亲爱的安宁卡:在这儿我们很愉快,身体也无还好。我邻床的女人患水×,还有人患天×。其它人都好。我们的食物够吃,只是要给些土豆×做汤喝。我听说帅克先生已经××了,劳烦你打听一下他的坟在哪,我们想在战争结束时给他上上坟,添添土。有一件事顺便告诉你,有一只匣子放在阁楼上的黑角里,一只 狗崽子装在里面。它自从我被×以后,也几个星期没有东西吃了。但我想,现在喂也来不及了,估计那只小狗也××了。(“×”是书信检查署删去的字)
信封上那粉红色的邮戳表明:此信件已经帝国及皇家斯特因霍夫集中营的检查。
“果然那只小狗早就死了,”米勒太太的表妹哭着说,“您曾经住过的这间屋子您恐怕也认不出来了。这儿现在布置得像个小客厅,是因为我找了一些女裁缝住在这里,她们在墙上贴满了时装图片,又在窗台上摆了许多鲜花。”
心情怎么样也无法平静下来的米勒太太的表妹长久地哭泣着、怒诉着,甚至还表示出对帅克的怀疑,担心他是从军队里逃出来的,现在又来连累她,给她带来不幸。到最后,她对帅克说话的口吻与对一个淫荡的冒险家说话的口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真是开心死了!”帅克说,“我最喜欢这样了。我可要让您知道,格依谢娃太太,您说对了,我就是逃出来的。我干掉了十五个警卫官和军士,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您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
当帅克离开他那所不愿意收留他的房子时对格依谢娃太太说:
“请您替我把我留在洗衣房的几条领子和背心取出来。这样我从部队里复员回来,才有件衣服穿。请您注意保管我的衣服,别让衣柜虫子蛀了我的衣服。另外,请代我向那些睡在我床上的小姐们问个好。”
后来,帅克还看了看“杯杯满”酒家。巴里淮茨太太以为他多半是开小差溜出来的,所以不肯给他倒酒喝。
“我丈夫,”她又开始聊起旧话,“是那么谨慎的一个人,可现在却无缘无故地被关进了牢房。而有些从军队里开了小差回来的人,却在这里逍遥快活。他们上星期还来搜捕过你呢!”
“我们比你小心得多,”她结束自己的话题,“可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交到您这样的好运啊!”
有一位年轻的斯密霍夫的钳工此时走到帅克面前,对他说:“先生,劳驾您在外面等我,我想和您说几句话。”
在街上,他和帅克交谈了一阵。他听到巴里维茨太太的话,也以为帅克是开小差从部队里跑回来的。
他对帅克讲,他有一个从部队上开小差回来的儿子,现在住在耶塞纳他奶奶那儿。
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帅克向他证明自己不是逃兵的话,更是往帅克手里塞了十个克朗。
“这是给你应急用的,”把帅克拉到酒店的角落里,他又说,“你用不着害怕我,我很理解你。”
直到深夜,帅克才回到神父那儿,可是神父还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回来的神父叫醒帅克说:“咱们明天要去给野战军做弥撒。你负责煮点儿黑咖啡再在里面加上罗姆酒。要不,加点儿格罗格(一种加糖和热水的烈性酒)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