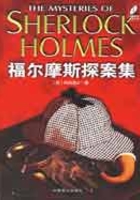第八章 成了装病逃役犯的帅克 (3)
礼物被男爵夫人从篮子里拿出来:用玫瑰色绢纸包着的十二只烤仔鸡,还有一根红黄丝带子扎在上面;贴有“愿上帝惩罚英国”标签的两瓶军用烈性甜酒,弗兰西斯?约瑟夫与威廉两人手拉着手,像小孩子准备做“小羊坐小洞”游戏那种架式的商标贴在瓶子的另一面。
然后从篮子里,她又取出两盒烟和三瓶滋补身体的葡萄酒。在帅克床边的空床上,摆满了男爵夫人带来的礼物。接着又添了一本由我国官方报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报》的功勋主编撰写的、书名为《吾王生活轶事》的装潢考究的书;从老弗兰西斯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床上后来又多了几包贴有“愿上帝惩罚英国”这种同样标签的巧克力糖,奥地利和德国皇帝两个人的画像同样是贴在另一面,只不过巧克力糖装纸是他们两人是背靠背地坐着,而不是手拉手了。男爵夫人还拿出一把很漂亮的印有“依靠共同的力量”题词的两行鬃毛的牙刷,这使得每一个使用这种牙刷的人都能想到奥地利。还有一套剪指甲的工具——一件在前线和战壕里都非常需要的精致礼物,盒面上画着爆炸的榴霰弹,戴着钢盔端着刺刀往前冲的士兵,下面写着“为上帝,皇上和祖国而战”。还有一包饼干,上面只有一首诗,却没贴画,捷克文的译文印在另一面:
奥地利啊,圣洁的大厦,
请把您的旗帜高高升起!
让它随风飘扬,
奥地利永远世不衰。
最后的礼物是那纯洁的水仙花。
男爵夫人在所有的礼物都被摆到床上之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有几个饥饿不堪的装病者已经在流口水了。男爵夫人的女伴流着眼泪扶着坐起来的帅克。就好像是在教堂里一般,病房里非常的寂静。帅克突然双手合十打破寂静说:
“上帝啊,您的名字将被奉为至圣,您的乐士将从天而降……夫人,对不起,这么说不对,我要说的是:‘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赐给我们这些礼物吧,因为您的慷慨,我们将尽情享用,阿门!’”
说完这几句话,他就从床上抓起一只烧鸡大吃起来,格林施泰因大夫惊讶地看着他。
“您看,这多么合帅克的口味呀!”老男爵夫人激动地对格林施泰因大夫说道,“我真是高兴,他已经康复,又可以再上战场了。这多么符合他的心意啊!”
随后,她又把香烟和夹心巧克力糖一张张床地挨个儿分发,转完一圈后重新回到帅克的床边,一边抚弄着他的头发,一边说着:“愿上帝保佑您。”然后便带着所有的随行人员出去了。
帅克趁格林施泰因大夫送男爵夫人下楼的时间把烧鸡分给了其他病友。等到格林施泰因大夫回来时他们早已狼吞虎咽地把烧鸡吃完了,只剩下了一堆鸡骨头。这些骨头被啃得极其干净,就像是刚出世的小鸡不幸落入了秃鹰的手中,而被啃光的骨头又好像已经被太阳曝晒了好几个月。
葡萄酒和军用甜酒也喝完了,一包包饼干和巧克力也被病号们吃完了;甚至连一小瓶指甲油也被一位老兄喝了下去。这瓶指甲油是和那套剪指甲的用具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把同刷子放在一起的牙刷也咬了一口。
回来的格林施泰因看到这一切,又摆出那副好斗的架势,发表了一篇演讲。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随着访问的结束落了地;而一堆堆啃得精光的骨头向他证明,这群装病逃避兵役犯是一群无药可救的家伙。
“士兵们,”演讲开始了,“如果你们还稍微有点儿头脑的话,那么就该让这些东西都好好地摆在那儿,并且对自己说:‘要是我们吃掉了所有的东西,主治大夫就不会相信我们身患重病了。’可是现在呢?证明你们根本不明白我的好意。虽然我给你们灌肠,洗胃,大力支持你们绝对禁食,但你们却在胃里塞满了东西。如果你们是想得肠炎,那么你们可是打错了算盘!我要在你们的胃还没来得及消化之前,就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叫你们一辈子都记得,甚至还会在将来给你们的孩子讲,曾经有一次你们是怎样吃掉烧鸡和其他别的好东西的,在你们的肚子里这些东西又是怎样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趁热被抽出来的。现在给我一个接一个地来!以便让你们都记得,我可不是一只与你们同样笨的笨牛,至少比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聪明一点儿。你们还要记住一点:我明天还要把征兵委员会的人请来。在这里,你们也呆得够久了,就你们刚才的行动来判断,既然在五分钟之内你们就能把胃弄得这么脏,那就足以证明你们都完全健康,现在,齐步走!”
轮到帅克时,因为想起今天这次神秘的探望,格林施泰因大夫瞅着他问道:“您认识男爵夫人吗?”
“她是我的后妈呀!”帅克毫无表情地回答,“很小的时候,她把我抛弃了,现在又重新找到了我……”
“待会儿再给帅克灌洗肠。”格林施泰因大夫简单地下着命令。
一片悲伤笼罩在夜间的病房里。大家肚子里几小时以前还装着的各式美味,现在就只有一杯淡茶和一片面包了。
窗口旁二十一号床位上的病友说:“嗨,伙伴们,我说炸鸡比烧鸡味道要更好一些,你们信不信?”
有人嘀咕了一句:“整整他这个不自在的!”
可是在经历了这次失败的聚餐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虚弱,谁也没力气动弹了。
格林施泰因的话在上午兑现了,几位军医从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来到这儿。
他们板着脸走过每一张床铺,机械地说着相同的话:“把舌头伸出来!”
帅克把舌头伸得老长,把眼睛也眯成一条细缝,表现出一副滑稽相。
“报告长官,我的舌头全都伸出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在帅克和委员们之间展开。帅克解释说,之所以他要加上那最后一句话,就是怕他们怀疑他把舌头藏起来了。
对于帅克,委员们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
有一半人认为帅克是一个白痴,但另一半人却认为帅克只是一个故意拿军事工作者开玩笑的坏蛋。
“要是我们斗不过你,那除非是遇到鬼了。”主任委员对着帅克吼道。
帅克则用那种儿童般天真的纯洁无邪的眼神望着所有的委员。
军区的参谋长走到帅克跟前说:“我倒是很想知道,你这个猪头,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鬼主意!”
“报告长官,什么我也没想。”
“混蛋,”委员的腰刀碰得铿锵一响,大声吼道,“他原来什么都没有想!你这个大笨蛋,为什么啥都不想?”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什么都不想,是因为军队禁止士兵想问题。想当年,我在九十一团服役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尉总是告诫我们说:‘当兵的自己不许想什么,因为长官们都为你们想好了。一旦当兵的用起脑子来,那他就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满身尘土的臭老百姓了。思想绝不能……’”
“住嘴!”帅克的话被主任委员恶狠狠地打断了,“关于您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您这臭小子别以为我们真相信您是个白痴……什么白痴,您根本就鬼得很,尖得很,帅克,您根本不是什么白痴,您是个流氓、地痞、无赖,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您了,叫您住嘴!听见了吗?”
“是,听见了,叫我住嘴。”
“我的天啊,叫您住嘴您就住嘴!您该明白,我是在给您训话,不许您插嘴!”
“是的,我懂得,不许我插嘴!”
军官老爷们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他们喊来了一个军士,指着帅克对军士说:“带这个家伙到楼下办公室去,等着我们发落。他在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一定不会再这么多话。这个装病的小子,健壮得像条公牛,只是想逃避兵役罢了。他还乱闹,拿他的上司开玩笑。到了这儿,他还以为是来找乐子的,把军队工作当成一场玩笑,一出闹剧。等您到了拘留所,帅克,您就会被他们教导明白:军队工作绝不是儿戏。”
由军士带往办公室,经过院子时帅克还在哼歌儿:
我总觉得,
打仗如同儿戏。
打上一两个星期,
就可返回家园……
正当在办公室里值日官向帅克嚷嚷,说像他这样的小子早就该枪毙了的时候,在楼上的病房里,委员们还在折磨其他装病逃避兵役的人。一个给手榴弹炸断了一条腿的人和一个真正患慢性骨膜炎的人——七十个病号中只有这两个人得以解脱。
“行”的断语只有这两个人没听到,其他的人,包括三位奄奄一息的肺结核患者都被诊断为可服兵役。在这个时间里,军医参谋长并没有放弃大作演讲的机会。由一些各式各样的骂人话拼凑而成的演讲,内容枯燥乏味,把所有的壮丁都说成是粪土、畜生;并且说除非他们为皇上奋勇作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回到人的社会。也只有这样,到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曾经想装病逃避兵役、想离开军队的罪过才能得到宽恕;可他本人是决不相信他们会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的。他认为,他们都应当被判绞刑。
有一位心地纯洁无邪的年轻军医请求军医参谋长让他讲几句话,同他上司的话相比,他的话充满了乐观主义和幼稚简单的精神,他讲的是德语。
他长篇大论地讲着:无论是谁离开医院走上战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胜利者和勇敢者。他完全相信,他们不仅能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而且在作战期间或者是在其他所有战争年代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继拉德茨基和欧根?萨沃依斯基王子的荣誉的不可战胜的军事家将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灌溉英明君主的神圣疆土并顺利完成历史使命的将是他们。勇敢坚强、不怕牺牲、毫无畏惧、在本团那面饱经战火的军旗下奔向新的荣誉,新的胜利的也将是他们的。
军区参谋长后来在过道上对这位天真幼稚的人说:“同事先生,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把这些混蛋教育成士兵是不能依靠拉德茨基或者是您那位欧根?萨沃依斯基王子的。对他们您像天使一般温柔也好,像魔鬼那样凶狠也好,全都没有用。这只是一帮匪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