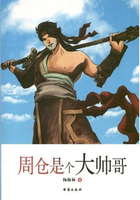小玛丽亚为了那可怜的男孩而干涉。她的干涉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受到了保护,不致遭受肉体上的虐待了。有一次,这位变心的母亲初次动手打那个她一度宠爱的儿子。这是初次,也是末次。那就是因为那个小女孩的抽筋毛病初次发作。这个,我们已经在本文的开头提出一个例证。因为母亲打哥哥,她突然晕倒在哥哥身上。当母亲用愚蠢的方法来医治她的时候,幸而父亲在家,才及时加以阻止。她的哥哥用抖动的手轻轻摩擦着她僵硬的身体,终于使它渐渐疏散,不致再变僵硬。最后,这女孩抱住他的脖子,进卧室时,她已在他怀中酣睡了。
后来,由于其他的突如其来的原因,又接着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情形。幸而,自从那件事以后,老丫头再也不打她的儿子。但是,她对他的厌恶变得更厉害,因为她不敢激烈地当众发作,泄发她的厌恶。她似乎想完全否定那男孩子的存在,目的是一心一意地照顾那女孩。为了女儿,她不厌其烦地去请教医生,和用草药治病的女郎中到圣地去朝拜,请教士诵弥撒经文,并且,由于她纵容她的方式无以复加,只要可能,她一定把她遇到的障碍除去。那软弱而心软的父亲让她照她的意思做。他在家中并不感到快乐。由于城市近在咫尺,因此,他可以看得见酒店门前的篱笆树在向他招手。本地的农民假日不可胜数,几乎把本地的日历都变成红色了。他便光明正大地到那里去庆祝节日。在那里,谁要愿意听,他就对谁说:最近五十年来,他的家里有三个人都死于震颤性酒疯。他说这并不是最坏的死法。
在她太太的眼里,他早已成为一件漠不关心的东西。她除了它的金发女儿以外,谁也不爱。她愈来愈不和亲友交往了,因为她那不自然的任性脾气使人害怕。她的房子位于那个赤裸裸的山岩上一个孤寂的地点,离大路很远。那条大路顺着库其尔山蜿蜒而上,通到提洛尔村。路过的人没一个人上门;她也不到任何人家里去。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教堂。在教堂里,她身旁的长凳仍是空空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难怪约瑟夫·希慈一年比一年更加坚决的避免接近丫头和她的家。并且,他毫不宽容地阻止他姐姐这样做。因为她有时候受了良心的驱使,对她的教子非常关心。他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会碰到安得烈和那个金发丫头的,但是,他非常严格地禁止他们在家里谈到他们。他自己无论在哪方面都非常突出,当地的人公认他是最有能力的管理人,最有野心的酿酒人,也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他的姐姐也同样得到更多主的宠爱和一些人的好感。尤其是因为她在她的遗嘱里写明:将她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教会和修道院。教土方面的报答是:他们可以保证她一去世就一定会上天堂。他的弟弟不能干涉。他的儿子,和那三个好女儿,由于父母双方都有庞大的产业,即使没有姑母的遗产,他们也受到足够的照顾。他们的母亲——阿尔干德的继承人——正当盛年就去世了。这时候安娜姑母便代替她照顾孩子。她一定要让她弟弟的孩子即使没有得到她的遗产,也会对她留下更好的记忆。
但是,孩子们虽然怕父亲,却不能盲目地遵从他的意思:即使在学校也要避开安得烈和他的妹妹。丫头生性明朗,活泼,非常喜欢欢笑,她毫无拘束地同他们来往,就好像对每一个对她和善的人一样。安得烈至少可以容忍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的安娜姑姑——他的教母——非常虔诚,只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她的弟弟才不许她关心他。除此之外,他是个喜欢沉思默想、沉默寡言的孩子,很容易发火,喜欢孤独,自小就显露对他很嫉妒。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假日,这时候他就可以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没别的孩子和他作伴,享受快乐的孤独滋味。那女孩子常常打扮,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他。他们在一个突出的岩石下面布置了一个隐蔽处,在那个大岩石上长满了许许多多的野莓,岩壁上爬满了稠密的藤蔓。这里有许多只有蜥蜴才晓得的隐藏处。他们就在这里玩孩子们玩的游戏。到了盛夏,葡萄藤的叶子密密地垂落到他们隐蔽之所的脚下。他们常常在这里坐上半天功夫。那小女孩常常不厌其烦地用一根针将一粒粒明亮的黄色甜麦仁串在一根根的长线上,做成项链。这些链子做成后,她的哥哥便跪在地面前,将这些漂亮的装饰品很巧妙地一圈圈环绕在她的额上、颈上和胳膊上。连同产生的是各种各样混淆与宗教有关的想法。戴这些装饰品的人知道自己是别人观察与羡慕的对象。的确,她那愚蠢的小脑袋周围有一个像圣像上的光环一样的光,于是,她就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快乐。那男孩甚至于更严肃。在这个时刻,假若有人敢来扰乱他这个致敬的举动,谁就倒楣。他的妹妹有时候由于任性及厌烦,会突然哈哈大笑,把那些黄色的链子扯断,把甜麦仁撒到山坡上,然后建议玩一些新的玩意。这时候,他会更生他妹妹的气。
在最初的几年间,他们的母亲不去管他们,任他们到他们常去的地方,去玩他们的秘密游戏。等到安得烈长得大一些,他们的母亲就表示憎恶他们的行为。于是,他那敏锐的眼睛里露出的惊讶与谴责神气,愈来愈厉害,并且有怀疑的表示。他这样表示来对抗母亲的憎恶。她用各种难听的字眼和卑鄙的怀疑言辞来激怒她,让她恨他,并且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分开他们。她甚至对丈夫说,这男孩子不肯做事,毫无用处,劝他把他送到十点钟弥撒教士那里去训练训练,将来好当教士。因为这孩子在校中显露出才思敏捷,热心向学的倾向,所以,这个计划很能投合这两位先生的心意。因此,安得烈便搬到城里,去和那位教士同住。他同小女孩分手时,默默不语,非常难过,但是,她却大笑,对他们俩为何会分开,一点也不了解。
那位助理教士,住在梅仑城的藤荫巷。那地方有两排石拱顶,阳光一点都透不过来。那巷子便因此得名。那些窄狭的房屋有整齐的长方形庭院和幽暗的门厅,大多非常古老,而且不整洁。这地方有相当的深度。房子那一边,广大的葡萄园向北伸展,直到库其尔山,向南通到城墙。这里光线较多。一个人可以由窗口眺望码头,以及河那边的阿迪吉广阔的山谷。那牧师的朴素住宅也有这种远景可以眺望。但是,那孩子习惯于高山上的畅快的空气,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个囚犯。其实,如果叫他拿那个向阳的阁楼卧室换一个暗暗的朝北窗户,他也非常乐意,因为在这样一个窗口,他可以眺望到高山,和葡萄藤尽头以外的那个小的岩石山岬。那就是他儿时常做游戏的地方。尽管那位和善的教士不断鼓励他,他却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寡言。突然问,他失去了读书的乐趣;他不大吃东西,睡得也不好,所以,过了四个礼拜,他变得面孔苍白,两眼深陷。一天,他来到老师面前对他说,要是再把他留在城里久一些,他就要死了。他并未提到他妹妹的名字,但是富于同情心的教士很明白他因思念那个小女孩,才变得一天比一天憔悴。失望之余,他便劝孩子的母亲,使她明白,现在必须要把他接回去住了。她大发脾气,不住责骂,而且不肯接他回去。但是,就在那同一天的晚上,那孩子来打门。经过一场大吵大闹,结果,小玛丽亚再度旧病复发。他的母亲明知不可避免,只好让步,她的条件是这个以前的学生,如今必须以雇工的身份,为他父亲工作,只可以住在屋后那个小棚的一隅。
那小女孩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而他似乎觉得为了这次重逢,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再大的苦楚和挫折,都甘愿承受。他愿意做他的继父指定的任何工作;他在葡萄园里工作,也情愿老远的跑到村那边去送信。他和母亲只在吃饭时候见面,而且彼此不讲一句话。因为他得不到金钱的报酬,只是得到一些起码的衣着。他同其他同年龄的青年仍然毫不相识,也从来不到酒店或保龄球场,但是,他并不想这些。因为,他经常像以前一样,同他的妹妹一同度假。虽然他们现在都长大了,他已长成为一个壮健的青年,她成为村里青年追求的对象:无论胆小如鼠的或是胆大妄为的,都在追求她。他们兄妹相处仍是两个孩子的关系,他们所讲的话仍然是些喋喋不休的傻话。她尽力设法舒解他的艰苦生活。她把她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好吃东西都拿来同他分享,并且,因为她喜欢吃甜食,她常常把她在城里买来的甜食分给他吃。他虽然轻视前者,但是对于后者,他接受时也显然非常高兴。往往在一日辛苦工作之后,尤其是在收割的时候,当礼拜目的阳光不能唤醒在无窗小屋中沉睡的青年时,她便悄悄走过来,在处在黑暗的角落里,他的稻草床边坐下来。我们称它为床,只是因为他盖的质料低劣的被单和马背上用的毛毯而已。她的手不住地玩弄他的头发,结果弄得乱乱的。他在暗中看不见她在身边,只是睡眼朦咙地移开她的手,仿佛是挡拒一只田鼠。这样,她觉得很有趣。等他真的醒来,他往往再多躺一会儿,静听身旁她的快活笑声。他是假装睡着,为的是要哄她再让她玩一会儿。她一定要他陪着上教堂。在那里,小伙子们都来接近她,以示爱慕之意,她并不表示拒绝。于是,他便嫉妒得心如刀割。他在这里也会碰到他的教母安娜姑姑,安娜总是静静的,以友善的态度望着他,他觉得很愿意和她交往。但是,约瑟夫·希慈在这种场合都在严密地监视着。他总是目不转晴地望着他们,让他们明白:他决不容忍那无父的青年亲近她。因此,孩子们也只是偶尔打打招呼而已。不过,丫头常常笑着对她哥哥说:露馨——希慈最小的女儿——又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老大半天了。她自从两个姐姐嫁人以后,家里只剩她一个了——丫头说,她准是爱上他了。
每当他们谈到这档子事,或是讨论一个婚礼的情形,那青年就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不往下谈。在他看来,所有的女孩子似乎都会使他局促不安,所有关于爱情的玩笑话他都厌恶。谁也猜不到他是否也会想到成家立业。但是,每当她偶尔想到将来的时候,便对他表示她可能会和他分开,而且这是一件可以忍受的事,他便会非常担忧地,带着奇怪的神气望着她。这时候,他往往说:“你还是个孩子,谁会娶你呀。男人都是坏的,家庭生活终久会导致争吵。你得同我住在一起。我会为你工作,让你过好日子的。你为什么总是喋喋不休地谈到别的男人?帕西叶的河流都流入伊芬格河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一个如意郎君给你。”
听到这番话,她往往哈哈大笑,并且很喜欢,因为,她感到他在奉承她。她那喜欢开玩笑的脑筋里也不会有认真的爱情生根。她的母亲也尽了她的责任,把外面来的求婚者都吓跑了。因此,这奇怪的小家庭住在库其尔山顶,过了许多年,丝毫没有变化。
后来,有一天,那个做丈夫的终于向那颗照亮他祖先到坟墓之路的星星投降了。他是由于饮酒过多,不醒人事,终于不治。自从那天以后,那个寡妇竭力把她的儿子逐出家门。至于经过多么激烈的吵闹,她才达到目标,我们还是不必细述吧。兄妹二人分开了:那金发丫头缺乏勇气鼓励她哥哥再受虐待。“走吧!”她说,“这样比较好些。我不会抛弃你的。你知道在她面前,我是想怎样就怎样的。假若她把我关起来,我会跳窗户出来找你的。”
她言而有信。除了礼拜天见面以外,她没有超过一个礼拜不去找他。但是这又有什么用?过去,他每天、每小时都有她在身边,已经习以为常了。经过炎热的一天工作之后,他往往坐在一株栗子树阴下。这时候,以前使他离开那位教士的孩子思家之情,往往又变得非常强烈。所以他常常横冲直撞地跑下陡峭的高山,到靠近格拉其村的地方去,只是想在睡觉之前看看那所小房子,如果看到一个人像那小女孩似的就更好了。还有一种情况,发生也不只一次了,尤其是在假日,当她没有在他们事前约好的地方见面时,他就会在通往她家的大路边守望,看是否有人和她同来。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埋伏着。要是有人走到山里来,他就假装睡着,目的是暗中观察他的面容。他这样做,并不安心。他渐渐感到轻微的怀疑;他觉得这样做不对,也不好。他为什么不让妹妹有所有少女都有意愿与爱好的自由?他非常不安地排除了这些念头,但是后来,又变得变本加厉。不错,他和她不同父,但是,难道因为这个,他们就更不像兄妹吗?
他往往想到必须到别处去,这样,他心里所感觉到的压迫才会在那里消失。但是,有什么障碍?什么力量在拦阻他?他在这里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和在外面广大的世界一样。并且,谁敢说,他到那里不会遇到他的父亲?无论如何,换换空气总是好的。要是他能鼓起力量采取第一个步骤多好!
今天,他在藤阴下坐在那沉睡的少女身旁,看到阳光在她的额上闪动着。这时候,他的心里又反复地考虑着这些念头。她现在正由方才那个打击渐渐复元,很爽快,并且什么都记不得了。可是,那个打击仍然会使他一想起来就浑身发抖。看到她那副天真而宁静的样子,他的心更加紊乱。他想鼓起勇气,现在就认真地发誓,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那种最自然的关系已变得纠缠不清,有大祸临头的危险。在她身边,他心里非常明白:非逃走不可。但是,等到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又觉得不可能逃走了。
他碰都不碰那个沉睡的少女。从小时候起,他从来不敢吻她那鲜红的、爱笑的嘴。他端详她的时候,内心的羞涩混合着一种隐隐的,情欲的折磨。她的细微的呼吸,轻轻掠过他的面孔,使他的血液跳动到他的心脏。
暮色已慢慢低垂了,因为西方的马灵山把阳光遮得很早。那沉睡的人现在已醒过来,她挺直地坐在草地上,眼睛张得大大的,四处打量。她看到她哥哥在身边,便友善地对他笑。“我睡了多久?”她惊奇地问。“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方才很热。”他说。“现在回家吧,丫头。我得到那边看看是不是平静无事。”
她站起来,伸手让他拉着。“晚安,安得烈。”她匆忙的说。现在她慢慢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后天是礼拜日。你要到教堂去,是不是?”
“不,丫头。你知道,只要我是守卫人,就必须在这里守卫。”
“不错。”她思索着说。“可是我会再来看你的。再见。”
他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不知道是否应该叫她不要再来。但是,他还来不及决定,她就走了。他站在那藤阴路的出口处,望着她迈着轻捷的步子,爬上陡峭的台阶。她那有百来个褶子的长裙,在脚踝上优美地飘动着:她每上一阶,’裙褶便一开一合的,像扇子似的。到了山顶,她向他挥手,他并没有挥手回答她的招呼。他所倚的栏杆颤动着,于是他发出一声压抑许久的叹息,但是,这叹息并没有舒解他那受到压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