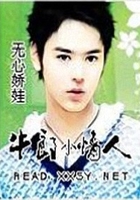某年——就这乡村的历史而言,那年代已由人的记忆中消逝了——九月间,正是闷热的正午时分,在梅仑城附近,那个占据库其尔山南面山坡的葡萄园里,坐着一个小伙子。在那比人还高的藤阴走道上,重重地挂满了那年天赐的丰硕产物,因此,一片绿色的曙光笼罩着那些寂然无声的长街。那里也充满了一股沉闷的热气,没有一点风会扬起一丝波纹。在两个葡萄园之间,灰石级陡峻而上,我们惟有走到这里,才约略地感到已由藤阴走出,来到可见天日的境界。原来,在这里,在这宽阔山谷的热锅里沸腾着的海水冒出热气,以加倍的威力,袭击着我们没戴帽子的脑袋。这里难得看见有人走过。只有无数的蜥蜴,反正不怕火,忽上忽下地爬过石级,冲过缠绕在园子基墙的坚韧葡萄藤。在拱形格子架上的深蓝的葡萄藤上,密密麻麻垂下串串的厚皮葡萄。在这无限寂静的正午时分,不时可以听见一阵奇怪的沸腾声,仿佛葡萄汁在藤蔓中循环的声音可以听见,在那灼热的阳光下,滚滚而流。
但是,那小伙子,他独坐在半山腰的葡萄藤下,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声响,充耳不闻,闷闷地陷入深思。他穿着古式的、奇怪的葡萄园守卫人(wine guard又称saltner)服装:无袖的皮夹克,上面的宽肩章用小带子,或是银链子系住。肩章将皮夹克袖口牢牢地托在衬衫的长袖上。短裤和背带也是皮制的,腰间系一条宽皮带,像拇指般粗,上面绣着园主人白色的姓名,白色的短统袜,上面有透孔的花纹。他的脖子上戴着野猪牙和土拨鼠牙编的链子,作为各色各样的装饰品。但是,他的制服当中主要的东西却丢在他身旁的草地上:三角形的高帽子,帽沿上缀满了公鸡毛和孔雀毛,狐尾和松鼠尾。在葡萄收成的季节,这东西可不是轻的负担;还有沉重的戟。要是有无权闯入辖区的人不缴出保证金时,守卫人可以用来加强他们的吓阻声势。
这些“活稻草人”,每人不分昼夜,没换班,没星期假日的休息,或做礼拜的时间,为了微薄的工资,都在指定的地区走来走去,从七月中旬葡萄开始变甜时起,直到最后的葡萄送到压榨厂为止。在酷热、潮湿的天气里,除了用玉米秸搭成的小棚子聊避风雨外,毫无其他的东西遮蔽。虽然如此,这种辛苦的职务却也是光荣的职务,惟有最靠得住的青年才叫他们选中。不但如此,在空山的高处,星光皎洁的夜色也自有吸引人处。并且,在下面的房子里,闷热的空气几乎一点儿不能发散。因此,葡萄园主人特别重视守卫人的饮食。他们每天供应丰富的食物和葡萄酒,务使他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
虽然如此,这样丰盛的饮食对我们所说的那个闷闷的青年毫不发生作用。那罐红葡萄酒、面包和几大片熏肉——这都是一个小男孩拖上山来给他当午餐的——仍然放在他身边那个权充桌子的石板上,一动未动。他那个带银链子的小烟斗,里面的烟早已熄灭。他闷闷不乐地噙着,牙齿深深陷入软软的烟斗嘴。他大约二十三岁。他的胡子,在下巴和面颊上微微地卷起。他脸上的轮廓分明,显示出早熟的样子,这是他那个地区的风尚。他的前额让头发遮住,他的头发很早就剪得快到眉际,现在已经使它长成一个个的发鬈,垂在太阳穴和颈间。他的青春气色大有让眼睛底下的黑影夺走之虞,这种发型就使他的头部恢复了所有的青春生气。
下面小路上传来缓慢的脚步声,愈来愈近,这声音使他突然抬头,戴上帽子,连忙抓起戟来。现在可以看得出,他的身高似乎比这乡下男子常有的身高要矮一些,但是,仍然很魁伟,并且他那有曲线的胸部和坚实的大腿配合得非常调和,乍看起来,非常惹眼。惟有他的头似乎太小,而他的手脚简直就是女人的手脚。那身材柔软的人在那拱形的方格子藤架下面不声不响悄悄走过。他甚至碰都不碰葡萄,由最近的石岬往路的那边窥视。
一个瘦长的人,身穿黑外套,头戴一顶极破旧的高帽子,正在葡萄园与草地之间的柳阴下漫步。交叉着的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心满意足的,两眼盯着美丽的葡萄,却毫无摘而食之的欲望。他的长外套几乎拖到黑长袜的脚后跟。即使没有那件长外套,任何人都可以在那深思的漫步者身上看出他是个教士,尤其是从他身上某些和蔼可亲的特征上可以看出,因为这些特征,在某些国度里,就代表了这种多彩多姿的教派。有些人曾经提倡统一教义,希望达到提洛尔的极乐境界(the promisedland Tyrol),因为在那里,诚信之乳与迷信之蜜,纯净地交流着。可是,在当时这猛烈的教派之争还闻所未闻,甚至于在这个古老的首都梅仑城,虽然以前有一种新的精神也曾多次猛烈地骚扰当地的安宁,可是当时,这古城仍然陷入满足于现状的状态中。因此传教士不必将他们的权杖像武器一样挥动着;他们能够沉着地尊奉他们那个情况的质朴美德。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些谦和的教士面孔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不过,在他们的脸上,我们不难发现窘迫的神气,这是他们自己的威严所造成的。这是一种不断的担忧,担忧他们对于主的伟大毫无贡献。可是,他们是披着主的衣裳呀。并且,担忧他们不得不一脸严肃地面对着他们那些尚未成为圣徒的同胞,但是又要露出不会不可亲近的神气。
那个戴破帽子的小绅士其实并不是你所常见的教会中的大人物,只不过是梅仑教堂里的助理教士。他的任务是每天十点钟在弥撒时读经文,报酬是每日一盾,分配给他一间小屋住,也有一些别的津贴。居民因为他态度谦和,而且地位仅次于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大家都很信任他,而且一定要称他为“十点钟弥撒教士”,因此,便用许多种方式向他表示敬意。无论远近,只要他一出现,没有一家不在餐桌上摆一罐葡萄酒和一些吃的东西。所以,经过一段时期之后,这位先生虽未改善他天生的细长身材,至少,他那微胖的肚皮也增加了他外表上的威严,他这个肚皮和他的身材不相称。在世俗的人看来,那样子非常滑稽。他坐下的时候,衣钮扣得紧紧的,那肚皮鼓鼓的,令人担心,会随时绷破他那件薄薄的外衣。但是,这个令人难为情的负担同他脸上的谦恭神气很调和,同时,那些受过洗,有资格接受圣餐的教徒,没一个人会取笑他这迟来的自然产物。原来,他一驾到,人人都急忙以他园中最好的葡萄酒来款待他。这件事一部分也是由于他所享的盛誉。那就是:远近许多英里之内,没有一个教士或是世俗人的舌头能比他更能品评那种酒的品质如何,可以贮藏多久,以及如果可能改良的话,要用什么配方;还有,谁也不能比他更有资格提出一个配方。过了一个时期,对一个葡萄酒品评者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他“有点像十点钟弥撒教士那样尖的品酒舌”。
但是,我们这位老兄的许多天赋与美德之中,勇敢这种特质并不是最强的。他虽出身于巴塞尔(Passeier)的农家,而且那地方出了不少勇敢的神枪手,参与了昂缀亚·侯佛(Andreas Hofer)的战役。可是,每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考验,他的勇气便逃之夭夭,把他那很容易崩溃的心灵弃之不顾。这是说,除非在他必须拯救一个陌生人的灵魂时,或是他的良心交代的某种伟大任务遭遇危险时。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宁愿以增强体力的方式来帮助精神的力量。因此他一定要注意,使家中地窖里中型酒桶里的德兰纳白葡萄酒永远不干,因为他认为那种酒有激发勇气的效果。但是今天,他刚刚到阿尔干德村去探望病人,不曾吃什么东西,所以,他遇到什么厉害的考验时,就招架不住了。一个黑影子突然从葡萄园高墙上跳下来,落在他身旁,并且抓住他的手。这时候,他就吓得魂不附体。
“赞美耶稣基督!”他一边大声说,一边抖个不停。
“永久,永久!”那孩子说。
“是你吗,安得烈,我的孩子?我真以为是魔鬼跳到我身上,因为他总是在主的葡萄园里溜来溜去,看看可以把谁吞下肚去。啊,啊,你要是陷入深思冥想之中,你很可能以为一顶帽子就是魔鬼本人。原来是你在这里呀,安得烈?你所守卫的是你自己的土地,我是说,你母亲的吗?”
那孩子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两颊也充血了。“才不呢,”他说,“我才不会再踏上我母亲的田园呢。她曾经打了我一个耳光,因为我烧了仓库。从此以后,她的儿子不管是白天或是夜里,再也不会迈过她的门槛。”
只有现在,教士才记得他已经碰到了伤疤。他诚恳而同情地摇摇头说:“啊,安得烈。你讲的都是善良的基督不应该讲的话。主在十字架上不是宽恕了他那残忍的敌人吗?母亲即使是惩罚得不公平,难道做儿子的就应该怀恨在心吗?我知道,这对你也许是很难受的事,你的母亲忘其所以地这样对待你,也许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安得烈,圣经告诉我们要宽恕人许许多多次。你离开主之后,把这道理已经忘了吗?”
“没有,神父。”那孩子坚定地说。“我发过誓,再也不想那天的事。只要我离开家,我就能信守这个誓言。但是,我如果回去,我母亲就会提醒我这件事,因为她恨我,一直都计划着如何折磨我,刺伤我,她会在遗嘱上写明不给我遗产。这一点,我确实知道,所以不太在乎。即使得不到遗产,我也死不了,而且不会不舍得让我的妹妹得到。我已经在格拉其和斯特若谈好,受雇为工头。今年,他派我担任葡萄园的守卫。我现在没有家里一文接济,也可以生活。但是母亲可能派七个差人,用四匹马将我拉回去。但是,我是不去的。迟早,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那小教士站在他面前若有所思地望望他。他觉得,与其再以教士立场规劝他几句,倒不如让事情自然发展的好。他以熟练的眼光望望墙上的葡萄藤说:
“斯特若种哈特灵哲品种的葡萄,而不种以往种的那种布拉特藤品种是对的。这些葡萄还小,但是明年会有加倍的收成。”
“这些葡萄在这里只种在边上,”那孩子说。“在那边,种的大部分是法纳其品种,其中也有些羊眼品种。他在下面提洛尔村种的是福赛琳品种,但是,他准备今年把那品种去掉,改种插枝,因为原来种的那个品种已经产了太多,快要枯竭了。”
“你们预料会产多少葡萄酒?”
“至少一百四十个单位到一百七十个单位。”
“安得烈,守卫葡萄园的工作投合你的心意吗?早晚你会觉得这工作可能很吃力呢。”
“啊,现在还过得去,神父。我的胳膊腿儿还不觉得酸呢。”
“你在夜晚也要时时警觉吗?”
“是的。但是,我只有两只眼。我得有十几只眼睛同时将每个地方都照顾到,那些士兵又开始在夜里偷偷侵入葡萄园了。葡萄的汁子很多,足够他们蘸部队里的面包了。他们总是同时来了许多人。但是,都采取单独行动。你要是抓住一个,同时,另外的人就在另一个没人防守地区下手。所以,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在他们的连长那里也得不到一点公道。”
“市政府应该向法院控诉。”
“是的,市政府!那样,我们就得有证人和证据。要是到早上,我们发现长长的一大片一大片藤子,上面最好的葡萄都叫他们偷走了。前后左右的葡萄藤,都叫他们用军刀像野草似的砍断了。这是出于怨恨,或是故意破坏。到了那个时候,又有谁会发誓作证,都是那些丘八干的?你要是抓住一个人的衣领质问他,他就会说他像一个尚在母亲肚子里的婴孩一样,对葡萄一窍不通。因此,我们就只好用私刑来自己惩罚他,这样,下次他就得三思而后行了。但是,我可以发誓,下一个如果叫我捉到,我们一定把他倒吊起来。他可以在空中练练腿劲儿,直到天明。”
“他们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安得烈。他们受到的诱惑很大,你们应该对待他们仁慈些。”
“难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野兽吗?神父,你听我说。”于是他指着一个葡萄藤给他看。那个葡萄藤已经在半腰上砍断,叶子软软地垂下来,并且已由卷须部分开始变黄了。“这长得很壮的、安静的植物,它在世上生存的目的就是使它主人的酒桶永远满满的。看到这葡萄藤让那些无赖破坏成这样子,会使你心痛!他们纯粹是用心卑鄙,只是想让我们活活气死。如果我能抓到他们再来偷,啊,愿主宽恕他!”
他一脸威胁的态度对着城的方向挥着他的戟,然后,把它挥在沙地上。
那教士微微发抖,但是,并未忘记自己的尊严。他说:“我要跟连长谈谈,就在今天,要他对部下约束得更严些。熄灯号吹过之后,谁也不许离开兵营。安得烈,愿主保护你。我今天大概要到高荫去看希慈。你有什么口信要我带给佛兰兹或露馨的?譬如说,问候话?”
“没有,神父。我同那个农人的关系仍然一样。他不承认我的存在,所以,我也不想问候他。他家里其他的人都很好,我不想因为问候他们而损害了他们同他们父亲的关系。但是,你也许会碰到我的妹妹——啊,不,也不要对她讲些什么,我只是偶尔想起而已。”
他很快地弯下身,恭恭敬敬地吻吻教士的手,似乎是要隐藏他内心的慌乱。然后,他就借着那把戟的支持,一跳跳上了墙,马上就在后面的枝叶中消失了。
那位“十点钟弥撒教土”一面摇头,一面继续往前走。他同那青年的谈话在他仁慈的心里,经过一段时候,仍然不曾消逝。但是,长久以来,他每日执掌教会方面广泛的职务,并且为自己,也为别人尽息事宁人的教士责任。所以,这同情心无比强烈的刺激已经缓和了,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晓得那青年的心情究竟如何。原来那青年现在正躺在他的稻草棚旁边,他的脸紧贴着石板地上,仿佛要摆脱极大的痛苦,将自己活活地埋在大地之母的子宫中,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