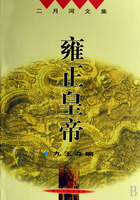诚然,从我论述的渺小的主题却引出这样重大的结论,好像是十分胆大妄为,可是我是那种相信什么事情都小中见大的人。孩子虽幼小,却孕育着成年人;头脑虽狭窄,却蕴藏着无穷的思想;眼睛只不过是一个小点,而辽阔的天地却尽收眼底。
两天以后,拍卖便全部收场,一共卖了十五万法郎。债主们瓜分了这笔钱的三分之二。玛格丽特的家人,一个姐姐和一个侄孙继承了余下部分。
当这位姐姐接到公证人的来信,得知她可以继承一笔五万法郎的财产的时候,被弄得目瞪口呆。这姑娘已有六七年没见着她的妹妹了。自从妹妹离家以后,就一直杳无音信。这位姐姐连忙赶到巴黎,玛格丽特的熟人见到她都大吃一惊,原来她惟一的继承人竟是个好看的乡下胖姑娘,而且还从未离开过她的村子呢。她一下子发了大财,甚至自己也弄不清这笔意外之财是个什么来历。我事后听说,她怀着由于妹妹去世而感到的巨大悲痛,又回到乡下去,不过她已将这笔钱放了债,每年有四厘五利息收入,这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
所有这样一些情况,在巴黎这个丑恶渊薮的城市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一下就被人遗忘了,连我也在渐渐地忘却我曾参与过的那些事。这时候,一件新发生的事情让我知道了玛格丽特的整个身世,了解到一些非常感人的细节,这就促使我产生了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念头。
那幢家具全拍卖光了的住宅,招租都有三四天了。一天早上,有人来拉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或者不如说我的兼做仆人的看门人去开门,给我拿来一张名片,并且说递名片的人想找我谈谈。
我瞥了名片一眼,看到了这样几个字:阿芒·杜瓦。
我竭力回想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于是我想起了那本《曼侬·雷斯戈》的扉页。送这本书给玛格丽特的人找我有什么事呢?我吩咐马上请他进来。
我看到了一个头发金黄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身穿旅行装,旅行服似乎穿了好些天,甚至到了巴黎以后也没有花点工夫刷一刷,那上面全是尘土。
杜瓦先生十分激动,对此他丝毫不加掩饰,泪汪汪地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先生,请原谅我这么衣冠不整地、冒昧地拜访你,但是年轻人之间是用不着这些俗套的。更何况我这样急于在今天见到你,所以我甚至来不及到我的行李先送去的那家旅馆去,就直接赶到你这儿来了。虽然时间尚早,还生怕见不着你呢。”
我请杜瓦先生在炉火旁边坐下,他便一面坐下来,一面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把脸捂了一会儿。
“你一定感到迷惑不解,”他伤心地叹着气说,“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样的时候,这样一身装束,这样哭哭啼啼地跑来找你是怎么回事。先生,我的来意很简单,是求你帮一个大忙哪。”
“请说吧,先生,我乐意为你效劳。”
“玛格丽特·戈蒂耶的遗物拍卖的时候你到场了吧?”
一讲到玛格丽特的名字,这个年轻人暂时抑制住的感情一下子又失控了,他不得不用双手捂住他的眼睛。
“在你看来我一定显得很可笑,”他又说,“请你再一次原谅我,请你相信,我永远忘不了你愿意听我讲话的这份耐心。”
“先生,”我回答道,“如果我给你的帮助可以稍稍减轻你的痛苦,那就请你快一点告诉我怎么做,你会看到我是很乐意为你效劳的。”
杜瓦先生的悲痛令人同情,我真渴望能为他尽点力。随后他便对我说:
“拍卖玛格丽特的遗物时,你买了点东西是吗?”
“是的,先生,买了一本书。”
“《曼侬·雷斯戈》?”
“一点都不错。”
“你这本书还在吗?”
“在我的卧室里。”
阿芒·杜瓦听到我这样说,像是压在心上的石块落了地,连忙向我道谢,仿佛我保存了这本书就已经帮了他的大忙似的。
于是我站起来,走到卧室把书拿来,交给了他。
“正是这本书,”他看了扉页上的题词,又翻了翻书,说道,“正是这本书。”说着两颗豆大的泪珠滴落到书页上。“那么,先生,”他抬起头对我说道,甚至不再想掩饰他已经哭过,而且止不住又要哭起来,“你很珍惜这本书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想求你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我说,“这么说来,把这本书送给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就是你?”
“是我。”
“这书归你了,先生,拿去吧,我很高兴能够让它物归原主。”
“可是,”杜瓦先生有点尴尬地说,“起码,我应该把所付的书钱还给你。”
“请允许我把这本书奉送给你吧。在这样一种拍卖中,一本书的价钱是微不足道的,我已经记不起花多少钱了。”
“你花了一百个法郎。”
“确是这样,”我说,这一下轮到我尴尬不安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很简单。我原指望能及时回到巴黎好赶上玛格丽特遗物的拍卖,但我直到今天早上才赶到。我好歹要得到一样曾经属于她的东西,于是我跑到拍卖估价人那儿,请他让我看看拍卖物买主名单。我看到这本书是你买去的,就决定求你割爱,虽然你付的高价令我担心,你一心一意要得到这本书,也可能是想留做个纪念的呢。”
阿芒这样说,显然好像在担心我也同他那样认识玛格丽特。我赶忙宽慰他。
“我只是见过戈蒂耶小姐一面,”我对他说,“她的去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漂亮女人给一个乐于见到她的年轻人往往会留下的那种印象。我想在那次拍卖中买一点什么,所以就固执地一再给这本书加价,同时也是出于好玩就有意激怒一位发了狠劲、好像向我挑战一定要把它弄到手的先生。我再对你说一遍,先生,这本书归你了,我再一次请你收下,不要把我也看成拍卖估价人,就让这本书成为我们来日方长的交往的保证吧。”
“好的,先生,”阿芒说,同时伸出手来紧握着我的手,“那我就收下了,这叫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不尽。”这时,我很想问问阿芒关于玛格丽特的事情,因为书上的题词,这个年轻人的匆忙跋涉,他渴望得到这本书的急切心情,样样都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可是,我不敢贸然提出来,生怕会引起他的误解,认为我之所以拒绝书款不过是为了想得到窥探他的私事的权利。
他像是猜到了我的心思,因为他对我说:
“你看过这本书了吗?”
“从头到尾全看过了。”
“我题的那两行字,你是怎样理解的?”
“我一下子就看出来,在你的眼里,接受你赠书的那位可怜的姑娘非比寻常,因为我不能把你题的这两行字看做普普通通的恭维话。”“你说得很对,先生。这姑娘真是一位天使。喏,请看看这封信吧。”说着他递给我一封信,这信他翻来覆去读过不知多少遍了。
我打开一看,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芒,来信已经收到,你的心肠还是那样好,我真要感谢天主。是的,我的朋友,我病倒了,而且患的是一种绝症;可你还是如此关心我,这就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病痛。我料想活不长了,你亲手给我写来这封刚刚收到的感人肺腑的信,而我连要握一握那只手的福分也没有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治好我的病的话,那么你信里的话语就足够了。我休想再见到你,因为我眼看就要离开人世,而你却远在千里之外!我可怜的朋友,你昔日的玛格丽特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与其看到她现在这副凄惨的模样,倒不如不见为好。你问我是否肯原谅你,啊!朋友,我是非常非常乐意的,因为你使我受到伤害的做法,恰好是你对我依恋不舍的一种凭证。我卧床不起已有个把月了,我珍惜你对我的尊重,所以才每天都要写下我的生活日记,从我们分手的时刻写起,直到我再也没有气力写下去时为止。如果你真诚地关心我,阿芒,那么请你回来以后去看看朱丽·迪普拉,她会把这些日记交给你。你会在日记里找到发生在我们之间的那些事情的根由。朱丽待我非常好,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谈到你。你的信寄到时她正好在我这儿,我们俩都为之伤心落泪。
阿芒,就算你没有寄来片纸只字,我本来也已经委托她,等你回到法国以后便把这些日记交给你。请不要为了这个而感激我,每天追忆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那些幸福的时刻,对我也有莫大的裨益。如果你在阅读这些日记时能找到对往事的谅解,我呢,也就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受用不尽的慰藉了。我本想给你留下点什么,好让你常常想起我,可是我家里的东西全都已经给查封,我真是一无所有了。
你理解我的处境吗,我的朋友?我眼看就要离开人世了,而从我的卧室也能听见客厅里的脚步声,那是债主们安在那儿的看守人在踱来踱去,严防任何东西私下里给弄走。所以,即使我不死,也没有一样东西算是我的了。我真希望他们能等到我死后再开始拍卖。
啊,人们真是冷酷无情!不,我错了,不如说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是天主!
好吧,我亲爱的,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遗物的拍卖,你要买下点什么,因为,哪怕我给你留下一样最微薄的东西,别人也就会有可能诬告你,说成是侵吞查封了的财物。
我就要离开的不过是悲惨的一生!
但愿天主慈悲,能让我死前再见上你一面!就眼前的情况看,我的朋友,我们得永别了。原谅我不能把信写得再长一点,那些答应治好我的病的人常给我放血,弄得我精疲力竭,到此我的手再也没有气力往下写了。
玛格丽特·戈蒂耶
诚然,最后两个字只能勉强辨认。我把信还给阿芒,趁我看信的时候,他一定在心里又把这封信默念了一遍,因为他一面接过信一面对我说:
“谁会相信写这封信的人竟是一个堕入青楼的姑娘呢!”往事的回忆令他十分激动,对着信上的字迹凝视了一阵子,末了才把信贴到嘴唇上。
“我一想到,”他又说,“她没有再见到我就离开了人世,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一想到她为我做的事是一个亲姐妹也做不到的,我就不能原谅自己让她这样悲惨地死去。死了!死了!她临死还思念着我,给我写信,呼唤我的名字,我可怜的玛格丽特!”阿芒任凭自己思绪翻腾,热泪滚滚,同时向我伸过手来。接着说:
“如果别人看到我为这样一个姑娘的去世如此心碎,会认为我幼稚可笑,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曾让她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对她多么狠心!而她则是多么善良和温顺!我原以为应该原谅她的是我,而现在我发觉自己连接受她的宽恕都不配。啊!假如能让我跪在她的脚下痛哭一个小时,少活十年我也心甘情愿。”
不了解别人的痛苦的情由是很难加以安慰的,然而我对这个年轻人还是十分同情,他又这样坦率地把我当做他可以倾吐悲伤的知心人,我相信对我的话他也不会无动于衷,所以我便对他说:
“你没有亲戚朋友吗?你要振作起来,去看看他们,他们会给你安慰的。至于我,我只能怜悯你而已。”
“你说得对,”说着,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真的叫你厌烦了。原谅我吧,我先没有想到我的痛苦跟你毫不相干,我对你唠叨的事,你是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感兴趣的。”
“这你就误会我的意思了,我非常乐意帮助你,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你的悲痛我感到有点爱莫能助。如果跟我或者我的朋友在一起可以减轻你的烦恼,总之,不管你在哪方面用得着我,请你相信,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对我都是莫大的愉快。”
“请原谅,请原谅,”他对我说,“痛苦令人感情激动。请允许我在你这儿再待几分钟,好让我有时间把眼泪擦干,免得街上的闲人看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还哭鼻子,会把这当做稀奇的事。你刚才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就够叫我高兴的了,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那你就分给我一点友谊,”我对阿芒说,“请把你悲痛的原因告诉我吧。把你心中的痛苦讲出来,这样你会感到好受一点。”
“你说得对。但是今天我太想哭了,说起话来也不会有条理。改天我会让你知道整个故事,你会看到我有没有理由哀悼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他最后一次擦了擦他的眼睛,照了照镜子,才又说下去,“希望你别认为我太没出息,并且允许我再来看你。”
这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此时他显得温文尔雅。我几乎要拥抱起他来。他呢,泪水又开始夺眶而出了。他看到我发觉他在流泪,就转过头去。
“好吧,”我对他说,“放勇敢一点。”
“再见。”他对我说。
他拼命忍住泪水,与其说是慢步走出我的房间,还不如说是冲了出去。
我撩起窗帘,看着他走进等在门口的双轮轻便马车,但是他刚在车上坐好就又号啕大哭起来,于是忙用手帕捂住了他的脸。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听人谈起过阿芒,但是与此相反,玛格丽特却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一个与你素昧平生的人,或者根本与你毫不相干的人,一旦有人在你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围绕着这个名字你每每能风闻到许多琐事,你会听到所有你的朋友对你谈起他们以前从未对你谈过的事。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你的生活里已经多次出现,几乎跟你擦肩而过,只不过你却没有注意罢了。你在别人告诉你的一些事情当中看到一种巧合,一种跟你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经历相一致之处。对于玛格丽特,我倒不是绝对地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我看见过她,遇到过她,因为我从相貌上和名声上都知道她这个人。然而,从那次拍卖以后,她的名字经常不断地送进我的耳朵,加之由于我在上一章里讲的那些情况,这个名字已牵连着那么缠绵悱恻的感情。这就会令我越来越感到好奇,越来越想打听她的事了。结果是,过去我向来不曾跟一些朋友提到过玛格丽特的名字,现在我一碰见他们劈头就问:
“你认识一个叫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女人吗?”
“是那个茶花女吗?”
“正是她。”
“熟悉得很哪!”
“熟悉得很哪!”这几个字有时伴随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那么,这姑娘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个好姑娘。”
“就仅仅这样吗?”
“是呀,比别的姑娘聪明,也许心肠稍微好一点。”
“你不知道她的什么特别的情况?”
“她曾弄得G伯爵倾家荡产。”
“就这么一点吗?”
“她曾做过某老公爵的情妇……”
“她真是他的情妇吗?”
“大家都这么说。反正他给了她很多钱。”
听到的总是这么一个大同小异的说法。然而,我却渴望知道一些有关玛格丽特和阿芒之间交往的情况。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跟那些风流名媛来往甚密的人,我问他:“你认识玛格丽特·戈蒂耶吗?”
回答我的还是那句:“熟悉得很哪!”
“她是怎样的一个姑娘?”
“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她不幸红颜薄命令我非常难过。”
“她不是有一个叫阿芒·杜瓦的情人吗?”
“一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
“正是。”
“你这话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这个阿芒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小伙子,他跟她在一起把他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光了,然后不得不分手。据说他因此简直发疯了。”
“她呢?”
“大家都在说,她也非常爱他,但只能像她那种姑娘那样地爱他,对这种姑娘不应当苛求。”
“阿芒后来怎么样啦?”
“我不知道,我们不熟。他跟玛格丽特同居了五六个月,不过那是在乡下。她回到巴黎,他也就离开了。”
“你后来就没有见过他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