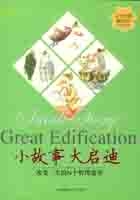大约60年前,小湖周围森林茂密,一片黑暗,有一位老人经常光顾于此,他告诉我,在那些年代,有时他看到湖上生机勃勃,全是鸭子和其他水禽,空中还有许多老鹰盘旋。他来这儿是为了钓鱼,用的是在岸边找到的一只古老的独木舟。这是两根五针松,树干挖空,钉在一起,两头削得方方正正的。小舟很笨重,但却用了很多年,才浸满了水,后来没准儿沉到湖底去了。他不知道小舟的主人是谁,于是小舟便归属了湖。他常常将山核桃树皮一片一片地绑起来,做锚链。革命前在湖边住过的一位老人,一位制陶工人,有一次告诉他,湖底有一只铁箱,他曾亲眼见过。有时候它会浮到岸边,但是等你走近,箱子又会沉人湖底,就此消失。听着独木舟的故事,我感到很高兴,这只古老的独木舟取代了那只印第安小舟,虽然它们材料一样,但是这一只的构造更为优雅,或许它起先只是岸边的一棵树,然后落人水中,漂浮了二三十年,从而成为最适合在湖中漂游的小船。我记得第一次观看湖底的时候,看到湖底隐隐约约躺着许多大的树干,它们或是从前被风刮倒的,或是上一次砍伐之后,留在冰面上的,因为当时的树木非常便宜,可是现在,这些树干都不见了。
我第一次荡舟于瓦尔登湖上时,周围全是松树和橡树,高大、茂密,在一些小湾里,葡萄藤爬过了水边的树,形成一个个凉亭,小船可以从它下面悠然而过。形成湖滨的群山这么陡,山上的树木又是这么高,你从西端望下来,湖滨就像是一个圆形剧场,可以上演一出森林剧。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湖面漂浮,任凭和风吹拂,消磨时日。夏日的一个上午,我荡舟来到湖心,仰面躺在座位上,半睡半醒,似梦非梦,直到小船撞到了沙滩,我才清醒过来,于是我从座位上爬起来,看看命运将我推到了什么样的湖岸。那些日子里,闲散是最迷人的产业,产量也最多。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就这样,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虽说我没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供我无限使用。我没有将它们更多地消磨在工场中,或教师的办公桌上,对此我并不后悔。但是自从我离开湖滨后,伐木工人将树木全都伐光了,在此后的数年里,人们再也无法在森林小径中漫步,也无法透过树林,观看湖景了。如果我的缪斯就此沉默,那也在情理之中。树林都给砍光了,你还怎能指望鸟儿去唱歌呢?
现在,湖底的树干,古老的独木舟,四周的黑森林,全都不见了,本来,村民们还不知道湖在哪儿,现在,他们想的不是到湖中洗澡或喝水,而是用一根管子,将这恒河一样圣洁的湖水引到村里,好让他们刷碗洗碟!一他们只要转一下龙头,或拔掉塞子,就可以使用瓦尔登湖水了!这魔鬼一样的铁马,其震耳欲聋的哗啦声,全镇都能听到,它那只肮脏的脚,搅浑了沸泉,正是它,把瓦尔登湖滨的树木都给吞噬了;这匹特洛伊木马,肚里藏了一千个人,全是希腊雇佣军想出来的!勇士们应该来到“迪普卡特”,将复仇的长矛剌到这个得意忘形的害人精的肋骨上,可是,这个国家的斗士,摩尔厅的摩尔人,又在哪儿呢?
话又说回来,在我所知的各种特色中,或许只有瓦尔登湖保存得最好,也最为纯洁。许多人都被比做瓦尔登湖,但是当之无愧的却没有几个。不错,伐木工人巳经把岸边的树木一棵一棵全都伐光,爱尔兰人在岸边搭起了肮脏的小屋,铁路侵犯到了它的边缘,卖冰的人还来此取过一次冰,但是湖的本身并没变化,湖水还是我年轻时见到的湖水,发生变化的是我们自己。湖水涟漪不少,但是永久的皱纹却一道也没有。湖泊永远年轻,我可以站在这儿,看着燕子跟从前一样,扑向小湖,从湖面上衔起一只小虫。今晚我的情绪又上来了,好像我有20多年没有天天见到它了。啊!这就是瓦尔登湖,我多年前发现的那座林中之湖;去年冬天,湖边的一片森林被砍掉了,但是另一片森林又在抽芽,永远充满生机;同样的思想跟当时一样,涌上湖面,同样清澈的欢乐和喜悦涌上湖水,涌向它的造物主,是的,也有可能涌向我。这无疑是一件勇士的杰作,其中没有任何欺诈的成分!他用双手将湖水围起,在他的思想里加以深化,加以澄清,并在自己的遗嘱中将它传给康科德。放眼湖的水面,我看到同样的倒影前来拜访;我几乎要说:瓦尔登湖,是你吗?
装点一句诗行,并非我的梦想;只有住在瓦尔登湖旁,才能接近上帝与天堂。
多石的湖滨就是我,微风从上轻轻吹拂;在我的手心捧着的一首英国民谣中的英雄,曾杀死一头龙。
是它的水,它的沙,而它最深的水底行宫,则高高地躺在我的心中。
这么好的湖光山色,火车却从不停下观看,然而我想,火车司机、司炉工、制动手,还有那些手持月票,经常观看的人,其实更适合欣赏这种美景。到了夜晚,火车司机并没忘掉,或者说他的天性并没忘掉,他在白天至少看过一眼这种宁静而纯洁的景色。就算看过一眼,也足以清洗掉州府大街和引擎上的油烟。有人提议将此湖称为“神水一滴”。
我曾说过,瓦尔登湖的来龙去脉无处可见,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方面,一连串的小湖从弗林特湖那儿流过来,将瓦尔登湖远远地同弗林特湖间接地连了起来,而后者稍高一些;另一方面,一连串同样的小湖显然又将瓦尔登湖同康科德河直接相连,而后者较低,在其他某个地质时代,也许它曾泛滥过,只要稍稍挖掘一下,它又会流淌过来,可是上帝不准。就这样,瓦尔登湖缄默、简朴,像森林中的隐士一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获得了神奇的纯洁,一旦相对不洁的弗林特湖水流淌过来,或者它自己流向海洋的波涛,失去它的纯洁,又有谁不会感到痛惜呢?
弗林特湖,也叫沙湖,坐落在瓦尔登湖以东一英里开外的林肯乡,是我们这儿最大的湖泊和内海。弗林特湖大多了,据说它占地197英亩,鱼类更为丰富,只是湖水比较浅,水也不够清纯。漫步穿过林中,光顾此湖,常常是我的一大乐趣。哪怕是感受一下自由之风吹拂在你的脸上,看看波浪的翻滚,缅怀一下水手的生活,这也是值得的。秋天,起风的时候,栗子落到了水中,冲到你的脚前,于是我就趁这机会去拾栗子;有一天,我正在莎草丛生的岸边爬行,一阵新鲜的浪花溅到我的脸上,我看到了一只船的残骸,船舷都没了,灯心草中,几乎只留下一个平底的印象,然而,船的模型却是纹路分明,仿佛是一只庞大的烂垫板。可以想象,这是海岸上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只残骸,而且还饱含着很好的教训。然而到了这时,它仅仅成了腐殖质,和湖滨分不出彼此,上面长满了灯心草和菖蒲。此湖北端的湖底沙滩上,留有阵阵涟漪的痕迹,常常使我羡慕不巳,在水压的作用下,湖底的沙滩变得十分坚硬,涉水者的双脚踩在上面,感觉非常明显,而那些纵横交错的灯心草则像阵阵波浪,和这些痕迹上下对应,仿佛是波浪种植了它们。在那里,我还发现不少奇怪的球形植物,很显然,这是些细草或块根植物,也许还是谷精草,它们的直径从半英寸到4英寸,非常圆。沙滩上的浅水将这些球形植物冲来冲去,有时还给冲到了岸上。它们要么是些牢固的草,要么就是中心有点沙子。起先你会说,它们是波浪冲击而成的,就像鹅卵石,然而,就是半英寸长的最小圆球,其质地也跟那些大的一样粗糙,它们一年之中只长一季。况且我还怀疑,这些波浪不是在构筑,而是在破坏这业巳获得的坚强物体。倘若干燥的话,这些球形植物的形状可以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弗林特湖!这就是命名的贫困。这个肮脏而愚蠢的农夫,居然将农田开在蓝天一般的湖边,将湖滨残忍地糟蹋掉,他有什么权利给小湖命名?有些人一毛不拔,一心只爱美金或亮闪闪的分币的反光,从这个分币的反光中,他可以看到自己那张厚颜无耻的脸;就是落户湖上的野鸭,他也视作侵犯者;由于长期掠夺,他的手指变得又弯又硬,就像哈比的魔爪,因此,湖名不合我意。我到湖那儿去,既不是为了看他,也不是为了听人们议论他;他从未见过湖,从未在里面洗过澡,从未爱过它,从未保护过它,从未说过一句湖的好话,也从未感谢赐予了此湖的上帝。因此,湖名宁可采用湖中游嬉的鱼儿,经常光顾此湖的飞禽走兽,依湖而长的野花,或某个生命线与湖泊相互交织的野人或野孩子,也不要采用他的名字,除了趣味相投的邻居或立法机关给他的一张契约,他对此湖并无所有权,实际上,他想的只是此湖的金钱价值,他在湖边的出现,给所有的湖滨都带来了灾难;他耗尽了周围的土地,而且宁可抽尽湖里的水;只可惜这里没有变成英国干草或越橘牧场,在他的眼里,此湖巳然无药可救,因此,只要湖底的淤泥能卖钱,他宁愿抽掉湖水。湖水又转不动他的磨坊,而且他也并不觉得观赏湖水是一件殊荣。我并不敬重他的劳动,因为他的农场处处都在明码标价,要是有利可图,他会把风景,甚至是他的上帝,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到市场上去,为的只是他的上帝;在他的农场上,没有一样是自由生长的,他的田地不产谷物,他的牧场不开花朵,他的树木不结果实,它们只产美钞;他爱的并不是果实的美丽,在他的眼里,果实只有变成美钞,才可谓瓜熟蒂落。让我来享受一下那种真正富有的贫困生活吧。农夫们越是贫困,就越发受人尊重,令人关注,一贫困的农夫们啊!还是一个模范农场!农场上的房子,就像是粪堆里长出来的一群真菌,什么房间啦,马厩啦,牛棚啦,猪圈啦,无论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全都连在一起!人居然像牲口一样挤在里面!简直是一个大油渍,散发出粪肥和乳酪的味道!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人的心脏和大脑居然成了粪肥!就好像你是在教堂的墓地上种植土豆!这就是模范农场!
不行,不行,如果最美的风景要冠之以人名,那还不如选用最高贵、最有价值的人名。要让我们的湖泊拥有真正的名字,至少也要像伊卡罗斯一样,在“这静静的海岸”,一次“勇敢的尝试至今仍在传诵”。
从我这儿到弗林特湖,中途有一个不大的鹅湖;往西南一英里处,便是美港,是康科德河的自然延伸,据说占地约70英亩;美港再过去一英里半,就是白湖,大约40英亩,这就是我的湖区。所有这些,再加上康科德河,便成了我的专用水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们研磨着我送去的谷物。
自从樵夫、铁路,包括我自己,玷污了瓦尔登湖之后,所有湖泊中最有魅力的便是白湖,虽说不算美,但却是森林中的瑰宝;一白湖的名字或者源于湖水的清纯,或者源于沙石的色彩,由于湖名平凡,因而并不耀眼。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跟瓦尔登湖都可谓孪生兄弟,虽说略逊一筹。它俩相似至极,你甚至会说它们一定在水底相连。湖滨是同样的石头,湖水也是同样的色彩。正如在瓦尔登湖,三伏天大热天气里,穿过森林,抬眼观看,瓦尔登湖的一些湖湾不是很深,但是湖底的反射给湖泊染上了一层色彩,湖水不是雾蒙蒙的蓝青色,便是雾蒙蒙的淡绿色。许多年前,我常推车到那儿去运沙子,用它来造砂纸,后来我仍一直前去游玩。经常光顾此湖的人提出要称它为绿湖。或许也可以称之为黄松湖,理由如下:大约15年前,你还能看到一棵棵北美油松的树梢,这种树不算特别突出,周围的人都将它称为黄松,这种油松冒出深水的水面,离湖滨有许多杆。甚至有人认为,湖泊曾经沉过,这儿原来长着一片原始森林,这棵油松就是那片森林中的一棵。我发现早在1792年,就有人这么说过,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藏书中,有一位市民写了一本《康科德镇地方志》,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了瓦尔登湖和白湖,随后作者又说道:“水位很低的时候,在白湖的湖心可以看到一棵树,虽然树根在水底50英尺之处,但是它生长的地方仿佛就是它现在矗立的地方;树顶巳被折断了,经过测量,折断地方的直径为14英寸。”1849年春天,我跟一个住在萨德伯里、离此湖最近的人聊天,他告诉我,10或15年前,正是他拿走了这棵树。就他所忆,此树离岸约12到15杆,那儿的水深有30到40英尺。当时正值冬天,他上午前去取冰,并决定下午找邻居帮忙,将这棵老黄松取出来。他在冰上锯了一条通道,一直通到岸边,然后用牛来拖,希望把树根拔起,放到冰上,但是,还没等他有多大进展,他却惊奇地发现,拔上来的一头是反的,残余的树枝还面向水里,树的小头牢固地钉在沙滩上,树的大头直径约一英尺,本来他想得到一根上等锯材原木,但没想到树根烂得那么厉害,只配作生火燃料,别无他用。当时,他的棚屋里还有一些木头的根部。木头上面还有斧头砍过和啄木鸟啄过的痕迹。他以为这是湖边的一棵死树,后来给风刮到了湖里,等到树顶注满了水,便头朝下,底朝上沉了下去。因此,树根仍是干的,一点都不重。他的父亲年巳80,记不清何时树巳不在那儿。湖底仍可见到一些大的圆木躺在那儿,由于水面的波动,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游动的大水蛇。
此湖很少给小船玷污过,因为湖中没什么渔夫感兴趣的东西。湖里既没有洁白的百合,这需要泥土,也没有普通的白菖蒲;在这片纯净的水里,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蓝菖蒲(Irisversicolor),它们沿着湖边的水底沙滩升起。6月份,蜂鸟飞来,蓝菖蒲的蓝色《片和蓝菖蒲的花朵色彩,尤其是它们在水中的倒影,和海蓝色的湖水格外和谐。
白湖和瓦尔登湖是地面上的两颗巨大水晶,是明亮之湖。如果它们永远凝结,小得可以携带,那么奴隶们或许就会将它们带走,就像携带宝石一样,去装点帝王的王冠;但这是液体,况且湖水充裕,可以永远惠泽我们及其子孙,于是我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却去追求什么科依诺尔钻石。湖水太清纯了,清纯到没有市场价值;同时也不含任何污秽。跟我们的生命相比,湖水多么地美丽!跟我们的性格相比,湖水又是多么地透明!我们从未听说湖水有什么卑贱之处,跟农夫们门前群鸭游戏的池塘相比,湖水不知要漂亮多少倍!就是来这儿的野鸭子,也是干净的。大自然中,又有哪一个居民能欣赏她呢。鸟儿的羽毛和鸟儿的乐音与花朵相映成趣,但是少男少女们,又有谁和粗矿、富饶的自然美丽打成一片呢?自然孤寂一身,欣欣向荣,远离他们所住的城镇。你们连大地都在侮辱,居然还敢谈论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