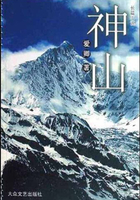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噢,你不会再看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中被杀害了。”我把报纸递给了他。
我刚刚看过这份报纸,上面报道说:昨晚现年三十四岁的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在家中遇害,警察发现屋内一片狼籍。一把印度匕首刺中房主的心脏,死者的一只手仍抓着椅子腿,倒在椅子旁。屋内贵重物品没有丢失。
福尔摩斯看了一会儿问:
“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巧合吧。”我说。
“不,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正说到这里,房东太太拿着托盘走进来,盘内有一张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牌,说:
“如果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愿意的话,请她上楼来。”
随后,候普夫人出现在门口,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是的,夫人。”
“那么,请您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说:
“请坐下吧。”
“福尔摩斯先生,您能告诉我,丢失的是什么文件吗?”
“夫人,恕我不能回答,我觉得您还是应该问您的丈夫。”
“我问过他,可他总是守口如瓶。您如果不能明确告诉我,那么给我一点点启发也可以啊。”
“夫人,您是说一?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这个事件而受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丢失文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夫人,您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那好吧。再次请您千万不要对他说我来过。”候普夫人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中充满着焦虑不安,然后走出了房门。
接连三天,福尔摩斯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直到第四天上午,报纸刊载了一封从巴黎拍来的长文电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这封电报里说到,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二自伦敦回到巴黎,有证据说明她的行踪和卢卡斯谋杀案有关。经警方核对照片,认为她的丈夫亨利·弗那依和艾秋阿多·卢卡斯为同一个人。弗那依太太患有躁狂症,据估计弗那依太太可能因癫狂发作而行凶。事发的第二天清晨,有人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看到酷似弗那依太太的女子举止狂暴。同时有人证明事发当晚,有一位妇女在高道尔劳街一连几小时盯着卢卡斯的寓所。
“你怎么看这段报道,福尔摩斯?”我问。
“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文件,而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事件。哦,这儿有一封雷斯垂德的信。”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眼仆人刚交给他的信说,“华生,我们去高道尔劳街。”
我们来到卢卡斯寓所前,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们开了门。雷斯垂德迎了上来,带着我们走进屋子:
“有件小事,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什么事呢?”福尔摩斯问。
“今天调查结束后,我们打扫屋子,碰巧掀了一下这块地毯,发现浸透了地毯的血迹并没有印在地板上。”
“地板上没有血迹?”
“是的。”雷斯垂德掀开地毯的一角。
“可是,应该有啊——”福尔摩斯有些迷惑。
雷斯垂德又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洁白的地板上有一片紫红的血迹。他说:
“这一块地板上有一块血迹,和地毯上血迹的位置不一致。肯定有人移动了地毯,可是谁移动的,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门口那个警察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
“是的。”
“那么,你把他带到后面屋里,单独和他谈谈,问问他为什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告诉他只有坦白才能得到谅解。”
“好的。我这就去。”
雷斯垂德刚离开,福尔摩斯一反刚才平静的神态,迅速拉开地毯,匐匍在地板上,用手指拨弄地板,有一块木板竟然可以向上翻起,下面露出一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进去,但是洞里什么也没有。
这时,过道里传来雷斯垂德的说话声,福尔摩斯立刻扣上那块木板,盖好地毯。
“他已经承认了。”雷斯垂德把那个高个子警察领进屋里。
“先生,我并无恶意。”高个子警察满脸通红,“那位年轻的妇女昨晚走到门前,发现自己走错地方了,于是我们就攀谈了起来。她说从报纸上看到了凶杀案的报道,想看看现场。我想让她偷偷看一眼没有什么问题,谁料她一看见地毯上的血迹就昏倒在地板上,我连忙跑到后面弄了点水来,但还是没让她醒过来。我就到拐角商店买了一点白兰地,可等我回来时,她已经走了。”
“那块地毯怎么会移动了呢?”
“我回来时发现地毯有些皱,因为她是晕倒在地毯上的,我就把地毯铺好了。”
“她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个子高吗?漂亮吗?”
“是的,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子。”
“很好。华生,我们走吧。”
那位高个子警察送我们出来。福尔摩斯走到台阶上,转过身,掏出一张硬纸片。高个子警察看见了,惊讶地喊一句:
“天哪,先生一”
福尔摩斯示意警察不要出声,又把纸片放进了口袋里。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福尔摩斯忽然大笑起来:
“华生,我想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故而遭受损失的。”
“你把问题解决了。”我很诧异地问。
“目前还不能这样说,走吧,我们直接去崔洛尼·候普先生的住宅。”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福尔摩斯却要求见候普夫人。看见我们来访,候普夫人非常生气:
“我希望我到您那儿去的事要保密,可是您为什么执意要到这儿来造访我呢?”
“很抱歉,夫人,我受人之托要找回这封信,我只能来找您,请您把信交给我吧。”福尔摩斯说。候普夫人脸色骤变。她站了起来,愤怒地说:
“你想要恐吓我,福尔摩斯先生!”
“夫人,请您坐下。如果您交出信来,所有的事情都会结束,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
“你究竟知道什么?”
“我知道您去过艾秋阿多·卢卡斯那儿,您给了他那封信。昨晚您又巧妙地从地毯下隐蔽的地方取回了那封信。”
候普夫人凝视着福尔摩斯,脸色苍白。过了一会儿,她大声地说:
“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片,那是从照片是剪下来的一张面孔:
“那个警察已经认出这张照片了。”
候普夫人低头沉默了好一阵子。
“希尔达夫人,我为您感到遗憾。看来一切都是徒劳。”福尔摩斯起身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崔洛尼·候普先生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先生,他十二点三刻回来。”
“还有一刻钟,”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等他回来。”
管家刚走出屋门,候普夫人忍不住哭了起来:
“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不要告诉我的丈夫,我很后悔这件事伤害了他高贵的心灵。现在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您,夫人,”福尔摩斯说,“您在最后时刻终于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信在哪儿?”候普夫人急忙走到写字台前,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长长的粉蓝色信封。
“快,快放回去,文件箱在哪儿?”福尔摩斯说。
“卧室里。”
不一会儿,候普夫人拿着文件箱走过来,她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文件箱,福尔摩斯把那封信塞在诸多文件中间。锁好箱子,候普夫人又把它送回卧室。
“现在,还有十分钟,”福尔摩斯说,“希达尔夫人,我想知道您冒这么大风险偷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先生,我愿意如实相告。问题出在我恋爱时一时冲动写了一封信。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再信任我了。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信落到了卢卡斯手中。他要挟我拿着那份文件换回我的信,否则就把它交给我的丈夫。所以,我偷偷地取了钥匙的模子,后来卢卡斯给了我一把配制的钥匙,我就拿了文件并送到了高道尔劳斯。”
“到那儿发生什么事了?”
“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外面站着一个妇女。我们很快把事情办完了。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卢卡斯急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又盖上地毯。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神色癫狂的妇女破门而人,用法语尖叫道‘我终于发现你和她在一起!’,然后他们扭打起来,我立刻逃了出去。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丈夫因丢了文件而心神不宁,我懊悔极了,我上您那儿去,是想知道我的错误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文件拿回来,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至于我怎么拿到的,您已经知道了。”
候普夫人刚说到这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崔洛尼·候普先生冲进屋里:
“有什么好消息吗,福尔摩斯先生?”
“有点希望。”
“天哪!首相正好和我一起来吃饭,他可以上来听听吧?”
不一会儿,首相上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您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我相信没有人把信拿走。如果文件丢失,现在一定已经公之于众了。”
“那么信怎么会不在文件箱呢?”候普先生问。
“会不会你弄混了,或许有人摇动了文件箱,弄乱了。”
“不,不可能。”
“候普先生,”首相说,“就让我们把文件箱拿来看看吧。”
候普先生摇铃让仆人拿来文件箱,然后,他打开了文件箱:
“你看,这都是些其他文件。梅娄公爵的来信,查理斯?哈迪的报告,贝尔格莱德备忘录,马德里来信,福劳尔君主的来信一啊,上帝,这是什么?!首相从他手里一把抢过那个狭长的粉蓝色信封:
“是的,就是它!”
“您是怎么知道这封信还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候普先生惊诧地问。
“因为我知道它不在别处,再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转身向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