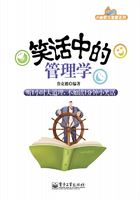从维西奥港到拉维支群岛,我乘坐的是“爱米莉号” 。这是海关的一条又老又破的小船,只有半边甲板。它那间小小的涂着柏油的甲板室,里面只放得下一张桌子与两张小床,躲风避雨,逃离海浪的袭击,全靠这小块地方,乘这么一条船旅行,可真是艰苦,不过,这就可以好好看看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的水手们了。满脸汗水淋漓,湿透了的上衣在身上直冒热气,就像蒸汽浴室里的浴巾,隆冬季节,这些穷汉也是这么一天天打发日子,甚至在夜晚,他们也是蹲在湿淋淋的凳子上,在有损健康的潮湿条件下全身发抖;因为在船上不能生火取暖,而要靠一次岸又很不容易……真难得哟,这些汉子没有一个人有怨言。遇上最恶劣的天气,我看见他们也总是沉着自若,心平气和。但是,这些海关水手实际上是过着多么艰苦的生活啊!
他们几乎都已经结婚成家,在岸上有妻子儿女,自己则成年累月在外奔波,在险情不断的海上战恶风、顶骇浪。他们只有发霉的面包与野葱头,可以用来充饥。从来没有酒,从来没有肉,因为酒与肉都很贵,而他们一年只能挣到五百法郎!……一年只有五百法郎!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海边的小窝棚是多么黑暗,他们的孩子是怎么都赤着双脚……一切都不在乎!这些好汉个个都显得乐呵呵的。在船尾甲板室的前面,放着一个盛满了雨水的大木桶,船员都来这里喝水解渴,我记得很清楚,当这些穷汉子喝足最后一口水时,每个人都摇一摇自己的杯子,心满意足地发出了一声“嗨”!那种舒服惬意的表情,既滑稽又令人感动。
他们之中最嘻嘻哈哈、最心满意足的,是一个博尼法西亚人,他身材矮壮,皮肤晒成了褐色,大家叫他巴龙波。他平时总是不断地哼着唱着,即使是在风急浪高的日子。每当波涛汹涌、阴暗低沉的天空弥漫着雨雪的时候,别的水手都昂着头,用手紧握着船索,观伺着大风即将袭来的方向,全船一片沉默,大家忧心忡忡,这时,巴龙波平静沉稳的歌声却唱起来了:
并非如此,主教大人,
在下实在受宠若惊,
丽赛特本来贤慧聪明,
她从小就生长在农村……
此时,任你狂风猛吹,帆上的索具嘎嘎作响,船身颠簸倾斜,这个水手仍然唱个不停,歌声在空中飘荡,就像海鸥在浪尖上翱翔。有时,狂风怒号,使人讲话的声音也听不清楚,可每当风浪掀起的瞬间,在海水的迸射之中,你总能听见他歌中那短促的叠句:
丽赛特本来贤慧聪明,
她从小就生长在农村……
但是,有一天,风雨交加,急猛异常,我没有听见熟悉的歌声,这真有些异常,我把头伸出甲板室,问道:
——“哎,巴龙波,今天怎么不唱了?”
巴龙波没有搭腔,他躺在凳子下面,一动也不动。我走近他。他的牙齿在打战,全身正烧得发抖。
—— “他得了一种叫庞肚拉病。” 他的一个同伴发愁地告诉我。
叫庞肚拉的这种病,是一种胸痛病,一种胸膜炎。这时,天空灰沉沉的,船已经淋得透湿,可怜的高烧病人,裹着一件被雨水淋湿、像海豹皮一样湿漉漉的橡胶大衣,滚来滚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痛苦难受的病人。不多久,寒冷、大风与海浪的颠簸,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开始神志昏迷,船非靠岸不可了。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努力,黄昏时分,我们的船才驶进一个荒凉而寂静的小海港,只有几只盘旋飞翔的海鸥才使得这个地方略有生气。海滩周围,高高兀立着陡峭的岩石,杂乱长着一些四季常绿的灌木丛。下边,靠近海岸,有一间带灰色窗子的白色房屋,那就是海关哨所。在这一片荒野之中,这个标着数字号码、形状像制服帽的官方建筑,显得有点阴森可怕。人们就是把巴龙波安置在这里。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糟糕的避难所!我们一进去,就看见一个海关人员和妻子以及几个小孩,正在火炉旁边用餐。这一家人全都面黄肌瘦,眼睛突出,眼圈带有病容。那个妈妈,还算年轻,怀里抱着一个待哺的婴孩,跟我们说话时直打哆嗦。
——“这是个可怕的小哨所,“这个海关人员低声对我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两年轮换一次。否则,疟疾病会把人吃掉……”
此刻,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医生。在到达萨尔泰勒之前,也就是说,离此地六至八法里之内,是休想找得到的。怎么办呢?我们的水手都不能去,打发一个孩子去,路又太远。于是,那妇人转身向着门外,叫道:
——“塞戈!……塞戈!……”
只见走进来一个高大健壮、身材匀称的小伙子,样子颇像偷猎者或绿林好汉,他头戴棕色毡帽,身披羊皮大衣。我上岸时,早就注意这个人了,他当时坐在门口,两腿之间夹着一杆枪;不知什么原因,见我们一走近,他就避开了。也许,他以为有警察跟我们一道来了。此时,女主人一见他进来,脸上就泛出了些许红晕。
——“这是我的表弟……”这女人说,“他即使丛林里迷了路,也不会有危险。”
接着,她悄声对他说了说,指着那个病人。那男子点头同意,他走出房间,打了个呼哨唤来他的狗,肩上扛着枪,迈开长腿,从这块岩石跳到那块岩石,就这么出发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孩子们由于父亲在场而有些胆怯,他们很快就吃完了淡奶酪煮栗子的晚餐。他们从来只能吃上汤汤水水,除了汤汤水水外,餐桌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就要算丰富的了,在孩子们看来,就像是喝了一杯美味的葡萄酒。唉!穷到了如此地步!接着妈妈把他们带到楼上去睡觉;爸爸呢,他点燃了手提灯,就到海边巡查去了,我们则待在火炉边守着病人,他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就像仍旧在海上,受着海浪颠簸的煎熬。为了减轻一点他的疼痛,我们把鹅卵石与砖头烤热,放在他胸肋上。有一两次,我靠近他床的时候,他认出是我,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他费了好大的劲把手伸给我,那一双粗糙而滚烫的手,好像刚从火炉里取出来的一块砖头……
这天夜晚真是凄惨得很!在屋外,随着夜幕降临,坏天气又卷土重来了,海浪肆虐逞凶,发出一阵阵撞击声、轰隆声、飞溅声,海水正在跟岩石展开搏斗。有时,一阵狂风刮进海湾,吞没了我们这栋房子,风力使得炉子的火苗向上猛蹿,火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水手们忧郁阴沉的面孔,他们围坐在火炉旁边,带着一种平静漠然的表情看着炉火,由于长期在海上面对一望无垠的空间与远方单调的前景,他们这种表情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巴龙波偶尔也轻轻地呻吟几声。于是,我们的眼光就投向那个阴暗的角落,在那里,这个可怜的水手正在逐渐死去,远离他自己的亲人,得不到急救;他的胸部正在肿胀,可以听见他一声声长叹。此情此景,使得这些坚韧而驯良的海上工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命运的悲惨。没有反抗,没有罢工。只有声声叹息,其他什么也没有!……但不,我估计错了。他们之中就有一个水手,当他到火炉前去添加树枝时,正从我面前走过,我听见他压低声音悲愤地对我说:
——“先生,您瞧……在我们这个行当中,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