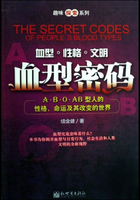太后怕是也有些怀疑是邪物作祟吧?
只是太后万不敢声张,巫蛊邪术历来是各朝各代的禁忌,前朝就曾出过因巫蛊害人而诛杀几百人的前例。
太后不说巫蛊邪术,我当然也不会说,况且这一切都还只是我个人的怀疑而已。再说,太子表现异常的事,也只有太后往别处想了。其他人只认为太子是近来诸事不顺(尤其涁河沿岸各州的事务)又常遭皇上提骂所致。
第二日大早,太子过来寿宁宫请安,太后道他气色不善,让我给太子把把脉。我折腾了一番工夫,最后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太子言行正常,思维独立,瞧着也不像被控制了心智。太子走后,我摇摇头,太后便陷入了沉思。
一种沉静如水,让人摸不透看不明的表情在太后脸上浮现。
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直觉想逃离此处,逃离皇宫深院。这里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行走,那么遥远而陌生。让人分不清谁是真的善,谁是真的恶,谁对谁好又有怎样的企图?这么一想我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缺乏安全感。
这种像漂泊瀚海的孤舟找不到港湾的不安直到我想到了哥,才生出几分安全踏实之感。哥在墨阳王府属地过得应还好吧?上次传来的消息说墨阳世子清剿流匪的事进行的很是顺利,可哥却又为何总不给我来信,也不回我的信呢?
是辗转中弄丢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顺着思维里一根细细的线想着,哥送我的那座城堡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落入了谁的手中?许诚真正的主子又是谁?一个个没有解开的疑问潮水般涌来,堵塞了我思路的畅顺。
兰花仙子诞这一日平静的过了。
太后又留我在寿宁宫住了几日,明处是说许多日不见留我说说话,甚至连磬儿也一并接了来伺候。暗处我不过是费心查治太子的“病”罢了。这几日,太子的情形与我在晚宴上所见并无太大差别,冷冷淡淡的性子,话也不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奇异了。
我不知道太后为何如此敏感和在意太子性情的转变。可几天来的查治,到最后,我只能告诉她,从一个大夫的角度来看,太子的身体绝无疾病,若真有什么,怕就是心病了。
我从皇宫回到景王府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
用了晚膳,我坐在清宁院树下的秋千上,看过谦益送来报平安的家书,重重舒了一口气。谦益信上的内容不多,只道他一切安好,算算日子,我与谦益竟已未见一月有余了。
淡月升起,晚风渐渐有些凉了,吹得老绿的树叶微微发抖。
“王妃,起风了,回屋歇了吧。”磬儿从屋内出来,拿了件单衣给我披上。
我淡淡一笑,“你先去歇吧,我再坐会儿。”
“那奴婢陪您。”磬儿在我身边站定。
沉默良久之后,磬儿支吾着开口,“小姐。”一声“小姐”带着最初的记忆,仿若令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仍在天医宫的时候,磬儿整日跟在我身后追着道:“小姐,不能做,宫主会骂人的……”
“小姐,”磬儿斟酌了半天,终是说出口了,“奴婢觉得您变了许多。”
“变了?变成怎样了?”我没有看磬儿,讷讷出声。我怎会不知道自己变了?变得越发不像往昔笑闹人世的慕容植语了。少了心境上的灵巧,多了份沉重。
“您以往在天医宫的时候,虽然很懒也不爱理事儿,还爱捉弄人……却让奴婢觉着您是开心自在的。”磬儿的脸上露出由内而外的微笑,“可自从您嫁给王爷之后,奴婢再没见您像往常那般开心过,还常常要忍受莫明其妙的委屈,奴婢见了很心疼……”
是啊,以前的我是那么无忧无虑,是一朵高高在上俯视苍生的云,了无牵挂的漂浮着。如今的我却是一个懂得筹谋算计陷入勾心斗角之中的俗物了。心里头牵挂着一个人,无形的压力和压迫感便扼紧了我的喉咙,喘息间就可令我命丧黄泉。我又如何能重拾以往无忧无虑的快乐呢?
到现在,只求心境不是一日暗过一日就好了。委屈?除了桃花源一般的天医宫,这世间人又有几个不受些委屈的?
我叹了口气。开始怀念以前每日里与师傅作对,怀念被师傅惩罚泡幽灵潭,怀念偷偷爬到我床上的天蓟,怀念天医宫我栽种下的每一棵花草树木。
“小姐明明什么也没做,那些人为何偏偏总要诬蔑您呢?”磬儿替我抱不平,“说的话也太难听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有些事又如何说得明白?问得清楚?
“磬儿,”我幽缓转移了话题,“你觉着飞鸟和鱼能在一起么?”
磬儿不明白我为何有这么一问,皱眉道:“鸟不能潜到水里去,鱼又不能飞出水面来,怎么到一处呢?可不难受?”
对,确实很难受。当一只飞鸟把自己伪装成鱼,潜入水中时,它难受到窒息,因为它忘不了它没有腮,没有能在水中生存的依据。
尽管我已谨言慎行,皇宫于我,还是那般格格不入。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或许一张,或许两张,或许更多。真真实实,虚虚假假,谦益的世界,原来是这般难以进入……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些累了。”我看着磬儿,指了指心。
“小姐是不是还在气十七公主的话?”磬儿低声询问,却是曲解了我的话。
十七?气?是啊,是真的很气的。
这会儿,十七在我离宫时辱骂我的话,一定已经传遍皇宫该传的每一个角落了。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三嫂,”十七颐指气使,贵公主的气派十足,语气是嫌恶的,“你不过是山里出来的狐狸精,迷惑了太子哥哥,又想把七哥的魂给勾走,真是不要脸……”
“你觉得我不该忍下那句话?”我抬起头来,我居然就把那样一句话给忍住了。
磬儿微点点头。
“那些子虚乌有的话,何必太过在意呢?尤其在意也不会有结果的时候。我们势弱,十七是嫡脉公主,谦益不在,我毕竟是个外人。我若回骂或动手打了十七只能是自找麻烦。反是称了某些人的心,那些人是恨不得我与十七打起来才好呢。”不然哪能往下做文章?
“小姐……”
“行了,不说了,回去歇吧。”
回屋后我很快入眠,一夜无梦,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
磬儿进房拉开我的纱帐,伺候我梳洗,随口道:“王妃,今儿的太阳喜洋洋的,外头的喜鸟也叫着,好像会有什么喜事呢。”
没想真是一语成谶。
下午时,果然应验了磬儿的话——喜事,我怀孕了,一个多月。
我本该早些知晓的,只怪我的月事总不规律,时而提前,时而延后,我便也没太留意。今儿也是一时兴起,号了个脉,这才发现自己竟怀孕了。
我低头,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情,轻轻抚摸着腹部,“磬儿,这件事先别跟任何人说,等谦益回来,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磬儿高兴的手舞足蹈,蹲在我身旁,热切的盯着我的肚子,仿佛那里藏着一个多么珍贵的珍宝,“王妃……您说……您怀的是小世子还是小郡主?”
我轻推了下磬儿,“你啊,这么激动作何?才一个月大,哪里就知道是男是女了?”
“一定是小世子。”磬儿傻笑道,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我的肚子,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小世子。
我浅浅笑着,“我倒希望是个小郡主。”谦益与我的女儿,呵,将会成长为怎样绝世的女子?
怀孕的喜讯几乎将我昨日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我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愉悦而满足。它可以让我忘记一切烦恼和压力,这一刻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享受着一份从未有过的快乐。
谦益若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也会很激动很高兴吧?我差不多已能想像到他那时将会有怎样灿烂无比的笑容,这可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我的好心情延续到了翌日。
一大早遣散了汇报家务的管家和管事们,有人来报,说宁右相千金求见。
我正揣测着宁毓儿此来的目的,她牵动一身柔弱的淡雅已随下人到了花厅。我命人上茶,与宁毓儿虚礼客套了一番。
宁毓儿倩兮嫣然道:“上次素琴下毒害臣女的事,多谢景王妃救命之恩,一直想自个儿登门致谢的,却是……到了这会儿才来……”
我笑笑,“哪里就是救命之恩了,宁姐姐说到‘谢’就实在见外了。”我知道宁毓儿此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若说致谢,我当初离开帝都前,宁右相便已经遣人送过谢礼了。
宁毓儿又应对了几句,稍稍有些拘束的坐着,一副茬弱模样,我见犹怜。
“宁姐姐若是有话不妨直说。”绕弯绕了快一个时辰,我实在觉得她那想说又不敢说的神情太过楚楚可怜。
宁毓儿看了看屋内伺候的丫鬟,没有开口。
我会意,挥手摈退了下人,宁毓儿也挥退了她的两个贴身丫鬟。
“宁姐姐有话就直说吧。”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朝向宁毓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