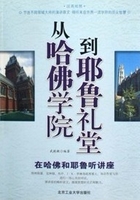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你倒想!”潜光看也不看我,冷哼道。
我冷笑,“这你就错了。你们不刺出心口血更好,横竖我没损失。”我依然是白湛莹,量你们也不会对我怎样,除非你们都不在乎心爱女人的死活了。
只要你们还心存一丝怜惜,我就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我来吧。”谦益平静无波的道出一句,“如果不确定谁最爱她,就由我先来试……昨日收到月霏飞书,又失了天医行踪。若是‘千面妖狐’费了这许多时日都追踪不到天医,必是有高人从中阻拦了。想来我是没有多少活命的希望了。我既已命不久矣,就让我为丫头做最后一件事吧。”
“不行!”潜光坚决反对,“我答应过雨儿,定要保你性命。”
谦益也不示弱,“我亦答应过丫头,绝不害你性命。”
我大笑起来,“慕容植语也算不枉此生了,居然有两个傻子争着为她送命。不过,依我看,你们俩真的不用争。你们都以为自己是最爱慕容植语的人,可在我看来,你们都不是。”
我成功的吸引了谦益与潜光的目光,他们停止了愚蠢的争执。
我得意笑道:“你,竹谦益,一再强调你爱她,不惜倾尽一切给她世上最美好的物事。可你用权利打造的极致之爱给她的却只是禁锢她的城堡,没有丁点儿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你,竹潜光,口口声声说爱她,能为她放弃一切,却偏偏始终不能放下对宁毓儿的愧疚与责任。到头来,你给她的爱只是让她在承受委屈的同时不断自我压抑。”
“你们一个以爱的名义折断她的羽翼,不给她广袤天地,不让她自由翱翔;一个以爱的名义,利用她的善良成全自己对别的女人的愧疚,让她在自我压抑中饱受煎熬。一个在她爱你时,猜忌她;不爱你时,禁锢她。另一个在她不爱你时,纠缠她;她爱你时,又委屈她。你们自己说说,哪一个配说自己最爱她!”
我说得畅快淋漓,听的人,神思早已不知飞过了几重山,几道河,坠落到久久远远的回忆里了。
所以,最爱她的人,是我,是我白湛莹!
我与她是一体的,我怎会不爱她呢?爱她就是爱自己。
“所以,就算你们都死了,也解不了咒。我是她的梦魇,也注定是你们两人的梦魇。这辈子,你们甩不开,除不去的梦魇。”我肆意妄为的笑起来,要笑得天也昏地也暗,笑得山河失色、乾坤倒转。
却没想到,我的心猛然间抽痛起来。
我嘴角抽动,紧锁娥眉,狠狠唾道:该死的江暮雨!你在为他们心痛吗?!
你为什么要为他们心痛?!
“王爷,不好了……王爷……”宁毓儿的贴身丫鬟跌跌撞撞的闯进来,满头大汗,一脸青紫,脸上泪痕遍布,喘着粗气道:“王爷,小姐……快……快不行了,您快去看看吧。”
潜光从痛苦的回思中清醒,惊道:“毓儿?那还不快传大夫——”
丫鬟哭丧道:“已经传了……大夫说,小姐……怕是不行了……小世子若还生不下来,也……也……没救了……”
“哈!搞了半天,原来宁毓儿还没生呢?我只当你已做了便宜爹呢。”我讥讽道:“想必是她素体虚弱,正气不足,临产时又过度紧张,心怀化惧所致难产。真是可怜啊。”我高声叹息,“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安徽灵壁虞姬墓对联,明朝倪元璐所做)。”
“救她!”潜光蓦地解开我的穴道,抓着我的手急道:“即便别的大夫没办法,你也肯定有办法救她。”
我狠劲抽出手,揉了揉,“怎么?这么心疼你的王妃?你这样心疼别的女人,你的雨儿会伤心死的……”我“咯咯”掩嘴轻笑。
潜光冷道:“保住她和孩子,这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我耸耸肩笑道:“可惜啊,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了。没错,我是有神医之名,是能救她。可我对她有杀之而后快的恨,我为何要救她?”我逼近潜光,轻轻地暧昧的吐出一口气,“光哥哥,不如你替我想个理由吧。”
潜光是聪明人,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紧张的神色也立时舒缓下来,转而邪魅道:“看来这是你一早预谋好的。你倒是说说看,需要我给你一个什么理由?”他反俯下身子,暧昧的逼近我的脸。
我退开一步,故作惊诧,“怎么?这会儿老神在在,不担心你的王妃命在旦夕了?”
他索性双手抱胸,挑眉邪笑道:“既然你一早布置好了,又怎会舍得就这么要了毓儿和孩子的命?”
“也许我现在又改变主意了呢?你知道,女人是善变的,我现在可能不想留她了。”我悠闲的点点头,摇摇头,再左转一圈右转一圈。
“说吧。”潜光冷眸直道:“你要什么条件?”
我娇笑道:“看不出来,光哥哥这么识时务,那我就好心给你指条明路。第一,先替我把思樱抓过来。第二,替我对付空空公子……”
“空空公子?”谦益与潜光异口同声的失声惊道,面面相觑后满脸古怪表情,“他得罪了你?”
我冷哼,“你们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在竹苑雅舍绑走慕容植语的不就是空空公子么?当然,也就是那日河岸边的那个锦衣男人。”
锦衣男人惊叫那声“韵致”时,江暮雨就吓了一跳,那个声音那么熟悉,熟悉到名字就在她的嘴边,就要溜出来,可当时还是没能一下子反应过来,那就是空空公子的声音!
“你是说他?”两人又异口同声道。
我渐生疑惑,“难道他不是空空公子?”江暮雨明明记得那个声音,她听过两次,她的记忆力超群,听过两次的声音没道理会记错。
潜光没给我深思的机会,催道:“你的条件我答应,你现在赶紧去救毓儿跟孩子。”
我笑道:“你放心,有你当爹的时候。她们母子,嗯,或许是母女,活着比死了对我有用。我只是让她受点活罪,不会那么早送她去见阎王。那样的话,我岂不是做了笔亏本买卖?”我才不会那么便宜宁毓儿。
我迈开步子,散步般往宁毓儿的寝房而去。
远远的,听不到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近了,到了宁毓儿的床前,才发现,她已痛得休克了。
汗水,打湿了宁毓儿的头发,它们卷曲着,贴在她的额前鬓角。浓浓的血腥味儿在鼻翼萦绕不散,随处可见的大片大片血渍似凋落腐败的花与宁毓儿那面无血色的灰白的脸一同控诉着我让她受了多大的罪。床前立着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稳婆不接生,丫头不换水,大夫不诊脉。他们一身狼狈的盯着床上一动不动的宁毓儿。
潜光看着眼前一幕,有些不敢相信,低唤了几声“毓儿”,真真实实发觉没有回应,面上顿急,催我快施援手。
我摸上宁毓儿惨白的脸,她就这样安静的闭着眼,娇嫩的容颜如温室之花,惹人怜爱与呵护。我的心隐隐一痛。我暗骂,江暮雨,你这个蠢女人,你还在怜惜她吗?她今日所受之苦都是她咎由自取,怨不得我。
丫鬟们低低的抽泣着,那盈盈嗡嗡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旋尤为刺耳,我烦闷道:“她还没死呢,你们哭什么丧!”
众人都惊“咦”了声,一个大夫不信道:“可是……已全然没了脉象。”
“那是你医术不够高明!”我一句话堵住了他的嘴,高声清场,“男人都可以出去了。主要包括大夫!”众大夫听我语气不敬,轻哼两声,一一甩袖而去。
我不紧不慢的取出银针袋,扯开锦被,解了宁毓儿的衣裳,在该下针的地方,稳稳扎下几针。推拿按摩之后,又施展绝技“梅花八针”,为她疏通血淤,顺畅呼吸。宁毓儿两个贴身丫鬟的眼一瞬不眨的盯着我,既想看我要如何起死回生,又担心我会不会一针要了她们小姐的命。
折腾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我停下来,拭了拭额头渗出的汗,喝斥呆若木鸡的丫鬟与稳婆,“还愣着作何?赶紧换水准备接生,她就要醒了。”
不多时,便听得宁毓儿轻咳了几声,缓缓顺过气来。她睁开眼,众人都松了口气,温和了面部表情。她却见鬼似的,惊叫一声瑟缩了身子往床的内侧挤去,只因她看到了我。
我冷笑,挤眉弄眼的俯身以只有她能听到的音量在她耳边说道:“你放心,我暂时还不舍得你去阎罗殿登记为常住民。所以,你就给我些颜面,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吧。”
看了看已经忙碌起来的稳婆与丫鬟们,我猛得拂袖起身,跨出房门,走至焦急的潜光身边傲然道:“放心吧,她死不了,你难道没听过……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吗?”
潜光流露出让我不能明白的表情,叹息道:“毓儿与我自小相识,她一直是个温婉娴雅的女子,温柔体贴,连蚂蚁都不忍伤害,谁曾想她会……”
“会害人?而且还害了你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对她的这种转变感到痛心和不忍相信,是吧?”我冷嗤,“这就叫女人心,海底针。尤其像她那样的温室花朵,嗯……大家闺秀,自小养尊处优,被人捧在手心里疼,几乎没受过什么苦。”被保护得太好,就没有抵抗风雨的能力,感情也相当脆弱,“所以只要一点点挫折就能给她心理造成极大的打击伤害,逼她走向极端。”
我白湛莹又何曾不是?
若非当年家逢巨变,昔日“公主”遭人拐卖毒打,我的天地一夕间完全变色,我也不至于狠下心肠给“爸爸”“妈妈”的饭菜里投毒,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我。从那时起,江暮雨就出现了,只是那时她仍叫白湛莹,她很懦弱,但她却顽强的处处压制我,直到把我压到心底最深处。
那个下着雨的黄昏,哥出现了。从此,她抛弃了“白湛莹”这个名字,她叫江暮雨,她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她责怪我狠毒无情,将我埋葬起来。她要跟哥学着做一个可以笑闹人生的人。
但是结局呢?她摆脱不了良知的桎梏,就只能一次次被人迫害,一次次饱受折磨。
江暮雨,拥有良知是你致命的弱点。
这世界,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至亲之人尚且如此,还要良知何用?没有那些失了良知的叔伯亲眷的逼害,我白湛莹会家破人亡么?!需寄人篱下么?!
我深深吸了口气,收回飘远的思绪,平复心情。抬头冷然对潜光道:“我已做了我该做的,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我想你该知道,我今日能救人,他日一样可以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