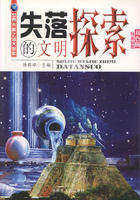汤米.杜克斯到薇碧山庄作客,另外有个温哈利,以及史杰克和他太太,欧莉芙。话局听克里夫老友相聚时还要无厘头,每个人都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天气不佳,只能关在屋子里打弹子,或和着钢琴声跳跳舞。
欧莉芙手上一本书,讲的是人类的未来,婴儿在瓶子里孵育,女人则将“免育”。
“那实在太棒了!”她说。“如此一来,女人就能过自己的悠哉人生了。”史杰克想要孩子,她却不想。
“你愿意“免育”吗?”温哈利问,笑得有几分狰狞。
“我当然愿意。”她答道。“将来的人一定会更聪明,女人也不必再受生理机能的牵绊之苦。”
“说不定她们还能飞入太空呢。”杜克斯接着道。
“我真的认为文明一旦进步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解决许多肉体残障的後果。”克里夫说。“比如说床第间的那一套,能免的就免了,只要我们真的能够在瓶子里孵育婴儿。”
“不是!”欧莉芙叫起来,“那样反而会有更多时间和心力来寻欢作乐。”
“我想。”白纳莉夫人沉吟道,“如果床第间那一套省掉了,势必会有别的花样来取代。说不定是吗啡,空气里调一点吗啡,保证人人精神百倍。”
“每星期六政府放点醚到空气里,让大家度个快活周未!”温哈利说。“点子好是好,可是星期二咱们到哪儿去?”
“只要忘掉肉体的存在,你就会轻松。”白纳莉夫人说。“一旦你注意自己的肉体,你就惨了。所以,文明如果有好处,就该帮咱们忘掉肉体的存在,那样,我们会过得快快乐乐的,不知老之将至。”
“帮咱们抛掉肉体吧。”温哈利说。“也该是人类改善本性时候了,特别是肉体方面的。”
“想像咱们像菸草烟儿那样飘飘欲仙。”唐妮说。
“不可能的。”杜克斯说,“人类的老戏会垮台,文明会崩溃,陷入无底深渊,永劫不复。相信我,要跨越深渊的一道桥就是阴茎。”
“哦,真是,真是受不了你,将军!”欧莉芙大嚷。
“我相信人类文明就要崩溃。”爱娃姑妈道。
“然後会怎麽样?”克里夫问。
“我完全不知道,但总会出现点什麽,我想。”老太太说。
“唐妮说人会变成一缕轻烟,欧莉芙说女人会免育,婴儿在瓶子里孵育,杜克斯又说阴茎是本来人类的桥梁,我想不透最後究竟会怎样?”克里夫道。
“哦,别伤脑筋了!咱们把握现在,痛快过日子吧。”欧莉芙说,“只是快点把繁殖瓶发明出来,让咱们可怜的女人解脱。”
“下一个阶级,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人类!”汤米说。“聪明、健全,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那书不是人类的一些变化?我们不是男人,女人也不是女人,我们只是一种代用品,是机械和智力的实验。说不定未来还会有男、女完人的文明,来取代我们这些自命不凡,其实脑力不超过七岁的人,这比化成烟的人和瓶中婴儿更惊人。”
“天呀,一讲到真正的女人,我就没辄了。”欧莉芙说。
“我们身上唯一可贵的东西,就是精神了。”温哈利说。
“是精神!”杰克说,一边喝他的威士忌加苏打。
“你这麽认为?那我要的是肉体的复活!”杜克斯说。“这会实现的,迟早的问题,就等我们把塞在脑子里那团石头推开一下下,把金钱和其他什麽的也都推了开,到时我们就有接触的民主,而不是荷包的民主了。”
唐妮听了这话,心里一动。“给我接触的民主,让我肉体复活!”她根本搞不懂这是什麽意思,但听了却觉得舒坦,有时毫无意义的事会有这种效果。
无论如何,他们讲每件事都蠢得可以,她对一切,对克里夫,对爱娃姑妈,对欧莉芙和史杰克,对温哈利,甚至对杜克斯,都感到厌烦到极点。讲,讲,讲!喋喋不休,这到底算什麽!
等客人全走了之後,情况也没好转,她继续晃来晃去,但那股躁怒已控制她的半个人,她摆脱不了。每一天都像折磨,难受得出奇,生活却是平静无波。她只是越来越瘦,连管家太太都注意到了,问她怎麽了,她自称无恙,但连汤米.杜克斯都认定她病了,她只是开始怕起泰窝村教堂下边,满山遍野的卡拉大理石碑,白得刺眼,像假牙那麽讨厌,她每每从园林看到那些阴森、丑恶的,假牙似的白墓碑,就感到不胜恐怖,她自觉葬身在这脏污的中部,与墓碑下的枯骨为伴的日子,似乎也不远了。
她晓得自己需要帮忙,所以写了封信给她姊姊:稀尔黛。“近来不知何故,我感到不适。”
稀尔黛住在苏格兰,很快有回音。三月里,她自己一人驾了一辆轻巧的双座小汽车来了。她开上车道,一路按喇叭。绕过生着两株野生山毛榉的椭圆型草坪,一霎在屋前停下。
唐妮奔下台阶,稀尔黛下车亲吻妹妹。
“你是怎麽回事。”她大叫。“唐妮!”
“没怎样呀!”唐妮有点赧然的答道。她心知和姊姊比起来,她要憔悴多了。姊妹俩本来都同样有一身光洁的皮肤,棕色秀发,和天生健美的身段,可是现在唐妮瘦巴巴的,面有菜色,露在毛衣外的颈子又黄又乾。
“你病啦,妞儿!”稀尔黛说,两姊妹说话声音都一样,轻轻柔柔的,却有点儿喘。稀尔黛大唐妮还不到两岁。
“不,没有痛,可能是太闷了。”唐妮说得有点可怜兮兮。
一股战斗的表情出现在稀尔黛脸上。她外表看似温柔肃穆,其实是天生不服男人的刚强女子。
“这鬼地方!”她低声说,恨恨望着那黑鸦鸦的老宅子。她看来温柔和悦,如熟透的梨,却不折不扣是那种老沉的烈女子。
她不吭声的就跑去找克里夫。她俊俏的风姿让克里夫在心里喝采,可是她的人又让他忌惮。他妻家的人不甩他那一套规矩和礼数。他一向把他们当外人,一旦他们闯入他的生活圈子,他就要受罪。
他穿戴整齐,有模有样坐在椅上,金发油亮,气色漂亮,蓝眼珠子泛白而且有点凸,一脸莫测高深的表情,但态度有礼。稀尔黛看他,只觉得他一副蠢相。他好整以暇的等着,显得气概十足,可是稀尔黛管他有什麽气概,她是来找他算帐的,就算他是教宗还是皇帝老子也一样。
“唐妮看来病得很重。”她轻声细语的,却拿一对美丽的灰眼睛直勾勾看着他。她是如此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唐妮也一样,然而她们的苏格兰性子有多倔,他可清楚了。
“她是瘦了点。”他答道。
“你不想点办法?”
“有必要吗?”他用英格兰人过度礼貌,而又僵硬的态度说。过度礼貌往往就成了僵硬的态度。
稀尔黛不作声,一迳盯住了他看。她并不擅长唇枪舌剑,唐妮也是。所以她光是瞪眼,什麽话都不必说,他就吃不消了。
“我带她去看医生。”最後稀尔黛说。“这附近有什麽好医生吗? ”
“我恐怕不知道。”
“那麽我带她去伦敦,那儿有我们信得过的医生。”
克里夫气炸了,却没吭气。
“我今晚大约得住这里了。”稀尔黛说,摘下手套,“明天我开车带她走。”
克里夫气得脸都黄了,到傍晚时,连眼白也都有点黄,简直怒火攻心。可是,稀尔黛始终温文婉约。
“你应该找个看护什麽的,好来照料你。你实在该找个男仆。”稀尔黛说。他们刚用过点晚餐,表面上舒舒适适的坐在那儿喝咖啡。她的声调柔和,不亢不卑,但克里夫听来,却好似被她拿棒子在头上猛敲。
“你这麽觉得?”他寒声问。
“当然!这有必要。否则的话,父亲和我就把唐妮带走几个月,这情况不能再拖下去。”
“什麽不能再拖下去?”
“你难道没看到那丫头的样子?”稀尔黛对他瞠目直视。这会儿他看来像只烧红了的大龙虾。
“唐妮和我会谈谈。”他说。
“我已经和她谈过了。”稀尔黛说。
克里夫受够了护士的摆弄,他恨她们,因为她们老让他不得清静。男仆那更不得了!他才不要有个男人成天在他周围绕,随便找哪个娘们都要比男仆好。可是为什麽不能是唐妮?
姊妹俩一早开车走了,唐妮那样子好像复活节的羔羊,坐在操持方向盘的稀尔黛身边楚楚可怜的。父亲不在家,不过肯辛顿那房子可以住人。
大夫为唐妮仔细做检查,询问她的生活史。“我不时在画报上看到你的照片,你们夫妇俩的合照。你简直有点声名不佳了,是不是?文静的小女孩长大了就是这样,你到现在也还是个文静的好孩儿,尽管画报上那样子说。没事,没事,你的器官方面没有问题,不过可不能这样子下去!可不能!告诉你丈夫带你进城,或者到国外去,散散心,找点乐子!你太没有活力了,没一点元气,没一点元气。心脏神经已经有点失常,哦,没什麽啦,只是神经衰弱罢了,到坎城或比亚瑞孜去玩一个月,包你百病全消。别再拖下去了,否则後果我不敢担保,好消耗生命力却没补充,要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一趟,可别再这个样子下去,你注意,不要消沉!千万不要让自己消沉!”
稀尔黛绷住了下巴,表示她打定了某种主意。
麦克立斯一听说她们进了城,捧着玫瑰花便跑来了。“哎呀,怎麽了?”他大叫。“你瘦得不成样子,我从没见过有人变得这麽厉害!怎麽都不让我知道?跟我去威尼斯!去西西里!走,跟我去西西里吧,这时节西西里正美。你需要阳光!你需要生气!唉,你这是在消耗自己!跟我走吧,到非洲去!去他的克里夫,甩了他,来跟我。他一和你离婚,我马上娶你。跟我一起去享受人生。老天爷,薇碧山庄那种鬼地方会害死人,要人命的地方!闷死人的地方!害死每个人!跟我一起去享受阳光,你就是需要阳光,而且,还要有个正常的生活。”
可是唐妮一想到要扔下克里夫不管,心跳就停了。她不能那麽做。不行!不行!她就是不能那麽做。她必须老老实实回薇碧山庄去。
麦克立斯恼了,稀尔黛不喜欢麦克立斯,但拿他和克里夫一比,她宁可要麦克立斯。最後,姊妹俩还是回中部去。
稀尔黛跟克里夫说明一切。她们回来时,他的眼珠子还是黄的。以他的状况,他也是心力交瘁了,但稀尔黛说,医生说的那堆话,他句句都得听,当然,麦克立斯说的除外,克里夫听着最後通牒,从头到尾默不作声。
“这地址是个好男仆的,他本来在照顾那医生的一名病人,一直到上个月,那病人死了才结束工作。他人很好,一定肯来。”
“可是,我又不是病人,我才不要什麽男仆。”克里夫,这可怜的家伙说。
“这里还有两个女人的地址,其中一个我见过,她一定能胜任,这女人差不多五十岁,蛮安静的、人很壮,心地好,有她的教养。”
克里夫悻悻然的,一句话也不说。
“好,克里夫,如果明天还是什麽事都没解决,我就打电报给父亲,我们要把唐妮带走。”
“唐妮要走吗?”克里夫问。
“她不想走,可是她非走不可,我母亲就是因为忧郁烦躁而死於癌症的。我们不想再冒什麽险了。”
因此第二天,克里夫就指名要泰窝村教区护士:包顿太太。这个人选,显然是管家柏兹太太建议的。包顿太太快要退休了,想要接些私人看护工作。克里夫很怪,他最怕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不过他以前得猩红热时,包顿太太照顾过他,他认识她。
两姊妹马上打道去拜访包顿太太,泰窝村一排比较新的房子,其中一栋就是她家。她们见到一位四十来岁,面貌相当称头的妇人,穿护士服,围了白领、围裙,正在拥挤的小客厅泡茶。
包顿太太十分殷勤有礼,看来人很随和,说话带一点含糊的土腔,但是用辞造句中规中矩。她照料生病的矿工有多年经验,很是自负,也很有自信。总之,她身份不高,但在村中也属统治阶级,颇受到一点尊敬。
“啊,查泰莱夫人的气色很是不好,她以前那麽健康有劲,现在却不成了,她这整个冬天垮下来了!哎,日子难过,真的难过。可怜的克里夫爵爷,呃,那场战争害了多少人!”
只要夏医师肯放包顿太太走,她立刻可以到到薇碧山庄来。照道理,教区护士这个职位她还得做两星期,不过,你晓得,他们可以找人替代。
稀尔黛找夏医师打个商量。星期天,包顿太太就提了两只箱子搭马车来了,稀尔黛和她聊,包顿太太是随时可以和人聊起来的,讲得起劲,她苍白的脸孔就会泛红,显得好年轻。她四十七岁。
她丈夫泰德.包顿,二十二年前,离上个圣诞节整整二十年了,当时也正是圣诞节的时候,在矿坑里意外死掉,遗下她和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中。这孩子伊蒂,现在已经嫁人了,丈夫在雪非德布兹卡药局做事。另一个丫头在契斯飞尔德教书,周末如果没约会,她就会回家。现在的年轻人懂得玩,和她阿薇.包顿年轻时可不一样。
泰德是矿坑爆炸时送了命的,当时才二十八岁。他们总共四人,最前头的夥伴大叫快趴下,他们都及时趴下,只有泰德来不及,一命呜呼。後来调查事故,他们偏向厂主,说是泰德自己太过惊慌,不听命令,想乱跑,所以照看是他的错。因此赔偿金也只有三百镑,而且他们赔得好像那是一笔赠款,而不是法定赔偿金,因为实在是死者自己出错。她想开一片小店面,但公司又不肯一次把钱给她,说她一定会把钱乱花光了,搞不好去喝酒喝光,她只得每星期去领三十先令。对,她每星期一去公司领钱,一次排上一、两小时的队,差不多四年。有两个小孩要抚养,你又能奈何?幸亏婆婆待她很好,幺儿会走路之後,她白天替媳妇看顾两个孩子,让她有机会到雪菲德去上急救班,到了四年,她更读了护理课,取得证书。她决心自力更生,把孩子带大,所以先暂时在尤塞特医院干个助理。後来公司,泰窝村煤矿公司其实就是老查泰莱爵士,见她能够自食其力,就对她很好,让她当教区护士,大力支持她,对这一点,她倒要替公司说句公道话。这些年来她一直做这份差事,如今渐渐觉得工作太繁重,需要换个轻松的话儿,因为做教区护士必须到处跑。
“没错,公司一直对我很好,我总这麽说。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怎麽说泰德的,打从他下坑开始就是最勇敢的,他们那些话等於说他是懦夫,不过他人死了,也没法子再说他们什麽了。”
包顿太太在言谈之间,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复杂情感。她偏袒她这麽多年所看护的矿工们,但又自觉得地位高他们一级又有一肚子愤恨。那些主子!主子和矿工起纠纷时,她永远挺着矿工,太平时期,她又一心巴望能做上等人,上等阶级令她着迷,投合她那种飞上枝头做凤凰的英格兰人心态。能够到薇碧山庄,她是乐坏了,跟查泰莱夫人讲话,真真乐坏了,老天,夫人和一般矿工的妻小差别有多大!她百般的描述与形容,然而从她的话里却可听出她对查泰莱夫妇的一股嫉恨心,对主子阶级的嫉恨。
“当然了,查泰莱夫人会给折磨死的,幸亏她有个姊姊来帮她。男人哪,不管高低,都认为女人为他们辛苦是应当的。啊,我向矿工们训过许许多多次了。但是你知道,查泰莱爵爷伤得这麽厉害,他是受不住的,那一家子一向傲慢,态度上总是冷淡,好像他们有这权利似的。可是,後来这样子凄惨的给送回来!这对查泰夫人是很难的,她或许要比爵爷更受不住,有多少她根本享受不到!我和泰德才做了三年夫妻,但是可以告诉你,那三年我有一个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丈夫,他是千中选一,每天开开心心,谁想得到他竟然会死?到今天我都还不太能相信,虽然我亲手处理他的遗体,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他真的走掉。对我来说,他没死,没死。”
薇碧山庄有个新人的说话声,唐妮感到新鲜,她便又有了兴趣听人说话了。
来到山庄的第一个星期,包顿太太却不开口,她那自信十足的专横态度不见,变得紧张不安。她在克里夫面前很害怕,都不说话。他喜欢这样子,很快就恢复镇定,让她替他做事,而丝毫不理会她。
“她是个很管用的小角色!”他这麽说。唐妮诧异地张大眼精,但并没有反驳什麽。两个人所得到印象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