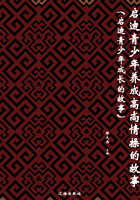“我没办法!我今晚一定要和他在一起,否则我根本去不了威尼斯。我就是没办法。”
稀尔黛面对的人好像又是她父亲似的,出於一种策略运用,她让了步。他同意开车到曼斯非,姊妹俩一道,吃过晚餐,等到天黑送唐妮到小路底,隔天早晨再到小路底接她。她自己则在曼斯非过一宵。那里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来去方便。不过她气得要死,呕她妹妹的气,气她破坏她的计画。
唐妮把一条翠绿色的围巾挂上了窗台。
由於一肚子气,稀尔黛对克里夫的态度反而亲切起来了,他到底还有脑筋。就算从功能上来说,他少了性能力,那反倒好,如此一来冲突就少多了!稀尔黛再也不想沾上“性”那档子事,“性”字头上,男人都会变得淫邪、自私而又有点讨人嫌。唐妮比许多女人要少忍受这方面的闷气,如果她能领略到这点的话。
而克里夫也认定稀尔黛毕竟是真正的聪明女子,会是男人最得力的夥伴,如果他有心往政坛发展的话。不错,她不像唐妮那麽呆,唐妮像个天真的小孩子,你得帮她找藉口,她不是那麽可靠的。
下午茶提早在大厅喝,大门敞开,让阳光透进来。每个人似乎都有点在期待什麽。
“再见了,唐妮丫头!要安安好好的回到我的身边来。”
“再见了,克里夫!是的,我不会去太久的。”唐妮简直是温柔的。
“稀尔黛再见!你会好好的盯着她吧?”
“我甚至两只眼睛会盯住她。”稀尔黛说。“她迷路不会迷太远。”
“你说得喔!”
“包顿太太,再见,我相信你会仔细照顾克里夫爵爷的。”
“我会尽力的,夫人。”
“有什麽新闻,写信给我,把克里夫爵爷的情形告诉我。”
“好的,夫人,我会照办。希望你玩得开开心心的回来,让我们也开心。”
大家都挥手道别。车开了,唐妮回头看着台阶上坐轮椅的克里夫,内心不免有点感慨。不管怎样,他总是她丈夫,薇碧山庄是她的家,一切还是不是环境造成的。
钱伯恩太太拉开园门,祝福夫人假期愉快。汽车驶出园林遮天蔽日的阴暗树林,上了公路,沿路有步行回家的矿工。稀尔黛把车转向克罗西路,这不是主线道,但直通曼斯非。唐妮戴上黑眼镜。她们沿着铁道直驰、铁道开在她们下方的路堑里,然後,她们从一座桥上越过了铁道的路堑。
“那是往小屋去的小路!”唐妮。
稀尔黛不耐烦的瞥了那小路一眼。
“真可惜我们没法子直接上路!”她说。“要不然晚上九点钟我们就可以到伦敦的巴摩大街了。”
“我为你感到难过。”唐妮在她的黑眼镜後面说。
她们很快便到了曼斯非,这个一度相当有浪漫气息,如今却是教人看了心碎的煤矿城。稀尔黛把车停在一家名列汽车旅游指南书上的旅馆之前,登记了房间。事情整个变得无趣之至,她恼怒得都不想说话了。可是,唐妮忍不住的要把男人的来龙去脉告诉她。
“他!他!你是怎麽叫他的?你一直只说“他”。”稀尔黛说。
“我从没叫过他什麽名字,他也没叫过我的名字,想起来也蛮奇怪的。我们就只用珍夫人和约翰爵士来互相称呼。他的名字是奥立佛.密勒斯。”
“而你愿意放弃查泰莱夫人的头衔,去当奥立佛.密勒斯太太?”
“我非常愿意。”
唐妮已经没救了。不过,要是这男人曾在印度干了四、五年军官,那麽他多少有点本事,显然也很有个性。稀尔黛开始松动了一些。
“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和他吹了。”她道。“然後你会觉得和他有过一腿很丢人。咱们和劳工阶级是混不来的。”
“可是你那麽主张社会主义!你一向站在劳工阶级那一边。”
“发生政治危机时,我或许站在他们那边,也就因为如此,我才了解咱们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有多困难。不是我势利,而是整个调调根本格格不入嘛。”
稀尔黛是曾经和真正搞政治的知识份子混过,所以驳不到她。
在旅馆里,这百无聊赖的晚上延延挨挨的过去,最後她们百无聊赖的吃过了晚餐。唐妮把几件东西丢进一只小丝袋,重新梳头。
“爱情终究是美好的,稀尔黛。”她说道。“在恋爱时,你会觉得你是活生生的,而且是活在天地之中。”她那口气像在自吹自擂。
“我想每只蚊子也都有这种感觉。”
“你觉得牠们也有这种感觉?那牠们真幸福!”
夜色清朗无比,而且天气一直很好,连在小镇也一样。今天一整晚都会有月光的。稀尔黛不悦地扳着脸,像戴了副面具,再度发动汽车。她们加速上路。穿过包士福,走另外一条路。
唐妮戴黑眼镜和遮掩的帽子,坐在车里沉默不言。稀尔黛越反对,她越护着她那男人。她会跟着他一起排除万难的。
她们亮着车灯,在经过克罗西路的当儿,火车嘟嘟的通过了,灯光暗淡,使夜色显得更甚幽微。稀尔黛算好了在桥尾拐弯开进小路。她一下子的减速。岔出路面,车灯白光闪闪的射入杂草丛生的小巷子。唐妮往车外看,见到一道人影子,她开了车门。
“我们到了!”她轻声说。
稀尔黛则已关掉车灯,集中注意力在倒车和转弯。
“桥上没东西吧?”她简洁的问一句。
“你可以倒车。”那男人出声道。她倒车上桥,转过来,沿着马路往前走了一段路,再倒入小巷子,辗着地面上的草和蕨,停在一株山榆树底下。最後,车灯尽熄,唐妮下了车。那男人立在树下。
“你等很久了吗?”唐妮问他。
“没很久。”他回道。
两人一起等候稀尔黛下车,可是稀尔黛拉下车门,紧坐不动。
“这是我姊姊稀尔黛,你不过来和她说说话吗?稀尔黛,这位是密勒斯先生!”
守园人用手提了提帽子,却未走近。
“陪我们走到小屋吧,稀尔黛!”唐妮恳求道。“不会太远的。”
“车子怎麽办?”
“常有人把车停在小路,你可以把车锁上。”
稀尔黛没吭声,在那儿想着。然後回头望了望路底。
“我能不能绕过树丛倒车?”她问。
“哦,可以的。”守园人说。
她绕着转弯道慢慢倒车,一直到离开了路面,再也看不见字止,然後再锁了车下来。入夜了,然而还有些亮度。荒凉的巷子,树篱长得又高又乱,显得十分漆暗。空气中飘着些淡淡的香气。
守园人走在前头,再来是唐妮,而稀尔黛尾随其後,大家都没说话。在崎岖的路段上他用手电筒照亮,三人继续往前走,一只猫头鹰在橡树间一直呼呼低呜,萝西安静地跟着。没人有话说,实在也没什麽好说的。
好容昜唐妮总算看见小屋晕黄的灯光了,她心跳了起来,感到有点忐忑。他们仍然走着,一个接一个。
他打开锁着的屋门,在她们之前跨入那虽然温暖,但四壁精光的小屋子。壁炉里火红而低,桌上首度端端整整的舖上雪白的桌巾,摆着两只餐盘,两只玻璃杯。稀尔黛把头发一甩,四下打量这间空荡荡,不怎麽上相的屋子。然後她一鼓作气的抬头盯住那男人看。
他中等高度,身材瘦瘦,相貌倒生得不错。他静静的,和人隔了段距离,好像压根儿不想开口说话。
“坐嘛,稀尔黛。”唐妮倒说了。
“坐!”他说。“要么我帮你沏杯茶或什麽的,还是你想来杯啤酒?凉的哦。”
“啤酒!”唐妮说。
“请给我啤酒。”稀尔黛说,故作矜持的样子像在嘲弄。他望着她,眨眨眼睛。
他抄起一只蓝色的壶子,慢吞吞走到厨房的水槽。等他端了啤酒回家时,脸上的表情又换了一个样子。
唐妮靠门边坐着,稀尔黛却往他的椅子坐下来,背对着墙,靠着窗户角落。
“那是他的椅子。”唐妮悄声说。稀尔黛像给烧着了似的弹起来。
“你坐,你坐!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咱们当中没什麽大人物。”他若无其事说。
他为稀尔黛拿了一只杯子过来,用蓝壶子先给她斟了一杯啤酒。
“至於香菸……”他说。“我是没有,不过也许你碰巧带着。我自已是不抽菸的。你要吃点什麽吗?”他转向唐妮。“如果我拿东西出来,你会吃一点吗?你平常都会吃一点的。”他操土腔说,有一种出奇的平静自在,好像他是个客栈老板。
“有什麽吃?”唐妮问,脸红红的。
“你要是想吃的话,有煮火腿,乳酪,腌渍的胡棑东西没有很多。”
“我就吃一点,”唐妮说。“你要不要,稀尔黛?”
稀尔黛却抬头去看他。
“你为什麽讲约克郡话?”她轻声问他。
“那个!那不是约克郡话,是德比郡话。”
他也看着她,带着那种疏远的笑容。
“好,就算是德比郡话好了!你为什麽说起德比郡话来了?你最先是说普通英语的。”
“哦,是吗?我想换个方言说说不可以吗?别这样,让我说德比郡话,只要我爽快就行啦。希望你不反对。”
“那种调调听起来有点做作。”稀尔黛说。
“呀,是这样子啊!那你的调调在泰窝村听起来也会很做作。”他再度看着她,脸骨边上故意现出一股冷漠色,好像在说:哟,你算什麽人呀?
他慢条条踱到储藏室去拿吃的。
姊妹俩对坐无言。他另外又拿来一副刀叉和盘子。然後说:“要是你们觉得没什麽差别的话,我想把外套脱掉,像平常那样。”
说着他就把外套脱了,挂在钩子上,然後只穿着衬衫,一件奶油黄的法兰绒薄衬衫,往桌前一坐。
“自己动手!”他道。“自己动手!别等人家问!”
他切了面包,之後便坐着不动。稀尔黛也和唐妮以前一样,感受到他沉默和疏离的力量。她看到他搁桌上那小型的、细致和放松的手。他不是个普通的工人,他不是。他是在演戏!在演戏!
“话虽如此。”她拿了一些乳酪开腔道,“如果你跟我们姐妹俩说普通英语,不是土语,感觉会自然点。”
他觑着她,觉得她意志强悍。
“会吗?”他用普通英语说。“会吗?你我之间有什麽会比你对我说,你巴望你妹妹再见到我之前,我已经下地狱去了,或是我也说了差不多一样不爽的话来回敬你,更自然的?别种话更会自然吗?”
“哦,是的!”稀尔黛说。“光是有礼貌就会自然了。”
“这麽说,是种习惯罗!”他道,哈哈大笑起来。“算了。”他说。“我不耐烦讲礼貌,就让我保持这个样子吧!”
稀尔黛显然是吃了瘪,一肚子怒气。再怎麽说,他也可以装出他晓得人家给了他面子,可他不但没有,反而还假惺惺的在演戏,摆出一副他是老大的架子,倒像是他在赏人家面子。简直不要脸到家了。可怜的迷迷糊糊的唐妮,给那男人掌控得死死的!
三人吃着,不说一句话。稀尔黛倒要瞧瞧他的餐桌礼仪是怎样。她不能不发觉到他天生要比她斯文、高雅。她有那种英格兰人的笨拙,他却有英格兰人的沉着、自信,举手投足都一丝不苟的。想要凌驾过他,绝非易事。
但他也板不倒她。
“你真的认为。”她说,口气略略亲切了点。“值得冒这个险?”
“什麽值得冒什麽险?”
“和我妹妹胡搞。”
他咧开他那令人咬牙的笑脸。
“这你得问她!”
说着,他掉眼看唐妮。
“你是自己来的吧,妞儿?不是我强迫你的吧?”
唐妮看稀尔黛。
“你可别随便怪罪别人,稀尔黛。”
“我当然不想这样,可是总得有人用点脑筋。你这辈子要有些事是持久的,不能想胡搞就胡搞。”
一阵安静。
“哈,持久的!”他开了腔。“什麽是持久?你这辈子又有什麽是持久的?我想你正在办离婚吧。那叫什麽持久?你自己持久的顽固性子,这点我倒看得很清楚。那对你有什麽好处?在你老掉之前,你自己就会被自己的顽固性子烦死了。一个顽固女人和她的自我意志?是呀,这两者倒是有极强的持久性,真的如此。谢天谢地,要对付你的人不是我!”
“你有什麽权利这样对我说话?”稀尔黛道。
“权利?你有什麽权拿好的持久来约束别人?让别人去搞他们自己的持久事儿吧。”
“拜托,你还以为我是关心你吗?”稀尔黛压着嗓子说。
“是啊,”他答道。“你是。这是出於情势所迫,你大致可算是我的大姨子。”
“还差得远呢,我跟你保证。”
“没差很远我跟你保证。我自有我的一套持久法则,你回去管自已的生活吧,我每天都过得和你一样痛快,如果你坐在那儿的妹妹来找我,是为了那点痛快和温情,那是因为她清楚自己要什麽。是她上过我的床,不是你,感谢老天,多亏了你那种持久性。”在一阵死寂後,他接下去说:“呃,我穿裤子可是把屁股穿在前面的,我要是有飞来的艳福,我会庆幸自己好运气。坐在那儿那女人能带给男人的乐子,远远比你这种女人要多太多了。这很可惜,因为你也可能是一只香甜的苹果,而不只是外表好看的酸苹果。像你这种女人需要好好的来接枝。”
他若隐若现的笑着看她,露一点色相和欣赏意味。
“像你这种男人。”她说:“应该给隔离起来,对自己的低级趣味和色慾振振有辞。”
“哟,夫人,像我这种的男人可只剩下硕果仅存的几个了,不过你是活该落得孤伶伶自己一个人。”
稀尔黛已经起身走到门口了,他也站起来从钩子上抄下外套。
“我自己就可以找到路。”她说。
“我相信你可以。”他悠悠哉哉说。
他们又很好笑的排成一列,走出小路,没人说话。一只猫头鹰还在呼呼直叫。早知道他该把牠抢毙。
车子安然在那儿,没有人动过,沾了点露水。稀尔黛上车发动引擎。另外两个人等着。
“我的意思就只是。”她在她的堡垒里发言道,“我怀疑你是不是会考虑到这麽做值不值得,你们两个都是!”
“一个人大块吃肉,对另一个人可能像在吞毒。”他在黑暗中说。“不过对我而言,那是佳肴美酒。”
车灯霍地亮了起来。
“唐妮,明儿早上别让我等人。”
“不,不会的。再见!”
汽车慢慢爬上公路,迅速而去,留下静悄悄的夜。
唐妮害羞的抓着他的胳膀,两人走回小路。他没出声,最後她把他拉住了。
“吻我!”她喃喃说。
“不,等一下!让我把心情定一定。”
她觉得他这话很有趣。她仍然抓着他的胳膀,两人悄然的在小路上走。此时此刻,她真高兴和他在一起。她打寒颤,晓得自己很可能会被稀尔黛硬给拖走。他则不出一声,莫测高深。
等他们再次进了小屋,她高兴得简直要跳跃,她是摆脱掉她姊姊了。
“你对稀尔黛真的很坏。”她对他说。
“该有人适时给她一巴掌。”
“为什麽?她那麽好。”
他没作答,一样一样的做好晚间的杂事,动作沉稳而又俐落。他脸上有怒色,不过不是生她的气。唐妮是这麽觉得的。怒色使他显得格外的英俊,又有一种灵气和神采,挑动得她四肢都酥软了。
可是,他一直没理睬她。
直到他坐下来,开始松开鞋带,这时才从因为发怒紧绷的双眉底下抬起眼来看她。
“你不上楼去吗?”他说。“那儿有根蜡烛!”
他扭了头过去,指指桌上那点燃的蜡烛。她听话秉烛上楼,他则盯着她丰满起伏的臀儿看。
那是个充满肉慾的激情之夜,她有些被那种激情吓到了,几乎不大情愿耽於其中。然而冲刺所带来的强烈快感,非常猛烈,非常不同,比之柔情带来的兴奋要更令人心醉。尽管有一点心惊胆颤的,她还是任着他为所欲为,那种把什麽都豁出去了的淫浪,让她震撼到了极点,将她剥得精光,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女人。那不是柔情蜜意,也不是男欢女爱,而是一种烈火般熊熊燃烧肉慾,把人的灵魂烧化成了灰烬。
就在那最最私密之处,把人心最古板、最顽强的羞耻感烧化殆尽。她是挣扎到最後才肯让他为所欲为,尽情尽性的。她被动而顺从,像个奴隶,一个献出了肉体的奴隶。然而那股激情之火蔓延到她全身,像要烧尽一切,那熊熊之火传过她的胸膛、她的五脏六腑的时候,她真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那是一种如火如荼,妙不可言的死。
阿贝拉曾说,在他和海乐思热恋的岁月,他们尝遍激情的各般层次和妙处,唐妮以前总是不大明白阿贝拉的言下之意。其实是同样一回事,一千年、一万年前都是同样一回事!希腊古瓶上所描绘的,到处都一样!美妙的激情,放纵的激情,是人生的需要,而且永永远远都需要,需要它去把那些做作的羞耻感通通都烧掉,把肉体这副最粗犷的原石焠炼到精纯的地步。用那把情慾慾火去焠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