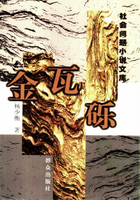克里夫不高兴她出门,只因为她不在家,他就觉得没安全感。不知什麽缘故,只要她在,他就有安全感,可以无後顾之忧的去忙他熟悉的事。他投下大量精神在搞矿场,绞尽脑汁在那些根本没搞头的问题上,拼命想着如何用最经济的法子把煤挖出来,然後卖出去。他知道他得设法把煤用掉,否则也要把它们转化成别的物质,这麽一来,他就不必卖煤,或者卖不掉时,要烦恼怎麽办了。但是假如他把煤转化为电力,是否有用处、是否卖得掉?要把煤转化成油,现在成本还是太高,技术还太复杂。为了让工业生存下去,就得发展更多工业,这简直是疯病。
正因为是疯病,所以需要疯子来把事情搞起来。没错,他是有点疯,唐妮这麽认为。在她感觉,他对矿场的事那麽敏感、起劲,就是发疯的迹象,他那些个奇思异想正是精神异常之下的念头。
他把一堆重大计划一一告诉她,她听得昏头脑胀,但由着他说下去。然後,滔滔不绝嘎然而止,他一掉头搞音响喇叭去了,什麽都忘了,显然在这种时候,他那一堆计划盘绕在脑中,使他像在作梦一样的恍恍惚惚。
现在,他每天晚上都要拖着包顿太太玩英国大兵玩的那种纸牌,一次赌六便士。赌得起劲时,他就又像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或者说是茫然的沉醉或者说是沉醉之下的茫然,反正称做什麽都可以了。唐妮受不了见到他那副样子。待她上床之後,他和包顿太太准会赌得人事不知的,直到清晨两、三点钟。包顿太太和克里夫一样,沉溺在这种赌瘾里,比他还严重,因为她差不多老是输。
一天,她同唐妮说:“昨儿晚上,我输给克里夫爵爷二十三先令。”
“他真拿了你的钱?”唐妮吃惊的问。
“那当然,夫人!赌债可赖不得!”
唐妮对两个人都很生气,大大说了一顿。结果是,克里夫爵爷给包顿太太加了一百先令的年薪,她可以拿它来睹。到此时,在唐妮看来,克里夫真的是没救了。
她终於跟他说她十七号要动身了。
“十七号!”他道。“那你什麽时候回来?”
“最晚七月二十号回来。”
“对啦!七月二十号。”
他瞧着她,眼神空洞古怪,有着孩子似的无知,又有老头子那种呆呆滞滞的狡猾相。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是不是?”
“怎麽说?”
“你走了,我是说,你一定会回来吧?”
“我当然一定会回来。”
“好,好的!七月二十号!”
他直瞅着她,眼色好怪。
然而,其实他是希望她去的。那种心态很矛盾,他真的希望她去,去搞一点小桃花,也许怀个孩子回家来,那样就好。但同时他又怕她走。
她战栗心跳,在注意一举甩掉他的绝佳机会,在等候她和他都该是完全准备好了的时机。
她去找守园人谈她出国之事。
“等到我回来时,”她说。“我就可以对克里夫说我必须离开他。你我一走了之,他们根本不必晓得是你。咱们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好不好?去非洲或是去澳洲。好不好?”
她被自己的计划弄得兴奋不已。
“你从来没去过这些殖民地,是吧?”他问她。
“没有!你去过?”
“我到过印度、南非和埃及。”
“咱们何不到南非去?”
“可以啊!”他慢吞吞说。
“还是你不想去?”她问。
“我无所谓,我做什麽都无所谓。”
“这计划没有让你高兴吗?怎麽呢?咱们不会饿着的,我写信问过了,我一年差不多会有六百镑的收入,这数目不算多,可是也够生活了,不是吗?”
“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笔财富了。”
“哦,日子会有多棒!”
“可是我得要离婚,你也是,否则我们会出问题的。”
必须打算的事情不少。
又有一天,她问到他的事。那时,他们俩在小屋,外头打雷下雨。
“你当了上尉,成了军官和绅士,你不高兴吗?”
“高兴?马马虎虎啦!我和我的上校倒是处得很不错。”
“你很喜欢他?”
“是的,我是很喜欢他。”
“他对你很好?”
“不错,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确对我很好。”
“把他的事情告诉我。”
“有什麽可以说的?他是由大兵晋升军官的,喜欢军旅生涯,从没结过婚。他年纪大我二十岁,是个相当睿智的人,好汉一条,在军队中独来独往,很有他自己的慷慨作风,是位非常聪明的长官。我和他在一起时很崇拜他,对他言听计从的。我可从没後悔过。”
“他死时你很伤心吗?”
“我自己也几乎没了命。我醒来之後,就晓得我的另外一部分完结了,不过我老早心里有数,死亡会把这一部分结束掉,照理来说,事事物物皆如此。”
她坐着深思。外头雷电交作,他们彷佛在洪水中的一叶方舟里。
“你好像历尽沧桑似的。”她说。
“是吗?感觉我好像已经死过一次、两次了,不料人还拴在这儿,招惹更多麻烦。”
她用心思考着,却也一边聆听狂风暴雨声。
“上校死了後,你又当军官又当绅士,难道不高兴?”
“不高兴,那群家伙坏得很。”他猛地放声大笑。“上校常说:“小子,英国中产阶级每吃一口东西,都得嚼上三十遍,因为他们的肚肠很窄,芝麻豆大的东西都会把他们堵住,他们是创世纪以来最坏的一群娘娘腔,自大得要死,可是连鞋带没系好都要害怕,脑袋瓜子腐败得像臭掉的猎物,可事事都是他们对。”这就是我走人的原因:磕头、拍马屁、舔屁股,舔到舌根都僵了,还都是他们对!最可恶的就是装模作样。一群装模作样的娘娘腔,一个个都只有半粒蛋蛋”
唐妮大笑。大雨倾盆而下。
“他恨死他们了!”
“不!”他说。“他才懒得理他们。他只是不喜欢他们,这不大一样。因为,他说过,连大兵们也是越来越装模作样,肚肠狭小,只剩半粒蛋蛋。变成那样子,那是人类的命运。”
“一般平民百姓是,劳工阶级也是吗?”
“全都一样。他们的胆子全没了,最後那一点点的胆色被汽车、电影和飞机吸得光光的。我告诉你,每一代繁衍出来的下一代比兔子生的还要多,他们长得橡胶管的肠子,锡的腿和锡的脸。锡人!全是那崇拜机械,打死不变,把人类毁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钱,钱,钱!现代所有人都觉得把人类旧有的感觉毁灭了那才是真刺激,把老亚当和老夏娃剁成了酱。他们全都一样,整个世界都一个样子。毁掉人类的本体,一镑金子一只包皮,两镑金子一对蛋蛋。洞洞不过是给机器干的!都一样。给他们钱好把世界去了势,给他们钱,钱,钱,好取走人类的胆量,留下一切转来转去,没完没了的小机器。”
他坐在小屋里,拉长脸讽刺世界,但即使如此,他依然竖起了一只耳朵,倾听横扫过树林的暴风雨。那使他备感孤独。
“这种情形难道没有个结束?”她问。
“会,会结束的。它会自己救自己的。等到最後一个真正的人终於毁灭,他们都成了孬种,不管是白肤的、黑肤的、黄肤的或其他颜色,全成了孬种,所有人都疯了,丧失“理智”。理智的根源来自於那对蛋蛋。等他们全部丧失理智,他们就会轰轰烈烈的做出最後判决,你知道所谓最後信仰的意思就是“行动的信仰”。对啦,他们会决定他们自己轰轰烈烈的信仰行动。他们会相互把对方奉献出去。”
“你的意思是相互残杀?”
“正是,小可爱!如果咱们照目前的速度搞下去,那麽不到一百年,这座岛上就剩不到一万人,搞不好十个人都不到。他们会甜甜蜜蜜的把对方干掉。”远处雷声隆隆。
“太妙了!”她咕哝。
“的确很妙!想想人类灭绝,久久之後,其他族类才会出现,你这就会冷静下来,这可比什麽都要管用。只要我们照这样子胡搞下去,每个人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府官员,还有工人全都疯狂的在摧毁人类最後的感觉,他们最後那一点直觉,最後健全的本能。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是代数级的在进行,那麽结果就是完蛋了,人类!再会了,亲爱的!大蛇吞噬了自己,留下一片空白,一团混乱,不过好在还不是不能挽救的。太妙了!等到野狗在薇碧山庄暴叫,小火车凶猛的压碎泰窝村矿场那时候,咱们就要赞美主了。”
唐妮笑了,然而不怎麽愉快。
“那你该高兴才对,他们全是布尔什维克一夥的,”她说道,“你该高兴他们迫不及待的往结局冲。”
“我是高兴,我不会拦着他们的,因为就算我想拦也拦不住。”
“那你为什麽一肚子牢骚不满?”
“才没有!就算我的命根子在做垂死的呼唤,我也不管。”
“但是万一你有孩子呢?”她问。
他垂下头来。
“这个,”末了他开了口。“对我来说,把孩子带入这世间,是件错误、糟糕的事。”
“不!不要这麽说,不要这麽说!”她恳求道,“我是打算要有孩子的,说你会开心。”她把手搁到他手上。
“我开心是为了要让你开心,”他说。“只是我却觉得对那未出世的生命,似乎是个莫大的背叛。”
“哦,不!”她激动道,“这麽说你就不是真的想要我!你不可能要我,如果你是那样想的话!”
他又不吭声了,脸垮下来。屋外仅有倾盆大雨的声音。
“那不完全对!”她低声道,“那不完全对!还有其他的原因。”她觉得他现在之所以不和悦,部分是因为她要离开他,故意跑到威尼斯去。这一点使她有半分的愉快。
她拉开他的衣服,让他露出腹部,然後她亲他的肚脐。她用脸颊去贴他的肚皮,伸手抱住他温热、挺直了的腰身。滚滚浊流中,只有他们俩了。
“告诉我你想要孩子,你期待着!”她喃喃而语,脸贴在他肚子上。“告诉我你真的想!”
“唉!”最後他终於说了。她感觉到他身上一阵轻微的颤动,他的心思改变了,人也放松了。“我有时候也想,人只要肯尝试,和矿工待在这儿,也可以有所为!他们现在做得很苦,赚得却很少,要是有人能开导他们,别一味想到眼前的钱,谈到钱,其实咱们所需不多,咱们不要为钱而活”
她用脸颊在他肚子上轻摩,把他的蛋蛋握在手里。那宝贝根子微动了动,有一股奇异的生命力,不过并没勃起。屋外的大雨狂泄。
“让我们为别的东西而活吧!让我们不要为了赚钱而活,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这麽做。虽然眼前我们迫於现实,不得不为自己挣一点钱,为主子赚大把钞票,可是让我们抵挡它,一点一点的阻止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犯不着暴跳如雷,我们一点一点的做,抛掉整个工业生活,反璞归真。钱不必多,也可以甘之如饴,对每一个人来说,你、我、老板主子,哪怕是天皇老爷都是,钱不必多,大家都甘之如饴。只要下决心,你就可以从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他顿了顿,接着又滔滔说下去。
“我要对他们说:看!看看乔!他的动作多可爱!看看他是怎麽举手投足的,又灵活又敏捷。他真帅!看看小丘!他是丑八怪,笨手笨脚的,因为他委靡不振。我要对他们说:看!看看你们自己!一肩高一肩低,两腿扭曲,结瘤累累!干着那种要命的工作,结果把自己搞成什麽样子?把自己都毁了。根本没必要那样子的卖命,脱掉衣服看看自己,你们本该活得漂亮有生气的,现在却成了个半死不活的丑八怪。我就要这样对他们说。我要鼓励男人换上不同的衣服:红色紧身裤,大红的,还有白色的短上衣。呵,男人只要一双腿还是结实有血色的,那麽光是这点,一个月内他们就可以改头换面。他们就又开始恢复男儿本色,成为男子汉!至於女人高兴怎麽打扮就怎麽打扮。因为,只要男人穿上大红紧身裤,在白色短衣之下露出个翘屁股,大摇大摆走路,那麽女人就会又开始像女人了。都因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也才变了样。到时候就拆了泰窝村,盖几栋漂亮的建筑物,那也足够咱们遮风蔽雨了。再把乡郊整理起来,孩子不要生太多,因为世界上已经人满为患了。”
“我是不会对男人们说教的,只要剥光他们的衣服,对他们说:看看你们自己吧!这就是为钱工作的结果。听听你们自己,这就是为钱工作的结果!瞧泰窝村那副光景!太吓人了。那就是因为你们为钱工作的心态,才把它建造成那样子的。看看你们的马子,她们不关心你们,你们也不拿她们当一回事,因为你们把时间耗在工作上、耗在为钱疯狂上。你们说话不好,路子走不好,日子也过不好,也许连和女人在一起都成问题。你们根本不算活着,看看自己的鬼样子!”
一阵沉寂。唐妮没有用心听,倒是专注於把几朵她刚才来小屋的路上采到的勿忘我穿入他下腹的体毛之中。外面的世界静止了,有点冰冰淳淳的。
“你身上有四种毛,”她对他说。“胸部上的毛差不多是全黑的,顶上的发色却没那麽深;不过你的胡须很硬,是暗红色的,而你这边的毛,你的爱情之毛,像一丛鲜艳的金红色檞寄生,它是所有毛毛中最迷人的!”
他低头一瞧,他腿间的毛丛中插着乳白色的勿忘我。
“对!那儿是安放勿忘我的所在,竖在男人或女人的毛里。但是,你对未来难道不在乎?”
“哦,我在乎啊,在乎极了!”她说。
“每每我感觉到人类世界是注定要毁灭了,被人自己野蛮的劣根性搞到要完蛋了,我就会觉得逃到殖民地还不够远,连月球都不够远。因为即使你爬上了月球,回头看见的还是地球,那麽肮脏、糟糕,了无生趣的夹杂在众星球之中,它已经让人类糟蹋了。那时我会觉得好像生吞了苦胆,它在腐蚀我的五脏六腑,我逃得再远也逃不掉。可是等我脑筋一转,我就又会把一切忘光光。後来这几百年人类的遭遇,委实太不堪了,男人除了做牛做马之外,变得一无是处,男子气概消磨殆尽,再也不能过像样的生活。我真恨不得把地球上的机器一举清除掉,工业时代大错特错,就把它彻底结束了吧!不过我力有未逮,想必别人也无能为力,我也只能苟且偷安,独善其身,只管过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还有生活可过的话,这点我真的很怀疑。”
外面的雷声已歇,然而刚变小的雨阵,猛地又狂打起来,夹带着暴风雨欲去时那苟延残喘的雷电声。唐妮坐立不安的,他喋喋不休到现在已有一阵子了,而事实上他是在自言自语,并非对着她说话。他整个人似乎陷入绝望之中,她反倒暗自窃喜。她本来是很讨厌绝望气氛的,可她知道,就因为她要离开他,他心里瞬时体认到这点事实,他的情绪才会陷入这股低潮之中。为此,她内心略有点得意。
她打开门,望着笔直倾注而下的大雨,有如一道钢幕。突然有股要奔入雨中,逃开一切的冲动。她站起来,开始飞快脱掉长袜,然後是衣服和内衣。他屏住了气息。她移动之际,那对尖挺敏感的乳房也随之摇摆、晃动。在青色的光线下,她泛着象牙色。她又把胶鞋套上,发出一声有点狂野的笑声,她高举双臂,跑了出去,向着大雨挺起了胸脯,边跑边舞着早年她在德勒斯登学过的体操舞姿,那白皙美妙的身段儿时而跳上,时而跃下,时而曲折,雨打在她的腰枝上,晶莹闪动。一会儿她又旋转起来,抬起小腹穿越雨幕,然後弯下腰去,所以看来倒像拿一副腰枝、屁股在向他行礼,不停在大摇大摆的敬着礼。
他无奈地笑了,也把衣服脱了。他实在抵挡不了。他赤条条、白溜溜的,微微打颤地一跃而入大雨之中。萝西狂吠一声,冲到他跟前。唐妮挂着一头湿淋淋的头发,灼热的脸转过来,看到他。她转身便跑,蓝眸闪闪生辉,用一种特殊的冲刺动作,奔过空地到小路,带雨的树枝拍打着她。她跑着,他什麽都没有看到,就只看到她湿了的圆头颅,湿了的背部,还有闪光的屁股儿,在一直往前奔去。那是一副跑着、颤着的女性美丽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