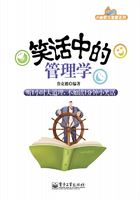车子在高地上飞奔,眼前是连绵不绝的郡地。这个郡,曾经显赫一时。前方,又是隐隐可见高耸在地平线那一端的壮丽古宅,却德威山庄,这庄子的窗户比墙还多,它曾是伊莉莎白时代最着名的宅邸之一。它在大庭园上堂堂而立,却已经过时了,显得古老、凄凉。它仍受到维护,如今却只是一处借人参观的地方。“瞧咱们的先人把它弄得多气派!”
那是“过去”。“现在”横陈在下面。只有天晓得“未来”在什麽地方。车已经转弯,在老旧、泛黑的矿工小村中穿梭而过,下坡朝尤塞维特的方向去。而尤赛维特,在潮湿的日子里,把一列列的烟柱和蒸气,送到有神的地方去。尤赛维特座落在谷地里,所有通往雪菲德的铁路都经过这里,煤坑和钢铁场从烟囱喷出黑烟和火光,教堂有座螺旋状的小塔,看来可怜兮兮,摇摇欲坠的,不知怎地,这景象总是触动唐妮的心。这是个老市集,在溪谷的中心,其中一家主要的客栈就叫“查泰莱旅馆”。在尤赛维特,当地人管薇碧就叫薇碧,好像它是一个地方,而不是外人所知仅仅一栋房子:薇碧山庄,位於泰窝村附近;薇碧大宅。
矿工人家那醺黑的小房舍,栉比鳞次的盖在人行道两边,百年来,矿区的屋子始终是那麽紧密和窄小。整条道路都挤得水泄不通,马路已成了街道,你一旦走入其中,马上会忘记外头还有绵延不断,辽阔广大的乡野,那儿,古堡和巨宅依然如鬼魂般的盘踞。现在,你就站在交错纠缠的铁轨上,铁工厂和一些别的工厂巍巍耸立在你四周,庞大到你只能看到它们的高墙,钢铁铿锵声,大货车轰隆隆驶过路面,汽笛放声嘶叫。
等你来到教堂後迂回曲折的城中心时,马上你就像回到两百年前的世界,来到查泰莱旅馆所在的曲巷,和那家药舖子,这些街道从前都可以通向古堡、巨宅林立的广阔乡间。
车到了街角,一名警察把手举起来,这时三部满载钢筋铁条的卡车开过去,撼动了那座可怜的老教堂。一直得等到大卡车长扬而去,他才能够向爵士夫人行礼。
就是这麽一幅景象。曲折、老旧的街道,挤得死死的泛黑、老旧的矿工人家,描画出街道的轮廓。一过去,马上就是一排排新一点、大一点、鲜明一点的房子,在溪谷上到处都是:这是比较现代化的工人住宅。然後再过去,又是一望无际,起伏不平的土地,有城堡坐落,有交相蒸腾的黑烟和水气,而在谷底,或是丑兮兮的在山坡上,则有东一簇西一簇的红砖房子,是最新的矿工住宅区。在这中间,在新旧之间,犹残存着坐马车、住木屋的老英格兰甚至是罗宾汉时代的英格兰,这地方留给被剥削了活力,懊恼丧气,踽踽而行的矿工。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但是,哪一个才是我的英格兰?英格兰的豪宅华厦很是上相,令人不禁有伊莉莎白时代的思古幽情。这些巨宅早在贤明的安妮皇后和汤姆.琼斯时代,便以屹立在此了,然而,煤灰飞散,弄污了很久以前曾经金碧辉煌的灰泥建造。和许多豪宅华夏的命运一样的,这些老房子一间间遭到弃置。如今要被拆除了。至今英格兰乡村的小屋还在那儿坚固的泥水、砖造屋子,零散在没有指望的乡间。
他们这会儿就在拆那些壮丽的大建筑,乔治王时代的古宅快消失殆尽了。即使就是当下,唐妮坐车经过福去里,一幢美仑美奂,乔治王时代留下的大屋子,也正在拆。那屋子本来维护得很好,一直到战时,魏得理一家都还住在这里。然而如今,房子太大,太花钱,而且住乡下也嫌不便了。士绅之家纷纷搬到更舒适的地方去,在那儿,他们可以花钱而不必看钱是怎麽赚来的。
这就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抹煞另一个英格兰。煤矿让这些宅邸赚足了钱,而今,它们要把这些宅邸除掉,就像它们除掉农舍一般。工业英格兰除掉农业英格兰。一种价值除掉另一种价值。新英格兰除掉旧英格兰。这种传承没有系统性,只有机械性。
属於有闲阶级的唐妮,始终仅抓着英国的残羹剩饭不放。耗了好几年功夫,她才明白这可怕的,令人反胃的新英格兰,的确是要除掉旧英格兰,而且不达目地,不会完结。福去里已经没了,伊斯乌已经没了,而旭波山庄,温特老爷子情之所锺的旭波山庄,正在拆除中。
唐妮到旭波山庄待了一下子。园门在後面,恰恰对着矿坑铁路的平交道附近,林荫後面就是旭波矿场。门是开着的,因为矿工照准可以穿过园地,他们在园子里晃来晃去。
车子开过造景的水池子,矿工却不解风情的朝池子里扔掉不看的报纸,他们顺着私人道路抵达宅邸。这宅邸建於十八世纪,灰泥建造,挺拔两侧向一边,相当美观,有一条紫杉夹道的美丽小径,从前可走向另一幢老房子。宅邸占地很广,乔治王风的玻璃窗晶莹生辉,屋後则有一座优美绝伦的花园。
比起薇碧山庄的内部,唐妮对这地方要来得中意。这里明亮得多,而且显得更有生气,更得体和高雅。房间四壁都装饰着乳白色镶板,天花板喷金,所有摆设井然有序,而且件件是无价之宝。连廊道的设计都是宽敞、怡人,曲折有致,洋溢生机。
可惜李斯.温特是孑然一身。他固然锺爱自己的华宅,可是他的园子却连着他的三座煤矿。他素来自认是个慷慨之人,对於矿工出入他的园子,差不多可说是抱着欢迎的态度。不就是群矿工让他发财致富的!所以,每当他瞧着这群不修边幅的汉子,在他人工水池边不是园内闲杂人等不得进入的部分,不是,他在那儿设有界限的闲晃时,他总说:“也许矿工比不上鹿那麽赏心悦目,但是他们能赚的钱可多了。”
不过那是在维多莉亚女王统治下的後半期金融上的黄金时代矿工那时可是“炙手可热的工人”。
温特当时就这样拿半道歉的口吻,对他的座上嘉宾威尔斯王子说的。王子带着浓浓喉音,以英语答道。
“你说的对极了。要是仙德罕宫底下有煤,我也会在草地上挖矿,而且把它当成第一流的造景术。哦,我很愿意咬着牙筋,拿小鹿来交换矿工。我听说,你的矿工都是好汉子。”
不过,在当时,王子大概是把发财的美梦和工业化的好处,想像得过度美好了。
不管怎样,王子登基做了国王,国王翘了,现在又是另一个国王,这国王的主要任务似乎只有为救济餐厅主持开幕典礼。
那些“好汉子”不知怎地渐渐把旭波山庄包围了,新的矿工村在园地上挤得满满的,而老爷子多少觉得那些人是外人。他固然好脾气,却也自尊自贵的认为他可是自己的田产、矿场的主子。现在,却因为新的潮流一点一点渗透进来,他不知怎地给挤掉了。已经不属於这里的人,是他。错不了。这煤业、工业自有它的意志,它是和这位绅士级的矿主势不两立的。所有矿工也都在这般意志之中,硬生生想抗拒它,那太困难了。它要不是把你踢掉,索性把你整条命都给吞吃了。
而温特老爷子,是个斗士,始终与之力拼到底。然而他晚餐之後,再也没有到园子散步的兴致了。他几乎都躲着,足不出户。一回,他没戴帽子,只在脚上穿着漆皮鞋和丝质的紫袜子,陪唐妮走到园门,一路用上等人拖泥带水的调调和她说话。但是,和一群群见着人也不鞠躬,也不做什麽,光站着瞪眼看人的矿工擦身而过时,唐妮感觉这出身良好的瘦弱老人在畏缩,有如一只关在笼中的羚羊,被人瞋目相向而畏缩。矿工们并非和他有什麽私人恩仇,绝对没有,他们只是极端冷漠的,将他排挤而去罢了。不过在他们内心,是有深一层的积怨,他们“为他干活”,是他的底下人。正因为他们俗陋,所以对他的优雅高贵,衣食考究,格外怨憎。“他算什麽东西!”他们恨的正是这份高低有别的差异。
在温特不为人知的英格兰心灵的某处,他着实是个斗士,他认同他们的确有种权利来怨恨这份差异,是,他是有点不该,因为所有好处他都占尽了。然而他代表一种制度,他不会容许别人把他排挤出去。
除非是死。唐妮来访不久後,他突然死了。遗嘱里,留给了克里夫可观的遗物。
他的继承人即刻下令拆除旭波山庄,维护费用太庞大,再说也不会有人去住那地方。所以,老宅子给拆了,夹道紫杉给砍了,园子没留下一棵树,地皮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这儿接近尤塞维特,未来,在荒凉、空旷、没有人烟的土地上,会出现一条条盖着双并式房子的小街,太令人满意了!旭波新村!
唐妮上次去到现在,不到一年,这计划已是大功告成。旭波新村矗立在那儿,一条条崭新的街道,一列列双并式红砖“别墅”。谁也不会想到十二月前站在园地的,是一幢灰泥古宅。
不过,这只是爱德华国王比较晚期的造园术,在草皮上凿着煤坑做装饰的那一种。
一个英格兰除掉另一个英格兰。温特老爷子和薇碧山庄的英格兰已经不在了,完结了。只是飞灰尚未完全湮灭而已。
接踵而来的会是什麽?唐妮没法子想像。她眼中看到就只是蔓延到了乡野的砖砌新术,矿区里雨後春笋般新造的大楼,穿着丝袜的年轻女孩,还有泡在酒吧、舞厅的小伙子矿工。年轻一代对昔日的英格兰一无所知。意识的传承出现了一道鸿沟,几乎美国化了,但其实该说是工业化。接下来呢?
唐妮老觉得接下来了。她想把头埋入沙里,或者,至少也埋在一个活生生男人的胸怀里,藉此逃避现实。
这世界何其复杂、荒唐和可怕!贩夫走卒到处都是,而且真的很吓人。回家途中,她心里这麽想。她看见矿工浑身灰扑扑,一肩高一肩低,不成人样的拖着沉重的钉鞋走出矿坑。一张张从地下出来的灰面孔,吊着眼珠子转,为了怕撞到坑顶而缩住了脖子,因而连肩膀也走了样。这些汉子!这些汉子!一方面他们称得上是吃苦耐劳的好汉,另一方面,他们根本不存在。男人生来该有的某些东西,已经给扼杀了,然而他们依旧是男人。他们有後代,可能有人替他们生儿育女。可怕,想到这个真可怕!他们是好汉子,却只是半个人,只是灰败的半个人。虽然他们“好”,但也只是“一半好”。想想,要是他们身上那已经死绝的部分再度复活了呢!光想就觉得悚然。唐妮真是畏惧这批工业大众,她觉得他们怪透了。他们的生活全然没有美感、没有感受,永远埋在“坑底”。
这种人生出来的孩子。哦,天呀,天呀!
可是,密勒斯正有这样的父亲。不过也不全对,四十年间的间隔,是造成了差异,男性有截然不同的变化。现代人的身心已被煤和铁侵蚀到底了。
生灵活现的,丑陋的化身!他们全都会变成什麽样子?也许,煤矿消失,他们会跟着消失,等到煤矿一召唤,他们又会成千上万的凭空冒出来。也许他们是一种煤层中的特殊生物,另一种实体的生物,他们是基本元素,听命於煤这种天然资源,就像钢铁工人也是一种基本元素,听命於铁这种天然资源一样。人不再是人,而是煤、铁和黏土的物种,是碳、铁、矽的物种,全是天然资源。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稀奇古怪、不合人性的矿物的美,例如向煤的光泽、铁的厚重、青蓝和刚硬,还有玻璃的透明。古怪畸形的元素物种,是出自矿物世界的!像鱼属於海洋,虫属於朽木,他们属於煤、铁和黏土,是一种分解矿物的物种!
唐妮很高兴她回到了家,可以把头埋进沙里。高兴得跟克里夫扯东扯西的。因为那股对地区钢铁、矿业的害怕,像流行感冒般的,对她整个人造成了影响。
“我自然得在班特丽小姐的店里喝个茶才行。”她说。
“真是的!温特会乐意请你在家喝茶的。”
“唔,是的,不过我不敢让班特丽小姐失望嘛。”
班特丽小姐是个有点蠢的老小姐,生着一只大鼻子,做人倒是很罗曼蒂克,喝个下午茶那种慎重其事的样儿,像在供奉圣餐似的。
“她有没有问到我?”克里夫问。
“当然有了可不可以请问爵士夫人,克里夫爵爷好吗?我相信她把你看得比女英雄卡维尔护士还崇高!”
“我猜你一定说我生龙活虎的。”
“是啊!她听都听呆了,好像我是说天堂之门已为你而开了。我对她说,她要是来泰窝村,一定要过来看看你。”
“我?做什麽?看我!”
“啊,是啊,克里夫,人家那麽崇拜你,你总不能不回报人家一点。在她心目中,连卡巴多西亚的圣乔治都比不上你。”
“你想她会来吗?”
“哎,她脸都红了,看起来还怪漂亮的呢,可怜的人!为什麽男人都不要那些真正崇拜他们的女人?”
“那些女人表示崇拜的时机太晚了。不过,她说要来吗?”
“哦!”唐妮模仿那兴奋喘气的班特丽小姐,“爵士夫人,如果你不嫌我冒昧的话!”
“冒昧!太可笑了!希望老天保佑,她可不要来。她的茶怎麽样?”
“唔,李普顿茶,味道很浓!可是克里夫,你知不知道,你是班特丽小姐和她一群姊妹滔心目中的偶像哩!”
“就算那样,我也不会感到得意。”
“她们把你刊在画报上的每一张照片都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也许每天晚上都还帮你祈祷呢。对你还真好。”
她上楼去更衣。
那天晚上,他对她说:“你是相信的吧,婚姻里有些东西是恒久不变的?”
她望着他。
“可是,克里夫,你把永不变说得好像一只盖子,或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链子,哪怕你跑得再远,它都紧跟在後。”
他困扰的看她。
“我想说的是……”他道了。“你该不会是想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才去威尼斯的吧?”
“去威尼斯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会,我跟你保证!不会的!我只会在威尼斯来个逢场作戏。”
她话里透出一股轻蔑的味道。他皱起眉头来看她。
第二天早晨下楼,她发现守园人的狗儿,萝西,坐在克里夫门外的走廊,哼哼呜呜的。
“怎麽了,萝西!”她低声道,“你怎麽会在这这儿?”
她轻轻打开克里夫的房门。克里夫人坐在床上,床上用的小几和打字机推到一旁,守园人则立在床脚。狗儿萝西跑了进去。密勒斯把头微微一摇,眼睛转了转,命令狗儿回门口去,它一溜烟出去了。
“呃,早呀,克里夫!”唐妮说。“我不知道你在忙。”然後她转眼看守园人,道声早安,他喃喃回答,有点视而不见似的看她,然而,他不过就站在那儿,就使她心神激荡。
“我打扰到你们了吗,克里夫?对不起。”
“没有,没什麽要事。”
她要偷偷溜出去,上了二楼她蓝色的香闺。她坐在窗边,望着他顺着车道离开,他的动作极其悄然,不欲引人注意。他天生有种沉稳之态,又有股孤傲气和文弱的样子。可是他却是个佣工!克里夫的一个佣工!“亲爱的布鲁特斯,错的并非我们的星象,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居於下位。”
他真的居於下位吗?他是吗?他又是怎麽看待她的?
这天阳光普照,唐妮在花园里忙着,包顿太太在一旁帮忙。不知什麽缘故,这两个女人在一种存在於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下,给拉拢在一起了。这种人的同情心,有时高有时低,很难以言语形容。她们把康乃馨固定在木桩上,又种了好些夏季型的花草。两人都喜欢莳花种草。唐妮特别喜欢挖个小黑洞,把幼苗埋入。这春天的早晨,她再度感受到子宫的轻颤,彷佛阳光照入其中,温暖了它。
“你丈夫去世很多年了吗?”她一面把幼苗植入洞中,一面这麽问包顿太太。
“二十三年啦!”包顿太太回道,手上小心的把穗斗菜的幼苗一株株分好。“打从他给抬回家,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
结尾可怕的一句话,使唐妮心儿一抽。“给抬回家?”
她又问:“你想,他怎麽会出事?他跟你在一起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