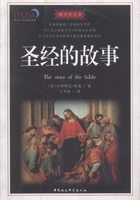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着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是“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 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
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
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着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克化”
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着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高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 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
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延安之旅
1936年初,王牧师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脑中装着无数的问号,斯诺在午夜登上了向西的火车。这一回,他无法像与艾黎初次见面时那样享用专属的VIP车厢了,因为他早已不是国民政府的贵宾。相反,若想接触共产党的核心,他还必须突破国民政府的重重封锁。
斯诺必须突破的,还有病菌的“围攻”。启程前,他的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可以想见,当年的共产党根据地条件有多么艰苦。
经过两天的颠簸,斯诺抵达了西安。在那里,他拜访了曾经是共产党员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半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那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与自己要剿灭的“共匪”成了同盟,邵力子也一度被怀疑为同谋。
斯诺错过了见证西安事变的时机,不过,他见到了促成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铁三角”的重要人物——此人也是促成斯诺陕北之行的关键,他就是上文提及的“王牧师”董健吾。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他曾在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手下任职,颇有地位,从蒋介石到杜月笙均熟识。后来,他丢官弃教,成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员,往返于红区和白区之 间,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
首次代表共产党接触张学良的正是这位王牧师。1936年初,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张学良大惊。
王牧师不慌不忙,详细解释了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团结抗日的必要性,最终说服了张学良。这位将军竟真的将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王牧师,由他去延安带回一个谈判方案,并促成了张与共产党之间进一步的会晤。
王牧师将这些故事讲给了斯诺听,这令斯诺感慨不已:“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但斯诺此次到西安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与王牧师的见面也正是为了通过他进入红区,另两名关键的联络人是刘鼎和邓发,前者是上文曾经提及的“查尔斯”,来自上海的地下组织,时任张学良的副官;后者则是被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取他首级的共产党政治保卫局局长——有趣的是,当时他却正住在张学良家中。
起初,王牧师准备再次去找张学良借飞机,安排斯诺搭乘,但后来这一计划告吹了,张学良担心自己的美国飞行员多嘴告诉外人,一个外国人被“扔”在了红区。
替代的交通工具是军用大卡车。7月初的一个早晨,斯诺终于出发,与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另一名外国人马海德——就是那个在上海专注于治疗性病,经常与艾黎、史沫特莱等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开展活动的美国医生。但奇怪的是,在斯诺后来写作的《西行漫记》中,并没有提及马海德。后来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曾就此问过父亲,马海德的回答是:“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
后来周幼马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其实就是宋庆龄。马海德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马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 出国。后来,她又把马海德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彼时的延安依然被国民党所控制,是靠近“匪”区边界的最后一个重要前沿据点。斯诺和马海德乘坐的道奇卡车一直开到了延安,然后便要开始步行,只有一个骡夫当向导,一头骡子驮着他们的行李。
这段在黄土高原上的步行令斯诺感到惴惴不安,他不仅惊异于四周“难以置信的,有时是令人恐怖的”景象,更担心自己和马海德的财物遭遇不测——骡子驮着的有照相机、医疗用品,他们手上还带着手表,脚上穿着牛皮鞋。一路上,骡夫对斯诺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每一次都令斯诺担惊受怕。
这样的跋涉历时两天。后来,最令斯诺担心的已不是财物,而是人身安全——两个外国人,从白区而来,会令红区的人们产生怎样的联想?
一路上,他们看见石板屋的土坯墙上写着许多标语,诸如“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这些都是极具共产党特色的事物。后来,共产党执政后,类似的宣传形式铺遍了大江南北,尽管标语内容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遇到一位“清瘦的青年军官”后,斯诺和马海德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位军官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们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斯诺又惊又喜。
他很快明白,这位军官就是周恩来。这位人称“美髯公”的共产党核心人物英语说得不太流畅,但很清晰。
与周恩来接上头,标志着斯诺和马海德终于真正抵达了他们已经念想很长时间的地方——共产党根据地。
“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这样总结自己成功抵达红区的经历。
克里斯马
“当我1937年到达延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人。而当时我所遇到的别的中国人却充满了卑鄙、残酷等各种令人厌恶的特性。”
在红区,最先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两个“红小鬼”。
见到周恩来后,斯诺只与他交谈了几分钟,随后便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两人约定第二天到附近村庄里的司令部见面。
天色已晚,斯诺和马海德与驻扎在百家坪的一些人一起吃饭,他们中有的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的是无线电报务员,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
“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斯诺这样记录自己在根据地的第一顿晚餐。
这位美国记者注意到,端来饭菜的是两个孩子,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斯诺冲其中一个孩子招呼。
可那个“态度冷淡”的孩子根本就不理他。过了一会儿,他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一样。场面有些尴尬。
同一饭桌上一位戴着厚玻璃镜片近视眼镜的军官笑了,他是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他扯了扯斯诺的袖子:“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 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在这时,“小鬼”端来了冷水。这一次,斯诺学会了“正确”的称呼:“谢谢你——同志!”
“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小鬼”看着斯诺回答道。
这段小插曲令斯诺感慨万千。“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他在《西行漫记》中记录说。
“生气勃勃的精神”,这或许是令斯诺对红区心生好感的一项重要原因。第二年,当斯诺的夫人海伦也得到机会前往陕北时,同样惊异于人们的精神面貌:“当我1937年到达延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人。而当时我所遇到的别的中国人却充满了卑鄙、残酷等各种令人厌恶的特性。当时,我还不懂得克里斯马这个词,但这正是每个领导人都具有的——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生存,就不可能在成千上万心怀敬佩的追随者中确立领导地位。
从人性的角度描写人的故事,或者说,描写根据地各类人物的克里斯马,成为斯诺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切入点之一。这位到华已经近十年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从未在中国的年轻人中见到过如此动人的精神气质——他们乐观,活泼,精力充沛,忠于革命。
“我最感兴趣的,正是红军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映人性特点和人类英雄行为的史实,而政治仅仅是第二位的。”从西北返回北京后,斯诺对《每日先驱报》的编辑说。
毫无疑问,从共产党的核心领袖身上,斯诺也领略到了这种神奇的克里斯马,他在自己后来的作品中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人性的”描写——毛泽东,在斯诺的眼中“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颇有林肯的气质”,“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或许是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斯诺记录下了毛泽东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喜欢不惹人注意地随意散步,从腰带下面找虱子,在热天脱掉长裤等。
周恩来,被斯诺视为“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