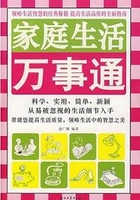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官方语言来说,“中国与非洲国家虽然相隔遥远,但人民都曾遭受过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在长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战斗情谊。”
这种“情谊”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中国政府为此投入巨大。
正如周恩来曾在1960年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所说的:“我可以保证一点,我们不仅在你们战斗时支援你们,在你们进行建设时,我们要给予更大的支持,因为那时我们的条件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正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却没有停歇过。比如,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予几内亚大米1万吨。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 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更为着名的援助项目是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为了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了9·88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6人为之献出生命。铁路建成后,为了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管理或提供咨询。
这条铁路的修建与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开国总统尼雷尔有关。
1965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与***主席会谈时,考虑到中国当时也不富裕,尼雷尔只提了一个要求,即希望中国帮助建造一家纺织厂,***主席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尼雷尔建议将纺织厂取名“毛泽东纺织厂”, 但中国方面表示没有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习惯,于是命名为“友谊纺织厂”。
尼雷尔后来回忆说,在那次会谈时,他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提出纺织厂的要求后,***又接着问:除了纺织厂,就没有别的啦?这时,他才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的要求。***听后说,如果需要,我们就干!后来,建铁路的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的回忆则可以更多的补充。他说,他曾与尼雷尔一同去西方国家,告诉他们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需要这条铁路,“然而,西方国家拒绝了我们”。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你看,这种友谊多么纯洁和真挚。当别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建成了这条铁路。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友谊呢?”卡翁达说。
辛格博士访华次数最多?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多来中国,一定要超过基辛格。最后,尼雷尔将这个数字定格在了13次。
实际上,尼雷尔本人也保持了另一项纪录——在所有非洲人中,他显然是与中国“关系最铁”的“老朋友”,迄今共被《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提及15次,跟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持平,比那个向延安送了摄像机的荷兰导演伊文思还多1次。
非洲的另一位“铁友”是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他被以“老朋友”身份提及13次。
纳米比亚是非洲最年轻的国家,1990年才获独立,因此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更多是在帮助努乔马领导的政治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向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中国训练我们的战士并提供武器和各种物资,让我们在跟南非种族隔离殖民政府的斗争中最终夺取了胜利。”努乔马说。
当然,中国政府绝不会傻到为了几个“老朋友”的“情谊”去做这么大代价的投资。实际上,这项投资的回报是丰厚的,它更多地体现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中国的非洲朋友在台湾、西藏、人权问题上给予中国一贯支持,多次在国际大会上挫败反华提案,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韩丁与土改问题
有人建议,把关于***的内容都删掉就行了,但韩丁却不肯通融,他说,那是刘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
“二代老友”的涌现并不意味着“一代老友”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让我们将目光转回斯诺、斯特朗们身上——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故事还很丰富、曲折。
还记得韩丁吗?那个在战争年代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他是寒春的哥哥,是阳早的大学室友。后来,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韩丁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并以专家身份留在了中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他1947年第二次来中国时本来就带着这样的任务,彼时,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了一批拖拉机给中国,韩丁随团而来,身份是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韩丁和妻子史克的女儿卡玛(CarmelitaHinton)出生在北京,并一直在中国成长。所以,她虽然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但却有一颗“中国心”:一口京片子,最喜欢吃中国北方家常菜,最欣赏中国国粹书画艺术。
“我记得不学英文的事。”卡玛后来回忆说,“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我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我一天到晚纠正他们,以为他们不会说话。”
在卡玛不到4岁时,父亲就离开中国回美国了。按照卡玛的说法,父亲选择回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专家的反感。“他是比较个性化的人,也比 较务实,苏联专家一来,一切都按官僚体制规程来做,他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
现在看来,这次回国似乎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原因显然还是幽灵般的麦卡锡主义。韩丁被冠以“叛国者”的罪名,随身携带的资料被美国海关全部没收。FBI严密监视他的行踪,窃听他的电话,限制他的活动。
在十六年的时间里,韩丁的护照被吊销,不能再回到中国。而在工作上,他也备受歧视,不被允许从事大部分带有技术和知识性质的工作,只能去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最后仅能依靠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务农为生。
但这些都不是韩丁所畏惧的,真正令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没收的资料——那是他在晋东南张庄所做的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调查笔记,多达1000多页。
1947年,中共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这项轰轰烈烈的改革深深吸引了韩丁,他详细记录下了运动的过程、成果,以及错误和问题。
为了拿回这些珍贵的资料,韩丁只能诉诸法律,他打了好几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好在最终于1958年胜诉。
根据这些材料,韩丁写作了一本名为《翻身》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书中,他把“张”字拆开,将张庄称为“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他在书的前言中说,自己“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
“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韩丁说。
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了解中国,这样的判断放到今日依然不过时,这让人不得不钦佩韩丁敏锐的眼光和细致的观察。
《翻身》于1966年在美国出版后,反响颇为强烈,不仅热销海外,被翻译为多种文字,被改编为话剧,甚至还成为了美国许多大学里,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但是,作为客观记录者的韩丁再次遇到了与斯诺类似的困扰——他不偏不倚的记录,不仅令反共阵营不高兴,也惹恼了共产党阵营,“罪过”是因为他在书中披露了土地改革带来的问题。比如,“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
在中国,《翻身》迟至1980年才出版了中译本,主要原因是书中大量引用了***的话,而这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被错误批判。有人建议,把关于***的内容都删掉就行了,但韩丁却不肯通融,他说,那是刘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
“我的朋友们十分恼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翻译、出版一本好书多不容易,有必要适当做点儿妥协,这个倔老头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卡玛后来回忆说,“然而气还未消,风向又变,***得以平反,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随即于1980年出版。”
扎根乡土
“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与韩丁一样,还有几位格外喜欢接触中国的农村,喜欢和底层民众在一起,他们是真正在中国扎根乡土、关注底层的人。
比如韩丁的妹妹寒春,以及妹婿阳早。上文曾经提到,他们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1949年春天,穿着肥大的八路军服装,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从事对牛、羊、马、驴的品种改良和疾病预防工作,并向当地农民传授机械化养牛的知识。直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天之后,他们才得知这盼望已久的消息。
1953年,他们被调到西安市奶牛场工作,丈夫担任副场长,妻子担任技术员;两年后,他们又一起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夫妻二人在此间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已销售近100万台。
“我们喜欢那样的生活,吃穿是配给制,自己不用操心。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工作。”阳早说。
寒春的说法则是:“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种吃饱了卧在地下反刍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1952年,他们的儿子阳和平出生,如本书上一部分末尾处所说,这个名字是宋庆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特意取的。
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左派,是毛泽东时代的支持者。他虽然喜欢自嘲为“假洋鬼子”,但他强调:“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从阳和平对自己的母亲寒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一窥他的思想倾向:“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不为资本和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大环境,所以她可以把一个科学家的好奇心带到她所干的行行业业上去,她可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
实际上,这种政治倾向或许是他们整个家族的传统——寒春的奶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正是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革命小说《牛虻》的作者,她的红色家庭里有好几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大跃进”时期,阳早、寒春所在的农场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那时的草滩上没有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只能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那时为了不坏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卫生和冷冻工作上去,每天忙着东跑西奔检查工作。”寒春后来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场的奶确实没坏一斤。”
显然,阳早、寒春所在的奶场出产的牛奶不仅没有变质品,更不会有什么三聚氰胺之类的非法添加物。
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向夫妇二人提出希望:在草滩农场上养鸭子。王震是南方人,以为有河有草就能养鸡鸭,因此希望他们能养十万只鸡鸭。
寒春当时就提出疑问:这么多鸡鸭,他们在这里吃什么?
而阳早则回答:要相信党。
根据阳和平的说法,他的父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歧,是因为“父亲是经过延安时期的,对党是绝对相信的”。
后来,虽然他们养了很多鸡鸭出来,但是由于食物不足,逃掉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寒春夫妇被调到了北京——丈夫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任译校,妻子在对外文委图片特稿社任译校。
就在阳早、寒春夫妇在草场上与牛羊在一起,同中国底层人民共劳动的那几年里,另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在中国各地旅行,行走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对他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并尽己所能写下自己的观感,这是一种极其令人兴奋的生活。
那些年里,艾黎写了许多本书,包括《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
等。但是,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则没能发行,原因与韩丁的《翻身》未能及时出版有异曲同工之处——艾黎的“书中有很多涉及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
和韩丁一样,艾黎对苏联专家的印象也不是太好:“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都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
“大跃进”开始后,1958、1959两年,艾黎访问了15个省,行程约4万公里。他对各地的激进做法也颇有微词。
“那时做的很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很不明智。”艾黎回忆说,“次年,即1960年,遭受了旱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艾黎这位依然不愿对“大跃进”进行全面的否定。他说,当时“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
“文革”来了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后来出版的《路易·艾黎自传》中,艾黎不仅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保留,对“文革”十年也着墨很少。他只是粗粗写下了“四人帮”的罪孽以及倒台之后百姓的兴奋心情。
“一个卖螃蟹的人手拿4只螃蟹,高喊:‘看我的螃蟹,3只公的,1只母的’。人们一阵大笑。用螃蟹的横行来比喻‘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似乎再确切不过了。”艾黎记录道。
实际上,艾黎本人也曾受过“螃蟹”们的祸害,他被怀疑、迫害。不过幸运的是,宋庆龄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冒着风险为他写了一份证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