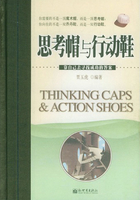世界性的冷战大幕已经拉开,中共新政权迅速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阵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美国与新中国“不共戴天”的时代。中国开始全方位将美国描述为帝国主义敌人,而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也几近疯狂——斯诺曾为《邮报》写了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坦率、真实、公正地叙述了周的革命生涯、政治风格和个人品质,但令他大为愤怒的是,《邮报》将斯诺拟定的标题“戴红色帽子的中国官员”擅自改为了“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编辑对这种“标题党”行为的解释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给每个标题都起个邪恶的名字,即便它与下面叙述的事情完全无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更令中美两国陷入彻底的敌对,曾经的“亲密朋友”和“示范先驱”,如今被称为“美帝野心狼”。直至二十余年后,双方才达成谅解。
作为史上第一个与中共进行密切接触,且写书为它表示支持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美国自然成为麦卡锡主义的重点攻击对象,一些人千方百计要找到他担任所谓“中国代理人”的证据。联邦调查局没有放过对他的监视。
1953年,政府特工人员曾以了解斯诺在新闻界的熟人为借口,在斯诺家中与他进行了谈话。后来他们报告说:“斯诺先生坚定地指出,他以前从来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仍然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他们的结论是,斯诺的态度“很诚恳,很合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然也很坦率”。
要证明斯诺为共产党干活的努力显然是徒劳。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记者以及一名信奉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者,斯诺对共产党的所有判断都是独立做出的,他与中共领导人的确曾经走得很近,但却并没有丧失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从来都是在为自己干活,并未将自己出卖给任何一个组织。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对独立性的坚持,从某种角度看,他成为“不识大体”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苏联的态度。
显然,如果他真的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工作,他应该和中共的观点保持一致。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1949年4月,这位美国记者在《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10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还说,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做出了“铁托式”的判断。这让新中国政府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1949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这或许就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悲剧——尽管中美双方彼此敌对,但哪一方都没有因此而欣赏他,遑论苏联。斯诺看到,自己已经成为所有阵营都不欢迎的人。
“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在经受了十年的孤独岁月后,50年代末,斯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斯诺虽然孤独,他的遭遇却并不是个案,安娜·路易·斯特朗也有着类似的遭遇——这位美国作家本来长期驻扎苏联,但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和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以及“二号人物”贝利亚所不容,这导致她在苏联入狱,后来又被驱逐出境。
加入中国国籍
“马海德放着上海的好日子不过,更别说放着美国的好日子不过,跑到陕北来,他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什么?”
尽管斯诺是群体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但他的政见和遭遇并不代表全部老友,尤其是那些真心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比如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医生。其实,他也是西方国家人士中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人。
新政权成立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马海德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
和平年代里,马海德不再需要扮演战地医生的角色,他对当官也没什么兴趣,而是开始重操旧业:对付皮肤性病。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1933年,马海德抵达上海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疗性病,其中大部分病人是旧上海的性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起了一场消灭性工作的运动,封闭妓院,取缔暗娼。他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与之相配合,马海德为性工作者根治性病,重新开始了早年在上海的工作。1953年,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会同其他专家制订了消灭性病计划,并先后到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 广东、广西、江苏、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为消灭各地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此后,马海德确立了新的目标——消灭麻风病。这项工作一度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很久,但依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1987年,他曾说自己是在用“最后的精力”帮助从世界上消灭那种病。
这位技艺精湛的医生对中国和中国人忠心耿耿。他坚持在医疗一线工作,当病人误以为他是“苏联老大哥”时,他总是回答:“我是中国人。”
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们增加工资,其中也准备了马海德的一份,但他却拒绝领取:“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不要因为我的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人!”
然而,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思维逻辑都是被扭曲的——马海德的身份总是被人猜疑,有人认为他是“外国间谍”,令他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工作上“大材小用”,无法正常参加一些党内会议,听报告,看文件。
这些猜疑主要的幕后黑手是康生。早在延安时期,康生就曾对人说:“马海德放着上海的好日子不过,更别说放着美国的好日子不过,跑到陕北来,他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什么?”
“不被自己人信任,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了。”马海德曾对自己的友人这样说。他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另一场叫作“文革”的更可怕的暴风骤雨在前面等待着他。
在马海德之后,另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友人是那位在新中国建国日到录音店里录下自己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记者爱泼斯坦。
在那几年里,和所有与共产主义“有染”的人一样,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在美国的生活颇为艰难,怀疑、调查、跟踪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们没有像史沫特莱一样被严格限制行动范围,而是在1951年接到宋庆龄的邀请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宋庆龄的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来,爱泼斯坦成为宋庆龄唯一指定的传记作者。
爱泼斯坦夫妇是从海路来到中国的,他们在海上颠簸了四十九天才终于 抵达天津港。当他们乘火车到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的四个字:“欢迎回家”。
这里的确成为了爱泼斯坦的家。他发挥特长,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后来更名为《今日中国》),担任执行编辑,一干就是半个世纪。
这份杂志的定位是对外传播,也就是今日常说的“外宣”,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中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但其性质则是“由非政府组织出版的外文刊物”,这样也就便于在美国市场上发行。
创办这本杂志的想法始自周恩来总理,周安排既有国际威望,又有宣传经验和技巧的宋庆龄主持创办,而宋则发动了爱泼斯坦前来担任得力助手。
早在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探访延安时,他就曾给妻子邱茉莉写信说:“这是个小规模伟大的国家……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现在,这个国家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他认为,新中国的景象印证了他曾经说过的,延安就是中国的未来。
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获得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七年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风云难料,就在爱泼斯坦入党不到四年之后,这位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朋友被关进了监狱,罪名同样是“间谍”。
不是在美国被怀疑为“间谍”,就是在中国因“间谍罪”入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似乎走不出这个怪圈。这段牢狱生活还将在后文详述。
细菌武器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在朝鲜伊川东南的一些地区陆续发现了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和昆虫等。化验证明,这些小动物、昆虫带有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
当然,在新中国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之间依然留下了一些闪烁着爱心、正义光芒的故事。
比如,宋庆龄营救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的故事,就流传至今成为佳话。
抗日战争中,有吉幸治跟随美国将军史迪威来到中国,和广泛连接外国友人的宋庆龄等人有了交往。二战结束后,他又作为军调处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被派往延安。
有吉幸治在延安观察到了浓厚的民主气氛,并将之写在了报告中,但这些溢美之词却引发了上司的不满,这导致他被调回美国。
回国后,有吉幸治创办了一份左翼报纸,仍在舆论上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麦卡锡主义者看来,这样的经历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劣迹斑斑”,有吉幸治不幸被逮捕入狱。得知消息的宋庆龄想要帮助这位老朋友,但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她显然无法在中美敌对的外交态势下通过官方途径有所作为。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想了另一个办法:将珍藏多年的母亲的结婚礼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这套礼服是用纯手工织成的绣服,宋庆龄希望有吉幸治的家人将其变卖,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后来有人曾疑问,既然这套绣服如此重要,为什么不能送些别的财物?
但事实是,高度清廉的宋庆龄副主席没有其他什么积蓄了,她在经济困难时期曾经主动要求下调工资,连国家安排照顾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资,宋庆龄也始终坚持自己承担。
幸运的是,有吉幸治的妻子并没有将这套绣服变卖,而是珍藏家中,待丈夫出狱后重新送回中国。但宋庆龄却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
最终,宋庆龄去世几个月后,这套绣服才重新漂洋过海回到中国的土地上。现在,它被保存在位于北京的宋庆龄故居。有吉幸治的儿子小有吉幸治作为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1984年到2002年一共带美国游客到故居参观了54次,并且个人捐款54次,累计约7000美元。
这则故事充满了患难中的人际温情,如果说它可以有一个主题词“情谊”,那么们合力揭露美国“细菌战”的故事则应该被打上“正义”的标签。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在朝鲜伊川东南的一些地区陆续发现了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和昆虫等。化验证明,这些小动物、昆虫带有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1952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美军侵犯中国领空和使用细菌武器。声明说:“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
然而,美军否认了这一指控。于是,这催生了一场庞大的外交战、宣传战。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宣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和朝鲜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但遭到 拒绝。而中国所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证明美军确实使用细菌武器,组织了调查团队进行实地调查。有两位着名的中国人民老朋友参与了这一阵营的活动,他们分别是文幼章和李约瑟。
当时,文幼章的身份是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他在从现场返回之后,出具了收集到的证据,并与《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进行了谈话。有记者提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
文幼章回答说:“看一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的构成,就可知道,它是没有资格调查这样的国际纠纷的。”
他还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朝鲜的代表奥图·莱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死亡营中的暴行从未加以谴责。
在冷战背景下,包括联合国、红十字会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也都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不是属于美国阵营,就是属于苏联阵营,没有普遍的公信力。
科学家李约瑟参加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并成为团队的领导者,委员会成员来自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这份长达669页的报告含有这样的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由于李约瑟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一报告通常也被称为“李约瑟报告”。也由于李约瑟的重大作用,此事之后,他被列入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去美国讲学困难重重,直到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时至如今,有关美军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美国方面并未正式承认,国际学术界围绕此话题发表的学术着作和文章也不计其数,而真相似乎仍是罗生门。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国际局势复杂,但几位参与调查的老友均是怀着伸张正义的朴素目的,为普通民众的利益鼓与呼。
二代老友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到了北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南海。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居然就接见了他们。
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他们与最初一批以记者、医生等群体为主的,在战争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结识的老朋友截然不同,可谓“中国人民的二代老友”。
这群“二代老友”在普通中国人当中同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之中最着名的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缅甸的吴努,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当然,也有属于同一阵营的国家领导人未被列入“老朋友”的单子,比如“老大哥”苏联。